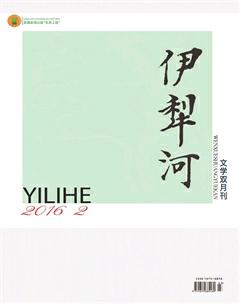“車子想回家呀!”
蘇北
上午十點多,父親打來電話,說車子過了全椒縣城,上了高速了。
很多天前,父親來電話,說省城的一個醫生,會用貼膏藥的方式,治療肺氣腫,貼三次即可,縣里有人貼了,據說效果不錯。父母要來,我當然歡迎,高齡了,不是說來就能來的,真是來一回少一回了。
昨晚來電話,說不要接,自己打的過來,我說接一下方便些,可父親堅持不要接。父親性格剛烈,說一不二,再說多了也無濟的。我又反過來想,父親是精明之人,一輩子要強,遇事喜歡研究,估計也問題不大。
這會兒父親打電話,說還是要接一下的,在中途下車會很遠很遠,還是到車站接一下吧。
省城車站多,自從有了私家車便很少去車站了,不知現在去我家鄉縣城的車停靠哪個車站。我在電話中大聲說,問清楚司機哪個車站,幾點到站?父親的耳朵這幾年明顯背了,車上又吵,他根本聽不清楚我的話,在電話中一個勁地“啊,啊,啊”。上次也是,他來電話要我先去醫院看看,順帶先把號給掛了,省得來了排隊麻煩。我去了醫院,聯系好醫生,并且還要辦個就醫卡,我在電話中告訴說:“要辦個卡才行啊!”他在電話中也是,一個勁地說:“還要檢查啊!還要檢查啊!”我說,還要有個卡啊!他還是啊啊的。于是我不耐煩地說,把電話給我媽媽。好一會兒,電話中傳來我媽媽的聲音。我說,問一下司機在哪個車站、幾點到達?母親也是聽不到,我只聽到她在電話中自言自語:車子聲音這么大我哪里能聽得到。之后又對我說:我聽不到啊,耳朵背氣,一點聽不到啊。我母親一貫能言善辯,她出身在窮人家,可她的機敏程度,一點不比《紅樓夢》里的王熙鳳差。可能是過去家里太困難,窮親戚有幾百個,她操持這么一個拮據的家庭,沒有一點善變和小心機是不行的。她的虛情和吝嗇,對我們也是一樣的。我習慣于她的風格。一輩子了,我們太了解她了。我又對著電話喊:把電話給我爸。這一下她聽清了,把手機又交給了我的爸。
父親在電話中還是啊啊聽不到啊,我于是一字一頓地用嘴對著手機的話筒大聲說:問、司、機、幾、點、到、車、站、什、么、車、站。說完,又說了一遍。這一下父親聽到了,說:“十一點十分啊。”過一會兒又說:“明光路車站啊。”我聽清楚了,便立即準備出發。
為他們來,和妻子還賭氣了一回。妻子說,他們來了,客廳睡一個,她奶奶同女兒睡。我心里想:父親最愛安靜,若把書房收拾了,放一張床給他,他可以關起門來,這樣要安靜得多。可書房書太多,要收拾起來也是很麻煩,妻子不想動,而且她還想著在書房電腦上炒股,最近股災,她套上了,這幾天國家忙救市,她每天盯著電腦,想解套呢。于是她堅持不肯收書房。
我賭氣說,干脆我去訂賓館,讓他們在賓館睡算了。反正也不怕他們回去講,到兒子那去,兒子不讓他們在家里睡。我又對妻子動之以情:八十多歲了,他們能來幾次,再來一兩次最多了。
妻子被觸動了。她很高興地去收拾房間,又上菜市場買菜,做飯。
我則上街去買了一只新的折疊床,好放到書房里去。
那天我去找醫院,這家原叫針灸醫院的小醫院現在掛牌為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了。我先找朋友打聽,之后自己又親自跑一趟,掛號,預約名醫。進到醫院,我一下子被震住了:可以說太壯觀了,一醫院都是中風的人在樓下院子里散步、透氣。能走一點的,拄著那種專門的四個爪子的拐杖,一歪一歪地走。不能走的,坐在輪椅上,被陪護的人(這些人或親人或雇傭來的)推著。坐在輪椅車上的,造型也是奇形怪狀,看得人心里真是又驚又怕。
可是一離開醫院的大門,來到大街上,又是一馬路的車水馬龍,人們匆匆忙忙地走著,各人帶著自己的心思去趕自己的路。
現在我去車站的路上,剛走了一半,電話來了,電話中父親說,我們到啦!剛下車,在車站大門等你。
我加快車的速度,可是老城區,路窄車多,樹密人稠,亂七八糟。我小心著,七拐八繞,還是來遲了。好在我剛停好車,就見父親拎著大包小包,在那東張西望,母親貼在父親身后,手里也是兩三個小包,正呆呆地望著遠處。我小跑過去,父親一下子看見了我,就朝這邊走來,母親還愣著,父親不耐煩,用胳膊肘兒抵了一下母親說,走走走,趕緊走。母親一愣神,立即跟上了父親。
我接過父親手里的東西,嘴里說,大包小包的,又帶什么東西,不要帶什么東西來。父親不吭聲,緊跟在后面,母親緊跟著父親。
我開好車門,將東西放好,安排父母前后坐下。回來的路上,母親說,又沒有什么東西,一點土雞蛋,一只老雞,昨天殺好的,放冰箱,早上出門時帶的,中午就把它煨了,還算新鮮。父親不吭聲,一路望著窗外,忽然問:這是什么路啊?我說長江路。父親一副驚奇的樣子:長江路變成這樣了?過去我們來開會老住在長江飯店,那個時候,長江飯店,算了不起的啦!
隨著,到家了。進了我們小區的院子,父親一下子熟悉了起來。因為小區一直沒有任何變化。進了家門,大包小包地放下,我讓父母先坐下休息,妻子在廚房也正噼里啪啦炒得起勁。不一會兒,幾個菜端上了桌,有肉圓和燒小雞,還做了一個紅通通的莧菜湯。中午一頓豐盛的午餐,父親還喝了點酒。本來不讓父親喝酒,母親主動說,有酒啊,拿給老頭子喝喝。我說,肺子不好不能喝酒,要克制。父親笑著說(很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醫生說能喝一點嘛,喝兩杯好下菜。母親接著說,今年給他喝掉幾十斤酒,每頓都喝,給他喝了一屋子的空酒瓶。父親說,散酒啊,幾十塊錢一斤。
吃完飯,坐在餐桌前閑聊。我把醫院的情況說了一下,把就醫卡找了出來。母親說,明天早點吧,遲了排后面。父親說,六點鐘吃飯,六點半出門吧。早看早安生。于是說定了,一個下午無事,他們看看電視,我則忙自己的事了。
第二天早早來到醫院,因我已踩過點,環境和所在樓層都已掌握,因此沒費什么周折,可是一進到預約的病房,喝!一屋子的人。捷足先登的大有人在。我們慌張地排上一個隊伍,排到一半,我仔細研究一下各隊情況,發現父母所排的這支隊伍,不是我找的那個名醫的隊列,于是我又轉來悄悄告訴父親,讓他們轉移。父親悄悄拽了一下母親,又趕緊排到最里面的一個隊列去。
排定了心便安了下來,慢慢往前挪吧。我到處走走,研究新情況,見到一個老年婦女正在和別人聊著,我走上去側耳旁聽,她嘻笑著說,我三十歲時就有關節炎,就是找了這個醫生貼膏藥,效果還不錯,貼了幾十年了。近幾年腰疼,于是又改貼腰上了。
隨著隊伍的挪動,貼起來還是挺快的。我還特地跑到醫生跟前討好,說,我是那天專門找過他的,父母也是從縣里專門慕名而來的,希望能引起他的關注,給認真貼貼,可是這個醫生根本無動于衷,對我的拜訪已沒有一點兒印象,他心不在焉地將粘有濃稠黑色液體的膏藥拍到那些老人的前胸或后背上,一會兒一個,一會兒一個。
隨后,輪到了我的父母,父親掀起瘦瘦的前胸,很快被貼了幾塊大大的膏藥,母親坐過去,同樣脖子上被貼了好幾塊。
之后交錢領藥,過些日子,還要再貼兩次,醫生都一一寫了。我們也一一記下。
父母安心了。一項夢想了幾個月的大事完成了。
回來的路上,父親說,現在反腐敗形勢這么緊,你們經濟單位,這次有人出問題嗎?
我說,沒有。
父親說,銀行制度完善些,可能執行要嚴格一點。政府部門,特別是搞什么開發區,整天就他媽招商招商,開發開發,胡搞一通,害了很多人。
我媽在后面插嘴說,一出事,就完了,豬不吃狗不聞的了。
父親說,這個時候,要處處小心,對自己要嚴格些。
我邊開車邊是是是。
到家里樓下,他們自己上樓了。我回單位去。
晚上回家,稀飯早已做好了,在那里涼著。家里有個老人,生活就是要條當得多。母親又炒了幾個下飯的小菜。這個廚房,才一天,儼然就是她的廚房了。
晚上父親依然喝了點,酒瓶就放在桌上,一開飯,他自己就倒上了。
吃過晚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父親對政治是十分有興趣的,新聞聯播,雷打不動,是要認真看的。
新聞之后,電視里開始放抗日神劇,這時候我母親來勁了,臉湊上電視去看,而父親卻不大在意,他有一搭沒一搭地看著,忽然對我說,你們中秋節、國慶節怎么安排?
我說,沒有安排,還是回老家去吧。
父親想一想說,今年八十歲,是真正的八十歲,去年是虛八十,要是你們回去,你老家的同學、朋友,弄兩桌,怎么樣?平時又多麻煩人家。
我一聽頭皮就麻,去年為他們過八十歲生日,把我們給煩死,又是編紀念冊,又是訂酒席、請客人的,我最煩這些事情。于是我斷然地說,不要,一桌不要,家里人聚聚就可以了。
父親聽我這么一說,把他給噎了回去。他臉色不好,要發作。半天不吱聲,硬忍了下去。
第二天大早,我起床早飯已全部弄好。匆匆忙忙吃完,我拿起包去上班了。
中午回來,吃過中飯,妻子悄悄對我說,你媽媽要逛街,要我帶她去,想買衣服。
我笑起來,人真是的,年紀再大,也還是那個人。母親年輕時愛美,在鄉下,四鄉八鎮的人,認識我媽的都說她長得漂亮。如今老了,還是不能忘,她的腿腳那么不好,走路都是一只棍子,還記得要去逛街,要兒媳婦陪著,給買衣服。
妻子說,不要笑,給錢!你媽買衣服,你給錢。
我沒有辦法,乖乖地掏了一千塊錢。
午休后,我要上班,妻子和我媽要跟我車上街。臨走時,母親對著書房床上躺著的父親大聲說,你在家啊,我和媳婦上街去了。
父親說,去干什么?
母親說,逛逛,能干什么?
父親問,幾點回來?還有事呢!
母親回道:什么事?又小聲嘰咕一句,“和尚道士”。一臉的不屑,
我不吱聲,望著妻子笑。
晚上下班回來,妻子和母親已回來了。母親一臉的滿足,在廚房忙活著。
晚飯父親又喝了兩杯,在桌上說,有幾個老朋友,想去看看,都老了,跑不動了,能看一回是一回了。可是他的幾個老朋友都住得比較遠,他也不認識地方,也只是說說而已。
下午在單位,一個剛去了福建出差的同事,帶回來幾盒鐵觀音,他每個辦公室走走,給發了幾包。我帶回兩包給父親,說,這是好的鐵觀音,你沒事泡泡喝。
父親接過去看了看,又放到了桌子上。
新聞聯播過后,父親無心看電視,他問我,孫女上班有多遠啊?
我說,不遠,和我的路程差不多吧?
又問:叫什么路啊?
我一一說了,并告訴了大致的方位。
之后便無話,他們早早睡下。
又一個早晨,依然是早餐涼得好好的。我們是匆匆忙忙,扒拉幾口趕緊上班去。
中午回來,得到一個重大新聞,父母他們打的到我女兒單位去了。母親說,沒有驚動孫女,我們在大廳和外面看看就走了。之后抱怨父親:神經病啊,人家只要十塊,甩手就給人家二十,你真錢多!
父親說,人家幫你找了。
母親說,幫你問一下就十塊錢啊,錢也太好掙了吧。
父親轉移話題,對孫女說,五個窗口是不是啊。你在最里面的一個窗口。
女兒說,我怎么沒看到你們?
父親笑說,怕影響你的工作,我們看看就走了。
隨后大家休息,父親在書房的床上躺著,門大開著,對著外面的窗子也開著,這樣有穿堂的風。
午睡起來,我輕輕走出臥室,見父親已醒,還在床上躺著,瘦瘦的身體細長細長,他頭對著門,赤著膊,下面穿著件大褲衩,他將大腿蹺在二腿上,手里舉著我給他的那包鐵觀音在反反復復地看,他像研究一個古董一樣,不斷地摩挲著,左看右看。他過去可不是這樣子,在我童年的記憶里,父親總是風風火火,不停地忙工作,他三十多歲就在領導崗位,家里的客人特別多,總是有許多亂七八糟的茶缸和滿地的煙頭。
我輕輕走過他的門口,到衛生間去洗臉,等我洗臉回來,他仍舉著這個紅色包裝的一小袋茶葉,看來看去,像一個孩子在玩著一件心愛的玩具。
我忽然心中一涌,眼睛就有些潮濕。
晚上父親依然喝了兩杯,一切如常了也沒有多少話可說。新聞聯播之后,父親忽然說:明天早上我們走啦。
我吃了一驚,才來兩三天,我花了這么大的精力,專門騰出書房,好讓你們多住些日子。回去也沒什么大事,“癱子掉井里”,回老家不是還是閑著?
我說,才來幾天,不能走。來一趟不容易,不住個十天半月哪成?回家也是坐,在哪兒不是一樣?
父親是說一不二的,我怎么說也不成。他堅持要走,我也沒有辦法。不知是他怕我們生活不方便,打攪了我們,還是自己不習慣,有什么難言之隱,不好說出口。反正他拿定了主意,明天一大早就走。
我無奈,只有服從,于是便到冰箱里拿了兩盒茶葉和一盒寧夏的中寧枸杞籽,包好,放到他們的包里。想想又找出兩瓶酒,用一個袋子裝好。我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又到里面房間,取了一點錢,塞在父親手中。父親客氣了一下,也是象征性的,就塞回口袋里去。這也是父親的變化,過去給他什么東西,他都是一概拒絕,而且態度很壞:不要不要不要……能說上幾十個不要。不知從哪一日開始,他變了,給他什么拿什么(但不主動要),最多是客氣一下。他好像變成弱者了。我成了家長,他倒是小孩似的。
母親在整理我給他們的東西,父親也在收拾自己的一個小包。他邊翻包邊說,我便秘的藥哪?明天上車要吃。
母親大聲說:早上起來就吃,上車吃!哪來的水!
父親問:明天星期幾啊?
母親說,星期幾?星期三吧?什么事?
父親說,沒有事,隨便講講。父親邊往包里塞東西,邊說,明天回家的車子要快些呢!這是規律,——車子想回家呀!
我在客廳沙發上坐著,聽父母你一句我一句的對話,眼淚在眼眶直打轉轉。我忽然站起來說:“早早睡吧,明天還要趕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