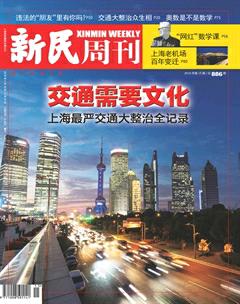路權相爭,誰該讓誰?
劉朝暉
一輛大眾汽車違法并線,妨礙到正常行駛的一輛比亞迪汽車,后者有些惱火,做了反擊舉動。大眾汽車的駕駛者知錯不改,繼續強行并線,結果被撞了個四腳底朝天——一段比亞迪汽車上的行車記錄儀所拍視頻,前不久在網上流傳得很火,也引來爭議無數。
去年10月,濟南一起慘烈的交通事故也引發了激烈討論。事發時,一輛出租車剛剛靠邊停車,騎電動車的女子想從左側超車,但在她超車的一瞬間, 不幸摔倒,被其左側駛來同樣正在超越出租車的公交車后輪碾壓,當場死亡。這種機動車和非機動車混行的現象,在多個城市每天都在上演,也由此引發了不少交通事故,但人車混行的局面并未因為事故的發生而得到改觀。
兩起交通事故的背后,體現的是尖銳的路權矛盾。行人、電動車、自行車、三輪車、汽車……共同使用這些原本已極度透支的公共交通資源。互相之間常常發生路權矛盾。
何為路權,簡單來說,就是交通參與者的權利,是交通參與者根據道路交通法的規定,在道路空間和時間內,在道路進行交通活動的權利和規則。路權又分為上路行駛權、通行權、先行權、占用權。
路權如何分配,不僅是緩解城市擁堵的必答題,更是保障人民群眾安全出行的需要。“中國式過馬路”無視紅綠燈、機動車之間搶道加塞、機動車與非機動車搶道“賽跑”、狹小馬路上劃出的停車泊位擠占了非機動車道、司機亂停亂放把馬路當自家停車場……職能部門為此頭疼,城市形象因此蒙羞。
從表面來看,“有待提高的市民素質”對交通亂象起到了推波助瀾作用,甚至產生發散效應。不過,城市道路是公共資源,各種亂象的真正誘因是公共利益失衡,導致出現“路權之爭”。一個無須爭辯的事實是,城市的道路不可能無限拓寬。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汽車規模裂變式增長,公共交通捉襟見肘。如何調和、破解公共資源的有限與公眾出行需求增長之間的矛盾,事關社會和諧,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路權的重新分配
杭州5·7飆車案的主辦律師,資深交通法領域專家魏勇強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從目前的絕對數據來看,對于道路的使用,非機動車的比例要高過機動車。然而我國在路權規則制定的時候,優先考慮了機動車。隨著經濟發展和機動車數量的爆發式增長,最近10年里,路權爭議逐漸產生而且愈演愈烈。
有專家撰文指出,既往的中國式路權分配過程中,始終存在過分偏向機動車,在機動車中過分偏向小汽車(公車和私家車)的傾向;與此相對,則是行人和自行車、公交車的路權被嚴重擠壓。
當行人和自行車的路權被壓縮到接近極限時,看似占盡先機的小汽車也沒有得到通暢的交通環境。行人闖紅燈、自行車向機動車“借道”,不僅讓機動車不能暢快行駛,也讓整體交通秩序陷入混亂。而因路權分配不合理造成的不公平感,則讓行人和自行車主們即使明知自己違規,依然可以理直氣壯,以致太多交通糾紛,都顯得茫無頭緒且無理可講。
上述路權分配原則雖然不曾被正式提出或闡述,卻貫穿于中國城市交通快速發展的全過程。其造成的結果是,在空間上,小汽車占據了交通干道的絕大部分;公交車則在與身手靈活的小汽車的劣勢競爭中,勉強擠出一席之地。以北京為例,直至1997年設立第一條公交專用道,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自行車、行人不僅無權占用主干道,在輔路上也被擠壓到最低限度。在時間上,過街天橋、地道,雖然實現了人車分流,但行人為此付出的時間卻大大增加。而在一些復雜的平交路口,當紅綠燈的設計分別滿足了機動車的直行、左轉、右轉的需求后,行人需要等待的時間已足夠漫長,而分配給行人的通行時間卻又壓縮到很難從容通過路口。
不少專家提出,“中國式過馬路需要中國式治理”,而中國式治理的重要方面,則是“在重新合理分配路權的基礎上,讓機動車給行人讓出更多的時間,盡量將行人的路口等待時間減少到忍耐極限之內”。路權的重新分配不僅涉及通行時間的分配,亦應涉及道路空間的分配。
經過幾十年發展,路權分配格局已成尾大不掉之勢,重新分配似乎已經無處措手。近年來各大城市紛紛大上地鐵項目,除了拉動經濟的目的之外,納入地下因素,緩解地面路權分配的失衡,也是重要的動因。但無論地鐵如何發展,人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仍然要回到地面。地面路權的再分配,仍然是繞不過去的難題。
優先發展公共交通
如何解決“交通擁堵病”,目前很多城市提出的方案是,大力發展公共交通。據目前全國主要城市的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北上廣及國內其他擁堵相對較嚴重的城市,2016年均推出了相應的解堵方案。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均提出了“公交專用車道”解決方案及軌道交通建設計劃。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居前的十大“堵城”中,北京、上海、廣州均提出了修建或新增公交專用車道這一解決方案。
北京市提出,2016年將增設50公里公交專用道。上海擬在2016年完善綜合交通體系,推行中心城區道路擁堵分級管理,深化公交行業改革,新增140公里公交專用道,優化公交線網,并提出“創建國家公交都市”這一概念。廣州則提出將在今年新增50公里公交專用車道的方案,提高公交車快速通行能力。
重慶交通大學公共交通學者王健認為,無論何種立場和觀點,其實爭奪的焦點只有一個,就是路權。由于道路資源有限,路權究竟誰用,是核心問題。而魏勇強的意見,也是路權要優先傾向于公共交通,包括地鐵、公交車。
以往,公交車的路權被削弱。最后的結果是,一輛載有30-80人的公交車只占用30平方米道路。而最多載客20人的四輛小轎車則占據了40平方米道路。王健認為,只有投建更多的公交專用車道,讓公交車更快、更便捷,乘坐更舒適,且小轎車只有去擠非公交專用車道,公眾才會更多地選擇公交出行,減少自駕出行,從而大幅壓縮上路車輛的數量。
維護“兩個輪子”的路權
在小汽車快速增加之前,中國曾經被稱為“自行車王國”,自行車曾經是多數中國人的主要出行方式。然而曾經的“自行車王國”正在迎接汽車社會的到來,自行車所享有的路權,在小汽車優先的指導原則下,逐漸被擠壓到今天的慘狀。
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在道路資源增長有限的情況下,“四個輪子”總是比“兩個輪子”更強勢,能分到更多的路權蛋糕。在不少城市,自行車道往往被機動車擠壓成了“一線天”,甚至被無故取消,變成汽車停車位,騎車人既要面臨與汽車洪流“貼身肉搏”、“馬路殺手”頻出等安全風險,也難以擺脫停車設施不足帶來的丟車之憂。機動車的“步步緊逼”,正讓自行車一族陷入“無路可走”的窘迫境地。
騎自行車的出行困境,在中國很多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隨著汽車數量的快速增加,從“兩個輪子”到“四個輪子”,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趨勢,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沖突與矛盾。
魏勇強律師指出,現在已經進入汽車時代,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路權問題如何解決,這涉及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國家一直在導向汽車的銷售,但這個導向在達到一定數量時還能產生效果嗎,魏勇強對此持觀望態度。他打了個比方,由于有大量電子支付方式,如今銀行排隊現象已經很少見。現在交通有了滴滴、優步等出行共享運營平臺,隨著發展加快,如果以后有了無人駕駛,還需要這么多的車輛嗎?他認為,現在應該改變之前效率壓過公平的狀況,把公平放在優先的位置。路權是典型的公共資源,路不是政府的,也不是哪一個人的,是全體市民和外地人員所共同擁有的。一個宜居的現代城市,應該為市民提供多種選擇的空間,而不是為了保障一種出行方式,就壓縮其他出行方式的生存空間。
無論是開車還是騎車,都應享有平等的路權。作為公共管理部門,理應合理分配道路資源,注重保障相對弱勢的自行車路權,這才能體現社會公平。在城市規劃、道路分配、交通管理等方面向“四個輪子”傾斜,處處要自行車給汽車“讓路”,不僅忽視了占有相當大比例的人群的正當權益,也會造成整個交通生態的失衡。
自行車不僅未退出公共交通的行列,其實,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提倡,自行車出行正在慢慢復蘇。資料顯示,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40%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車;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37%的職工騎車上班;法國自行車數量為國民數量的兩倍還多。即便作為汽車之國的美國,在加州的戴維斯,也有17%的上班族騎自行車。在國內,在杭州等城市,隨著綠道和公共自行車系統的完善,自行車出行更是成為很多人的選擇。
魏勇強曾向杭州市有關方面提出過將杭州打造成為“全世界著名的自行車的天堂”的建議,他的觀點非常明確,就是優先、傾向于把路權還給非機動車。
從城市治堵的角度來說,陳舊的交通規劃以及私家車的不斷涌現,導致城市擁堵的進一步加劇。治堵的思路有二,一是加大公共交通建設,二是限制私家車出行。無論是發展公共交通,還是從限制私家車,自行車出行無疑都是一種好的補充方案。提倡自行車出行,不僅能減緩交通擁堵,更能減少尾氣排放,對城市的交通治理和環保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科學規劃 全民參與
魏勇強律師認為,要解決好路權相爭的問題,需要從多方面著手,包括城市規劃、交通設施建設、交通管理的手段、交通觀念的普及,汽車文化或道路文化的提升。
他認為,目前國內很多城市的規劃,都是十幾二十年前做出的,已經適應不了現在交通狀況的巨大變化。因此城市在做規劃時,應該具有前瞻性。同時,每個城市的特點都不一樣,切忌照搬照抄,應該根據自身的發展特點來進行規劃。
同時他認為,要解決好路權之爭,車、人、路要三位一體,各司其職,發揮互動關系。而要達到這種良性互動,政府管理是一部分,更多地是要讓全民參與。他表示,汽車時代的汽車文明問題,必須全民參與。在這方面,大量的社區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光靠政府管是管不過來的,食品安全問題如此,交通問題亦是如此。魏勇強還表示,城市交通管理的限摩,限購、限行,都是在特殊時期的一種特殊手段。在管理措施出臺前,應該讓民眾有緩沖期,便于民眾接受。
也有不少專家指出,應該讓讓各個階層和選擇各種出行方式的交通參與者有參與交通決策的討論、決策的機會,使各方的合理權利都得到體現,尤其是讓相對弱勢的行人和自行車主,在討論中享有平等甚至更多的發言權,才不致重蹈上一輪路權分配的覆轍,就有可能形成一種不同于今天的中國式的路權分配原則和模式,中國的城市交通也可能形成一種更合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