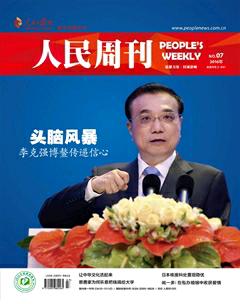打破“僵尸企業(yè)”的僵局
張配豪
在今年兩會(huì)上,“僵尸企業(yè)”成為高頻詞匯。中央提出清理“僵尸企業(yè)”,將從微觀基礎(chǔ)層面推動(dòng)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的調(diào)整。“重組救活為主、破產(chǎn)退出為輔”是處置“僵尸企業(yè)”的基本原則,中央大力推進(jìn)“僵尸企業(yè)”處置工作的目標(biāo)是到2017年末實(shí)現(xiàn)經(jīng)營(yíng)性虧損企業(yè)虧損額顯著下降。2016年,“僵尸企業(yè)”的妥善處置,將成為各級(jí)政府的重要經(jīng)濟(jì)工作之一。
事實(shí)上,長(zhǎng)期以來(lái),各級(jí)政府一直都在推進(jìn)“僵尸企業(yè)”的處置工作,也取得了一些寶貴經(jīng)驗(yàn),但從實(shí)際處置效果看并不理想。目前,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企業(yè)研究所正在就“僵尸企業(yè)”處置問(wèn)題開(kāi)展深入調(diào)研,對(duì)此,記者專訪了國(guó)務(wù)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企業(yè)研究所副所長(zhǎng)袁東明。
《人民周刊》:什么是“僵尸企業(yè)”?目前主要集中在哪些領(lǐng)域?
袁東明:實(shí)際上,“僵尸企業(yè)”的邊界比較模糊,國(guó)內(nèi)外尚沒(méi)有明確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國(guó)外最早提出“僵尸企業(yè)”是指“處于長(zhǎng)期虧損而政府又不得不對(duì)其進(jìn)行保護(hù)和補(bǔ)貼的企業(yè)”。2015年底,國(guó)務(wù)院常務(wù)會(huì)提出“對(duì)持續(xù)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方向的企業(yè)采取資產(chǎn)重組、產(chǎn)權(quán)轉(zhuǎn)讓、關(guān)閉破產(chǎn)等方式予以出清”。
目前我國(guó)煤炭、鋼鐵、有色、礦業(yè)、化工等行業(yè)“僵尸企業(yè)”數(shù)量眾多,那些高度依賴資源性行業(yè)的地區(qū)“僵尸企業(yè)”問(wèn)題尤為突出。作為我國(guó)優(yōu)秀企業(yè)的代表,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業(yè)”也不在少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2012年以來(lái)滬深兩市有多達(dá)266家上市公司扣除非正常損益后,連續(xù)三年虧損,完全依賴政府補(bǔ)助或出售資產(chǎn)粉飾報(bào)表,占上市公司總數(shù)近10%。
《人民周刊》:我國(guó)“僵尸企業(yè)”大體有哪些分類?各有何特點(diǎn)?
袁東明:“僵尸企業(yè)”量大面廣,分布在各個(gè)領(lǐng)域,形成原因也多種多樣。通過(guò)調(diào)研,我們發(fā)現(xiàn)目前我國(guó)“僵尸企業(yè)”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受資質(zhì)保護(hù)但不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企業(yè)。該類企業(yè)的基本特點(diǎn)是:由于行業(yè)有資質(zhì)要求,外面的優(yōu)秀企業(yè)進(jìn)不來(lái),原來(lái)的企業(yè)或依靠資質(zhì)保護(hù)低效生產(chǎn),或通過(guò)出售資質(zhì)來(lái)維持生存,譬如在汽車生產(chǎn)、醫(yī)藥、雜志等行業(yè)都存在這種情況。
第二類是長(zhǎng)期停產(chǎn)且占用社會(huì)資源的企業(yè)。該類企業(yè)的基本特點(diǎn)是:停產(chǎn)一年以上,經(jīng)營(yíng)骨干基本流失,企業(yè)資不抵債;占用土地、房產(chǎn)等資源;債權(quán)債務(wù)關(guān)系復(fù)雜。該類企業(yè)既包括國(guó)有企業(yè)中存在的大量“殼企業(yè)”,也包括民營(yíng)企業(yè)中的“跑路企業(yè)”。過(guò)去幾年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增速放緩,因?yàn)榻?jīng)營(yíng)性虧損而停產(chǎn)的企業(yè)大量增加,在鋼鐵、煤炭、有色、化工等基礎(chǔ)性行業(yè)尤其突出。
第三類是環(huán)保安全不達(dá)標(biāo)而且無(wú)力轉(zhuǎn)型升級(jí)的重化工企業(yè)。該類企業(yè)的基本特點(diǎn)是:負(fù)債率高,有的甚至超過(guò)100%;環(huán)保、安全等方面達(dá)不到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企業(yè)拖欠職工工資、社保費(fèi)用和稅費(fèi);盈利能力弱,無(wú)力轉(zhuǎn)型升級(jí)。
第四類是歷史包袱沉重、連續(xù)虧損的國(guó)有企業(yè)。該類企業(yè)的基本特點(diǎn)是:連續(xù)虧損三年以上;由于企業(yè)辦社會(huì)、兼并虧損企業(yè)等原因背負(fù)沉重的歷史包袱;人員過(guò)多,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遠(yuǎn)低于平均水平;負(fù)債率高,且隱形負(fù)債較重;市場(chǎng)化改革滯后。
《人民周刊》:如果不及時(shí)處置“僵尸企業(yè)”,會(huì)有哪些危害?
袁東明:一是它占用了大量的資金、土地、房產(chǎn)等寶貴的發(fā)展資源,消耗了大量的社會(huì)財(cái)富,卻不產(chǎn)生任何經(jīng)濟(jì)效益;二是它使經(jīng)濟(jì)體系一方面占用資源,另一方面繼續(xù)沉淀資源,造成了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粗放發(fā)展和效率低下,也使得經(jīng)濟(jì)逐漸失去活力;三是它是有可能引起系統(tǒng)性、大面積金融風(fēng)險(xiǎn)。“僵尸”不死,背后靠銀行信貸支撐,又產(chǎn)生了大量的三角債,累積下來(lái)就會(huì)形成巨大的資產(chǎn)泡沫和金融風(fēng)險(xiǎn)因素;四是如果“僵尸企業(yè)”不及時(shí)處置,行業(yè)內(nèi)的優(yōu)秀企業(yè)就得不到足夠的市場(chǎng)份額和市場(chǎng)空間,特別是有的甚至繼續(xù)擴(kuò)大生產(chǎn),不愿退出,就打亂了行業(yè)調(diào)結(jié)構(gòu)、去產(chǎn)能、降虧損的國(guó)家行動(dòng)。
《人民周刊》:明明危害巨大,地方政府又為何愿意為屬地內(nèi)的“僵尸企業(yè)”“續(xù)命”,而不愿其破產(chǎn)退出?
袁東明:首先企業(yè)因經(jīng)營(yíng)不善或其它原因,到了資不抵債的狀況,若讓其由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自動(dòng)破產(chǎn)死亡,則地方政府以前通過(guò)追加投資、稅收優(yōu)惠、低價(jià)土地、信貸扶持等方式給予的前期投入就會(huì)打水漂,無(wú)法收回,相關(guān)責(zé)任官員甚至還會(huì)被追究責(zé)任;另外,這些企業(yè)往往是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有的甚至是地方的支柱企業(yè),為地方做大GDP規(guī)模做了很大貢獻(xiàn),也解決了當(dāng)?shù)卮罅康木蜆I(yè)。破產(chǎn)退出會(huì)導(dǎo)致地方GDP“難看”,同時(shí)勞動(dòng)力轉(zhuǎn)移和再就業(yè)也會(huì)給地方政府帶來(lái)巨大壓力。
《人民周刊》:除政府之外,處置“僵尸企業(yè)”工作還存在著哪些阻力?
袁東明:處置“僵尸企業(yè)”工作確實(shí)存在著很多反面的阻力,還包括:一些企業(yè)主或管理層因擔(dān)心破產(chǎn)審計(jì)和查稅而不愿走司法渠道;銀行等債權(quán)人不愿讓隱形損失顯性化,擔(dān)心影響經(jīng)營(yíng)業(yè)績(jī)或追究決策者的責(zé)任;企業(yè)破產(chǎn)程序復(fù)雜,地方法院受理破產(chǎn)案件的能力有限,目前平均周期在2年左右;土地性質(zhì)不明或者性質(zhì)復(fù)雜,或者缺乏政策依據(jù),處理起來(lái)難度較大;國(guó)有企業(yè)職工安置難度大,主管部門寧愿拖著也不愿“找事”。
《人民周刊》:既然阻力重重,究竟該如何順利推進(jìn)“僵尸企業(yè)”處置工作呢?
袁東明:政府在處置“僵尸企業(yè)”這個(gè)問(wèn)題上,不僅資源有限,能夠發(fā)揮的作用也有限,因此要將更多精力放在健全和完善市場(chǎng)機(jī)制上,解決產(chǎn)生“僵尸企業(yè)”的體制機(jī)制因素。同時(shí),在現(xiàn)階段處置具體企業(yè)時(shí),建議政策對(duì)象適當(dāng)聚焦,針對(duì)不同類型的“僵尸企業(yè)”要有不同的解決思路和方案,尤其要關(guān)注國(guó)有企業(yè)體系中的“僵尸企業(yè)”。
對(duì)受資質(zhì)保護(hù)但不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企業(yè),要從改革行業(yè)管制入手。通過(guò)破除資質(zhì)“終身制”,建立起行業(yè)動(dòng)態(tài)管理機(jī)制,讓“僵尸企業(yè)”退出,讓優(yōu)秀的外部企業(yè)進(jìn)來(lái),形成一個(gè)有進(jìn)有出、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chǎng)。目前,工信部在汽車生產(chǎn)等行業(yè)正在積極推進(jìn)退出機(jī)制。
長(zhǎng)期停產(chǎn)且占用社會(huì)資源的企業(yè),還需要遠(yuǎn)近結(jié)合。近期,建議各地盡快摸排統(tǒng)計(jì)本地區(qū)內(nèi)停產(chǎn)超過(guò)一年且復(fù)產(chǎn)無(wú)望的企業(yè)數(shù)量,由主要領(lǐng)導(dǎo)牽頭,組織地方國(guó)土、勞動(dòng)、法院、銀行等相關(guān)機(jī)構(gòu)協(xié)同配合,集中處理一批停產(chǎn)企業(yè)破產(chǎn)。遠(yuǎn)期,應(yīng)該逐步完善土地、債務(wù)、職工安置、企業(yè)破產(chǎn)等方面的制度,提升政務(wù)能力,提高市場(chǎng)效率。
環(huán)保安全不達(dá)標(biāo)而且無(wú)力轉(zhuǎn)型升級(jí)的重化工企業(yè),解決思路是以破為主。因?yàn)樗谛袠I(yè)嚴(yán)重過(guò)剩,企業(yè)兼并的積極性不高。建議有關(guān)部門嚴(yán)格執(zhí)行國(guó)家環(huán)保法規(guī),有序安排這些企業(yè)破產(chǎn),逐步釋放產(chǎn)能過(guò)剩的風(fēng)險(xiǎn)。
解決歷史包袱沉重、連續(xù)虧損的國(guó)有企業(yè)則有賴于國(guó)有企業(yè)改革的深化。考慮到國(guó)企改革是一項(xiàng)長(zhǎng)期任務(wù),建議近期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國(guó)資管理部門全面梳理監(jiān)管范圍內(nèi)的國(guó)企經(jīng)營(yíng)狀況,列出一批優(yōu)先處理的企業(yè)清單。為防范企業(yè)破產(chǎn)帶來(lái)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地方政府和企業(yè)母公司要通力協(xié)作、密切配合,地方政府尤其是在職工培訓(xùn)、分流安置等方面發(fā)揮作用。中央及地方國(guó)有資本經(jīng)營(yíng)預(yù)算可安排專門資金,用于破產(chǎn)過(guò)程中的職工安置、解決歷史遺留問(wèn)題等方面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