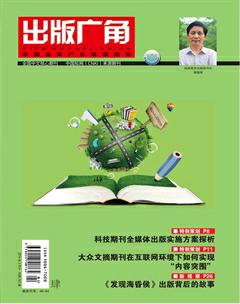出版商與出版家
黃國榮
在出版社年終總結大會上,社長們在年度總結報告中常常會說這樣的話:過去的一年,在全社員工的共同努力下,我社的改革與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業績,出書品種增加了多少,發行碼洋增加了多少,利潤增加了多少,凈資產增加了多少……出版社社長現在大多數是企業家,這么說沒什么不對。但是,評估一家出版企業的業績、實力、優劣,“碼洋利潤論英雄”應該僅是一個方面。
我們的前輩鄒韜奮先生,1926年接手《生活周刊》時,發行量只有2800份,到抗日戰爭爆發時,《生活周刊》的發行量達15.5萬冊。1932年他在上海創辦生活書店,初始原因是刊物屢遭查禁,有了生活書店才能隨時創辦新刊,同時也可以出版圖書。在日軍占領中國的戰亂年代,生活書店發展到全國56家分店的規模。這個業績可謂驚人。但我們可曾研究過,如此業績,他靠的是什么?他又是怎么做的?
《生活周刊》原是一本職業教育刊物,韜奮先生將刊物變臉為新聞述評周報,“就民眾的立場對政府對社會,都以其客觀的、無所偏私的態度,作誠懇的批評或建議,論事論人,以正義為依歸”。他把一本教育刊物“漸漸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和全國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刊物的內容契合了全國人民抗日的愿望,發行量因此創下當時我國雜志發行的最高紀錄。他還親筆給讀者寫了一萬多封回信,回答他們所關心的一切問題,今天還有人會這么做嗎?
韜奮先生堅持把生活書店建成新型的合作社,沒有資本家,大家都是老板,員工也可持股。當時政府不允許搞合作社,只允許股份制。他就堅持注冊是股份制,內部搞合作社。總經理、經理、常務理事都由社員選舉產生,重大事情由全體社員討論通過。用他的話說:“一個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業。”“為著做了編輯,曾經亡命過;為著做了編輯,曾經坐過牢;為著做了編輯,始終不外是個窮光蛋,被靠我過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樂此不疲,自愿‘老死此鄉。”
今天的社長們在做什么呢?
出版是內容產業,出版社是做內容產業的企業,追求規模、碼洋、利潤、凈資產,無可厚非。然而,規模、碼洋、利潤、凈資產僅僅是結果,這些結果要靠現代的經營理念、奮斗的創業精神、過硬的競爭內功、良好的服務宗旨、科學的運營機制來實現。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林爾蔚就發過感慨。他說:“我國出版行業里,商人太多,出版家太少。”他們用十年編一本《日漢詞典》,別人一年兩年就編一本詞典。內容產業,內容是根本,不能只做生意;管理從事內容生產的員工,靠一般的現代公司管理機制未必奏效。出版社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出版的使命是傳承、發揚、創新和繁榮中華民族文化。
出版社社長不能只當出版商,還應該做出版家。有些話應該問問大家,我們發掘、傳承、填補了多少民族文化的空白,培育、開發了多少新的經典選題,扶植、培養、造就了多少優秀的年輕作者,有多少優秀圖書走出國門譯介到了世界各地。
假如只是為了賺錢,當今比從事編輯出版賺錢的事多得很。但有一點需要記住,被社會稱之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職業只有兩個:一個是寫書出書的作家編輯,一個是教師。
人要健康、幸福、有價值地活在世上,需要兩樣東西:一是強健的身體,二是完美的靈魂。強健的身體靠物質食糧來營養,完美的靈魂靠精神食糧來營養。當物質生活有了保障,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人的精神生活需求便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強健的生命,沒有完美的靈魂,活著不過是行尸走肉。就人的生存意義而言,并非只是為了活著,人更渴望活得幸福,活得有意義,活得有價值。人們要實現這一愿望,需要知識、文化、人格與尊嚴。人的靈魂像生命需要物質食糧一樣需要精神食糧來營養滋補。
我們應該珍惜人們獻給我們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美稱,不只做出版商,更努力做出版家,盡心盡責做一生做不完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