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學漢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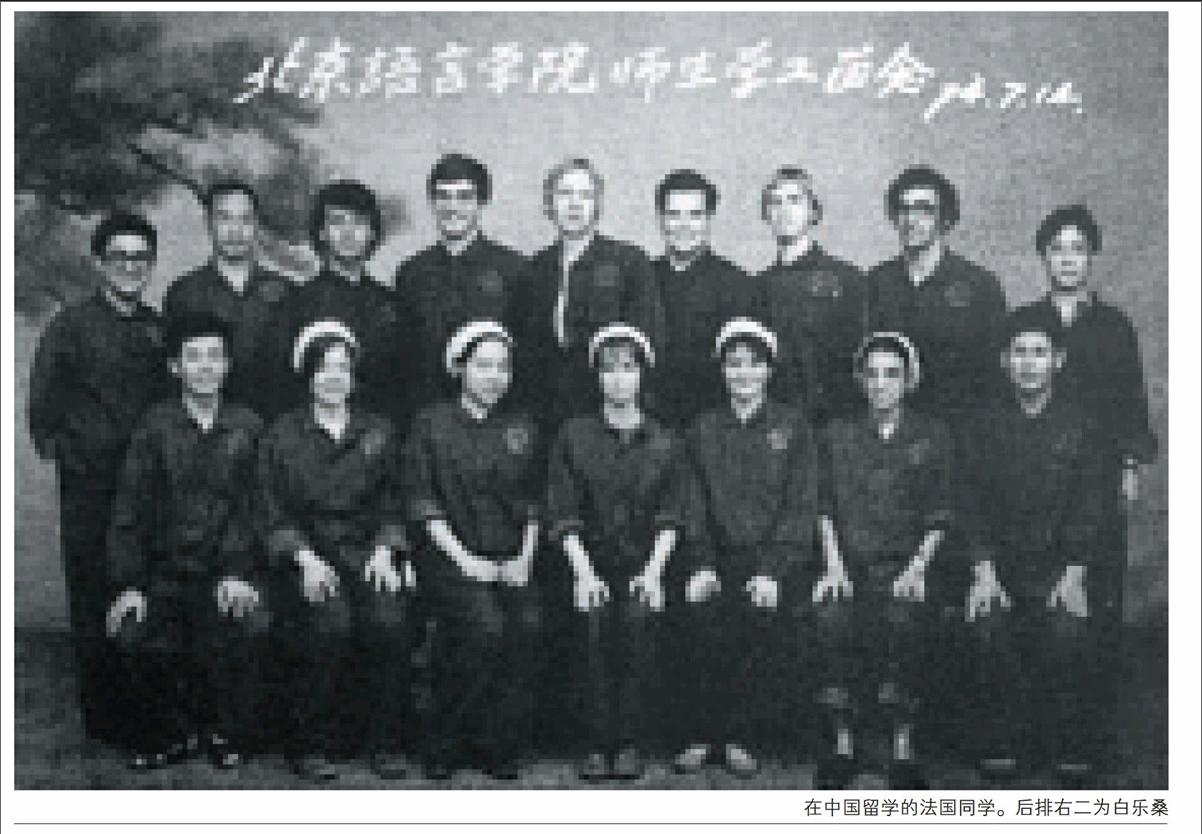

在世界漢語教學界,白樂桑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氣的人,法國國民教育部漢語總督學、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全歐第一位漢語教學法博士生導師、法國漢語教師協(xié)會創(chuàng)始人及首任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但是,在他身上,你看不到這些“官銜”的影子或光環(huán)。他言談是那么平和,待人是那么親切,衣著是那么樸實。如果只聽聲音而不看人的話,就像是同一位普通的中國學者交談。如果只看人不聽聲音的話,就是面對著一位普通的法國學者。但是,在平和之下,我感受到了白樂桑教授思想的深邃、知識的廣博和追求的堅韌。他告訴我,他原本是學哲學的,理性思維是他的長項。此言不虛,思維的縝密和邏輯的嚴謹,貫穿著他講述的始終,恰恰是他如數(shù)家珍似的道出的那一件件小事,鋪就了他人生的成長之路。
幾十年來,我經(jīng)常被問及“為什么學漢語”,而我找到的答案就是:“我學習漢語就是為了有一天,人們問我,您為什么學習漢語。”
有的人追求相近、熟悉,傾向于走向熟路,也有人一直追求踏上陌生的、別人沒有走過的陸地,向往發(fā)現(xiàn)疏遠的境界、新的視野。
“黑腳”的好奇天性
當自己在漢語教學與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甚至有了不小名氣的時候,我也不得不開始對自己進行反思,特別是思考在我一生中被問得最多的問題——你為什么要學漢語?你覺得漢語四聲調(diào)難學嗎?我走上漢語之路的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從個人角度說,我兒時有哪些因素能促使我后來選擇了漢語?這些因素對我選擇漢語和學好漢語甚至起了一些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用法文說,我就是出生在“黑腳”(pieds-noirs)家庭,是一個“黑腳”,對不同的文化有著好奇的和探索的天性。
一般來講,對于“黑腳”的來歷有這樣一種解釋:法軍19世紀30年代在阿爾及利亞登陸的時候,士兵穿的是皮鞋,而當?shù)氐陌⒗耸枪饽_走路。據(jù)說就是根據(jù)這個小小的細節(jié),從法國本土過去的法國人被稱為“黑腳”,意思是穿皮鞋的。
我的爺爺、奶奶、爸爸都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爸爸從事過不少職業(yè),還特別愛好唱歌,不是一般的愛好,特別愛好,而且他的嗓音是非常好的。我為什么指出這一點呢?也是為了回答經(jīng)常有人問我這樣的問題:中文的聲調(diào)那么難學,你有沒有什么好辦法?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常常想起我的父親。
我既是一個法國人,又不是一個正統(tǒng)的法國人。我現(xiàn)在分析,這些因素可能是決定20年以后就開始主修一種莫名其妙的、最遙遠的語言文字,那就是漢語。
1950年,我出生在阿爾及利亞西部奧蘭省(Oran)第二大城市西迪貝勒阿巴斯。
1962年,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我跟隨絕大多數(shù)的“黑腳”離開阿爾及利亞,回到了法國本土。
1968年,我進入巴黎第八大學,主修哲學。
入學的第一年我就知道有一個中文系,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踏上了漢語之路。
當時,在我快結束哲學系一年級學業(yè)的時候,校方發(fā)了一個通知,說從下一年開始,所有學生必須同時主修兩個專業(yè)。于是,我就去注冊西班牙語系,開始一年級的課。但兩三個星期后我做出了一個完全改變我一生的選擇:放棄西班牙語,改去中文系注冊。
放棄西班牙語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對于我來說太容易。是中文系秘書辦公室門上的“中文系”3個字吸引了我。對我來說,這3個漢字太有魅力了,是它們改變了我的一生。
于是,我去中文系敲門。進去之后,秘書問:“你有什么事?”我說我是哲學系的,學校不是要我們主修第二個專業(yè)嗎,我想學一點點中文行不行。他比較幽默地回答:“歡迎,但這個專業(yè)的學生少得可憐,只有6個同學,加上你就7個了。他們已經(jīng)上了兩三個星期的漢語課了。”我說:“那好吧。”就這樣,我開始走上漢語學習之路了。過了一個星期,我就被漢字迷住了。
我的聽覺本來是非常敏感的,可漢字是視覺的東西,這更激發(fā)了我的興趣,因為漢字是陌生的,因為漢字的透明度幾乎是零。如果看英文,因為與法文很相似,很透明,所以我能猜到他的意思。可是,如果不認得漢字,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比如,你會說“謝謝”,可你若沒有學過漢字,“謝謝”這兩個字擺在你的眼前,你都不知道這就是“謝謝”。
正因為透明度幾乎是零,我就很想發(fā)現(xiàn)漢字后邊的境界。所以,我覺得我的發(fā)現(xiàn)精神、挑戰(zhàn)精神都與漢字的神秘有關。其實,在這之前,我對中國幾乎沒有任何了解。
所以,我學習漢語的真正動機就是感到它很神秘,想去弄明白。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剛學過幾十個漢字,馬上就拿《人民日報》或者其他中文報紙看,經(jīng)常坐地鐵坐過站,因為特別想查到我學過的字。
按現(xiàn)在的話,我當時學的是“月球語言”。月球的意思就是說非常遙遠,是不可能去的國家。我沒想過中國會開放,我覺得中國就是封閉的。可無論如何,我對漢語還是入了迷。
入迷到什么程度?我的朋友和同學見到我時都會這樣和我打招呼:“中國人你好!”因為我們見面的時候,我主要對他們講關于中文、關于漢字、關于中國語言等方面的內(nèi)容,很少講我的另一個專業(yè)——哲學。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問我畢業(yè)后打算做什么,我好像是這樣回答的:“我知道學中文可能沒有任何就業(yè)價值,但中文的學士學位畢竟是文科,可以拿這個文科學位在法國教法文。”但是,這到底可行不可行,我當時也不知道。
到中國去留學
每個人在他的一生中總會有幾個時刻是難忘的。對于我來說,第一個難忘的時刻是1973年5月15日下午,大概是下午兩三點鐘。當時我正在學校里,再有一個多月就大學畢業(yè)了,正處在“繼續(xù)學習中文還是就業(yè)”之間的糾結當中。這時我得到了一個消息,中國與法國恢復了文化交流,其中一項主要內(nèi)容就是互派留學生。我們當時對文化交流這個概念不是很清楚,但對中法互派留學生感興趣。我們問學校留學生是否有助學金,他們說有,讓我們趕緊去外交部,領取申請表格。
這一切就發(fā)生在我快要放棄中文的前一個月。于是,我跑到外交部拿了一張表格。我記得,表格中讓我們填寫研究計劃。我們哪有什么研究計劃呀?我都忘了當時到底填了什么,就將表格交給學校了。
中文系的學生人數(shù)雖然很少,但我們也得寫一篇差不多100頁的畢業(yè)論文。當時我對中國的成語典故特別感興趣,于是去找我的兩個同學,希望合作把一本中文的現(xiàn)代漢語成語小詞典譯成法文并加解釋。詞典里共有3000個成語典故,每個人承擔三分之一,先是翻譯,找出與之對應的法文俗語,再對典故加以注釋。我還建議每個人寫一個關于成語的導讀。于是,我們按分工各自動手了。結果,他們沒完成,我完成了。1973年5月,我通過了這1000個成語的論文答辯。
答辯那段時間,我已經(jīng)知道去中國留學的申請已由學校轉(zhuǎn)給了外交部,但申請去中國留學的人還比較多,我是最年輕的。當時還沒有面試,也不知道外交部選擇的標準是什么。但最終我被選上了。
不久,外交部召集入選者開會,負責留學事務的官員向我們介紹了一些有關中國的信息,包括日常生活的信息。開會的時候很有意思,我們認真地記筆記,他們向我們通報了一些比較古怪的信息,有兩個我印象最深。一個是“中國的電壓是110伏”。當時我就想,法國的電壓都是220伏的,電壓不對,我刮胡子怎么辦?結果到中國以后發(fā)現(xiàn),中國的電壓跟法國是一樣的。為什么外交部官員那樣說呢?我后來才知道,只有三里屯使館區(qū)的電壓比較特殊,全中國的電壓都是220伏。另一個是“中國沒有洗發(fā)香波”。我到現(xiàn)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們是從哪兒得到這個消息的。這我們就犯愁了。我們在中國可能要待一年啊,不洗頭怎么行?其實,到北京之后,我第一次到學校周邊的商店轉(zhuǎn)了一圈,發(fā)現(xiàn)中國是有洗頭發(fā)用的東西的。
能到中國留學,我非常激動,隨時做著出發(fā)的準備。1973年的夏天,我休假時都不敢走得太遠,因為不知道什么時間離開法國。8月底,仍然沒有任何消息。到了9月,我去外交部問,負責的官員說:“我們也不知道你們什么時候能去中國,還是等消息吧。”后來我才知道,當時中國正處于“文革”后期,接待外國留學生的各方面都沒有做好準備,北京語言學院剛剛復校。11月初,法國外交部終于傳來消息說,我們11月18日出發(fā)。
那一天是禮拜天,下午4點,我們30個法國留學生乘飛機前往中國。這個時間,或者說北京時間11月19日晚上10點,像是我的第二個生日。從此以后,我的一生才真正與漢語、與中國分不開了。
當時,法國和中國之間沒有直達航線。我們乘坐的航班是巴黎飛往東京的,要經(jīng)停好幾個地方,其中包括北京。航班上只有我們30個法國留學生,沒有其他乘客,更沒有中國人。后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廉價的航班,所以飛機在中途多次經(jīng)停。
經(jīng)過漫長的飛行,飛機終于要降落在北京機場了。很多人激動得不能控制自己,飛機還沒落地就想站起來,想最先看看中國是什么樣子。我便是其中的一個。雖然天已經(jīng)黑了,但我還是想早點看看中國,真有點像是到了月球上的那種感覺。
飛機落地之后,我發(fā)現(xiàn)外面的燈光很暗,附近的路上也沒有燈,更看不見有騎自行車的。下了飛機,我們老遠就看到一幅很大的毛澤東畫像立在那兒。在候機樓等行李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地上有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當天的航班信息。就這么一塊小黑板!這在今天幾乎不可想象。很遺憾,我當時沒有用照相機把它拍下來。這些就是我到北京,或者說到中國后最初的印象。拿到行李出來后,我們見到了北京語言學院派來接我們的老師,然后上了大巴直奔北京語言學院。
幾天后,我在給家里的一封信中寫道:“親愛的父母,我們剛到北京,旅途很辛苦,飛行時間22個小時,估計很快就能進城參觀北京了,這里完全是鄉(xiāng)下。這里很冷,可是天空藍藍的,中國人穿的衣服很合適,所有的衣服都是填了棉花的。”我想特別指出,上世紀70年代,北京語言學院所在的五道口是非常荒涼的。
一步步接近中國語言和文化
1973-1975年,我在中國北京留學兩年。第一年在北京語言學院(現(xiàn)在的北京語言大學)進一步學習中文。第二年在北京大學專修哲學。對我而言,這兩年既漫長又短暫,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許多難以忘懷的記憶。更為重要的是,在提高漢語能力的同時,我一步步接近了原本十分遙遠的中國和中國文化。
在去語言學院的路上,我才意識到來接我們的這位老師一直在講意大利語。我說:“老師,對不起,我們是法國人,不是意大利人。”這位老師說:“我知道,可是意大利語和法語差不多一樣嘛,是不是?學院里沒有足夠的法語老師,所以就派我來接你們了。”我又說:“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多了,我們根本聽不懂。”這些對話在一定程度上讓我更加堅信,這的確是一個在文化和地理上都很遙遠的國度。
到宿舍后,與中國同學的頭幾次對話直到現(xiàn)在我都難忘。我先到對面的水房想洗把臉清醒一下,再喝點水解解渴。這時已經(jīng)很晚了,我在樓道里碰到了一位中國同學,他是學法語的,也住在3樓,正準備去水房旁邊的廁所。見我之后,他主動用法語打招呼:“Bonjour, je vais aux commodities(您好!我要去出恭)……”離開法國24小時之后,等了若干年之后,第一次和中國人近距離接觸,一個中國老師說意大利語,另一個中國同學使用的是路易時代的古法語,也就是只有19世紀文學作品當中才會出現(xiàn)的那種語言。我覺得很好奇。過了一段時間之后,我才明白,這些中國學生學習法語的途經(jīng)只有兩個。一個是法文的《北京周報》,另一個是19世紀法國的小說選本。過了兩三天,我去告訴這位中國同學,法國人上廁所現(xiàn)在不這么說,這樣說很多人可能聽不懂。
他上完廁所出來后,看到我正準備用嘴對著水龍頭喝水,這位“出恭”的中國同學在我后面喊道:“小心,這個水不能喝。”我驚訝地問道:“為什么?”他說:“這是冷水。”我說:“太好了,我正渴著呢,就要喝冷水。”“可是你干嗎要喝涼水呢?”他一臉驚訝地問我,然后說:“到我房間來吧,我給你點兒喝的。”我以為他要請我喝些中國酒什么的,慶祝我們到來。可是,他給我倒在杯子里的卻是冒著熱氣的開水。我還等著他給我加茶葉,但一直沒有。我說:“可是,這是熱水啊。”他說:“對啊,怎么啦?”你可以想象到,我在法國從來沒有聽說過在中國要喝所謂的熱水。當然,現(xiàn)在外國人都知道了中國游客要喝熱水。
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絕不僅僅體現(xiàn)在吃喝的表面上。只不過我們最初到中國的時候,對這些表面上的東西感觸比較強烈而已。后來,我慢慢領悟到更多的是這些表象之下中國文化更深層面的東西。
第一次接受中國老師的邀請去他家里吃飯,還是到中國三四個月之后。邀請我的中國老師一字一句地說:“明天晚上7點到我家‘吃點東西。”他說的這句話有點模糊,是吃一點小吃,還是正經(jīng)吃飯?那個時代中國北方的作息時間和我們法國很不一樣。在北京,吃晚飯的時間大約是17點半到18點,之后也沒有夜生活。邀請我19點去,我想當然地認為這是在晚飯之后了。于是我17點半到食堂吃了晚飯,19點再到老師家吃點小吃就行了。到了老師家,我迅速掃了一眼老師說的“一點東西”。招待我的菜肴已經(jīng)擺在桌子上了,我的天,有餃子、古老肉、牛肉片、芝麻芹菜,等等。這分明是一頓正式的晚飯嘛。打這以后,我開始注意語言背后約定俗成的東西。
第一年的學習結束之后,中國方面告訴我們,誰愿意延長可以再繼續(xù)學一年,也可以回國。后來我才知道,我們法國的30個留學生當中,有18個決定再延長一年,有12個回國了。后來,中法之間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交換生。我就是決定再進修一年的18個人之一。
學文學工又學農(nóng)
第二年,我們繼續(xù)留下來學習的人可以選擇專業(yè),中方根據(jù)報的專業(yè)分配我們到不同的大學。選擇文學專業(yè)的同學被分配到了上海復旦大學,而選擇中文、歷史和哲學專業(yè)的同學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學。來北京大學的同學中,多數(shù)都在中文系和歷史系,我是哲學系唯一的歐洲學生。當時,哲學系是留學生最少的系,除了我以外,還有5個加拿大的,1個坦桑尼亞的,一共7個留學生。
其實,我在巴黎大學中文系讀書的時候,就已經(jīng)知道“北大”這個詞了,知道它有一定的名氣和威望。得知被分配到北大,我有點榮幸的感覺。我還保留著1974年9月13日給家里的一封信,述說自己當時的感受。其中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剛剛成為北大哲學系的學生,不用說,能進入威望這么高的一所大學就讀所選的專業(yè),確實是一種難得的特權。學校滿足了我的要求,我跟一個哲學系的中國學生同住一個房間。北大校園很大,很漂亮,建筑都是中式的,還能品味到這些建筑古樸傳統(tǒng)的氣息。我迫不急待地等著‘十一,據(jù)說會有大型活動。昨天晚上學校特地為我們舉辦了歡迎晚會。我們走進校門,他們按照傳統(tǒng),用鑼鼓的聲音歡迎我們。”
因為留學生很少,我們上的課多半是輔導性質(zhì)的,對我們提高閱讀理解水平確實很有幫助。我當時還沒意識到將來要從事現(xiàn)代漢語教學、研究漢語語言。雖然學了中文,但我對哲學還是很感興趣的。但是,我覺得收獲最大的還是中文水平大幅度提高。當時的課老師都是用中文講,記筆記也是用中文,閱讀的書難度也比較大。這些對我來說,是提高我的漢語語言、文字、閱讀、書寫、聽力、表達的主要媒介。除了輔導課之外,系里有時給我們安排了與一些名人的座談,有的與哲學有關,如馮友蘭講的就是中國哲學問題。也有與哲學無關的,如費孝通講的就是社會學的問題。我印象最深的是《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作的一場講座。在此之前,我已經(jīng)讀過他的書,覺得他的語言很有味道,有農(nóng)村信息。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他的開場白:“我這幾天在農(nóng)村,有人通知我來北大作講座。我沒有做好準備,我只是來拜訪大家的。”聽他這么說,我開始還真以為他沒有做好準備呢,后來聽他講才明白這是客套話。就像準備了一桌子菜的中國人,會客氣地對你說,吃頓便飯。實際情況是,他講得非常有條理,生動有趣,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講座時我還錄了音,后來把他的講座也翻譯成法語并在法國發(fā)表了。
當時,外國人在中國受到限制,出行不是很方便,只有天津?qū)ν鈬耸遣灰S可證的。所以,我們決定到天津玩玩。在天津的大街上,到處都有好奇的當?shù)厝藝覀儯孟袷强赐庑侨恕W羁鋸埖囊淮问侨ヂ尻柭糜危诨疖囌荆覀冞@些留學生曾經(jīng)被街頭上百人看了很久,我還在車窗里向外拍了一張照片。
然而,我們真正走到中國人中間,是當時學校搞開門辦學。這原本是中國學生的專利,沒有留學生什么事。我們是通過某種“抗爭”方式獲得了機會。其中,到工廠去學工,還是在北語的時候。
大約是1974年5月,我們這些外國留學生得到允許,把課堂般到“廣闊的天地中去”,在北京吉普車制造廠實習5天。據(jù)說,學校這樣做是得到了國務院批準的。在這5天中,我們一半時間勞動,一半時間參觀,每個留學生跟學一個工廠師傅。我在信中告訴父母:“我跟你們說我們將會考試,因為毛澤東說過教育要聯(lián)系實際,聯(lián)系日常生活,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課堂。所以,考試是用中文描寫在工廠度過的5天。”
去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生活在一起的愿望是在北京大學讀書的那一年實現(xiàn)的。
第一次去農(nóng)村是在1974年冬天。我們一行15個人,7個留學生、6個中國學生、2個帶隊老師。我們分別住在幾個農(nóng)民家里。第二次是1975年5月,也是北京附近的農(nóng)村。這些村莊盡管離北京不過百十公里,但大多數(shù)村民也是第一次見到外國人。當然,我特別注意觀察,注意與他們交流。直到現(xiàn)在,我還很難忘記當時與農(nóng)民的一些簡單對話。總的來說,他們問問題時話并不多。
兩次在農(nóng)村的6個星期里,我吃、住和勞動都和村民在一起,睡的是火炕。每天早晨6點起床,不吃早餐,先去田地干活。當然,活比較輕松。8點回來,我們跟村民一起吃早餐,多半是棒子面粥。3個星期就吃過一次肉,主要是蔬菜。我在信中對媽媽說:“如果媽媽在中國會很舒服,因為這里頓頓吃蔬菜,連醫(yī)生開方子都可能開的是蔬菜。”
后來,每當我對中國朋友回憶起這段歷史時,他們總是說,你70年代在中國農(nóng)村住多苦啊。我對他們說,哪有什么辛苦,而是太難得了。就像到了月球一樣,簡直太難得了。在中國,我們?nèi)チ送鈬艘话闳ゲ涣说牡胤剑绻S、農(nóng)村。我們特別喜歡觀察,也高興能與普通中國人對話和交流。現(xiàn)在,你隨便問當時留學的法國同學,如貝羅貝,在中國這兩年中最難忘的是什么,他們一定會說在中國的工廠和農(nóng)村。
1975年5月的一天,從農(nóng)村回到北大的第三天,我就收拾行李回國了。
記得離開北京的那天,天氣不錯。學校有人把我送到機場。我注意到,剛來北京的時候在機場里看到的那塊寫滿航班信息的小黑板沒有了。這兩年北京的變化還是很大的。我一個人孤單單地推著那種超市的手推車,一直走到飛機的舷梯下。說實話,離開了已經(jīng)成為自己的一部分的中國文化、中國語言,我有一點難過。
那一班法航飛機上沒有多少人,空姐走到我跟前微笑地打招呼:“你好!”我禮貌地回了一句:“你好!”她又問道:“您在北京住了幾天?”我說住了兩年。空姐嚇了一跳,說:“這怎么可能?”我告訴她我是在北京留學。她又說:“那您給我好好講講中國吧。”看來她不了解我即將離開的這塊土地。但是,因為好像就要離開家鄉(xiāng)一樣,我的心情不是很愉快,所以沒再多說話,只是回答:“好吧,等一會兒講吧。”
飛機滑向跑道,我打開了音樂頻道,戴上耳機。音樂傳來,又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偶然。那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法國歌曲Capri,cest fini(《結束了,佳普利島》),我非常熟悉。它講的是一對戀人在意大利風景如畫的佳普利島上的愛情故事。故事的結局是無奈的。沒想到在離別的時候,剛戴上耳機就聽到歌手唱至那句“結束了”,好像是上帝有意安排的一樣。是啊,我的北京之行真的結束了。心里酸酸的,難以排解。
前面講過,我開始學習中文的時候,朋友們就開玩笑地給我起了“中國人”這個外號。如果我堅持去學西班牙語,會有人叫我“西班牙人”嗎?會有人問我你為什么學西班牙語嗎?肯定不會。我在自己的一本書中的引言中說過,在過去40多年里,我被問得最多的問題,不是“您貴姓”,而是“你為什么學漢語”。我的回答可能會使大多數(shù)人感到驚訝,我說:“我學習漢語就是為了以后能有人問我你為什么學習漢語。”這不是文字游戲,如果仔細思考一番,人們就能品出這個答案的內(nèi)涵。(本文選自《“黑腳”的漢語之路:法國漢語總督學白樂桑口述》,孔寒冰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