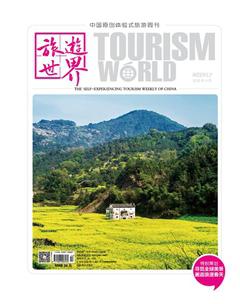宋朝:從—430米到攝影云端的傳奇
孫慧婷
2003年,正逢中法文化交流之春,宋朝的那組中國礦工的人物肖像一經展出便備受矚目,外媒的熱捧引發了國內對“宋朝現象”的關注。一時激起千層浪,稱贊、質疑、機遇等等,都隨之而來。這不得不講講他從-430米的井下到知名攝影家的傳奇故事。
從井下430米開始的人生蛻變
宋朝的叔叔是山東兗礦集團鮑店煤礦子弟學校的美術老師,為了能讓宋朝兄妹三人接受更好一些的教育,自幼就把他們兄妹三人從農村接到身邊讀書生活。叔叔喜歡攝影,上世紀90年代初期,每逢寒暑假都會一個人背上相機和煎餅到全國各地拍照采風,拍回來的135黑白膠片就自己沖洗,宋朝從那時起就幫著叔叔配制黑白藥液,沖洗,印放。叔叔訂閱的各種攝影類報紙也成為他生活中為數不多的課外讀物。這無形中成為了他的攝影啟蒙教育。
為了減輕家庭生活負擔早日參加工作,初中畢業后宋朝上了當地的技校,1997年技校畢業后,他有幸成為了兗州煤礦的一名正式礦工,雖然工作很是辛苦,但每月兩三千的工資收入在當時也足以令人稱羨。六年多的礦工生活,他大部分上早班,也就是每天凌晨4點就得起床準備下井前的系列工作,隨后坐著罐籠車深入地下430米的井下工作面,在礦井開采的最前線,緊隨工程進度每天不斷地向巷道深處掘進,一直到中午12點,才能結束當天的工作上井洗澡,和工友們吃飯喝酒,回家睡覺。
不安分的宋朝對于這種“三點一線” 的生活方式越來越不甘心。隨后便產生了換另一種活法的念頭,直到2001年10月的一天,來自北京的攝影家黑明到兗州礦務局的一個煤礦采訪,在煤礦安監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深入地下800米處工作面,一位隨行檢測瓦斯濃度的礦工的一句話,打破了井下的沉寂:“這是徠卡相機嗎?”年輕人指著那兩臺被黑明貼住了LOGO的徠卡M6相機問道。黑明頓時驚住了,沒想到在昏暗潮濕的礦井下竟然有礦工能認得徠卡,不僅如此,他還順口說出了黑明的代表作《走過青春》。原來他就是宋朝的哥哥,他興奮地撥通了另一座煤礦的電話,宋朝得知消息后感覺在夢里一樣不可思議。隨后,叔叔帶著宋朝前來拜訪這位北京來的攝影家,叔叔希望他能勸勸宋朝留在礦上,踏實本分的工作,珍惜難得“煤飯碗”。而宋朝覺得這是他了解北京的唯一機會。
在隨后幾天中,宋朝哥倆一直陪著黑明采訪,幫他背包為他帶路。臨別前,宋朝兄弟倆請黑明老師吃砂鍋、喝啤酒,并借著酒力宋朝和盤托出了自己的心愿。黑明也看出了他對井外世界的向往,對夢想的熱情。
黑明語重心長地說:“你想闖北京,可以,你靠什么?把你的作品給我看。”一語中的,宋朝當時只是對攝影有個膚淺的認知,毫無作品可言。“那你就從身邊熟悉的礦工開始,對于這個題材,你的礦工身份是別的攝影師所不具備的先天優勢。你要是拍得感覺好的話,一年后我在北京幫你辦個攝影展;否則,你就踏踏實實地繼續下井工作……”這句話直接激勵了年輕的宋朝。
隨后他找出叔叔多年不用的120基輔88相機開始拍攝,由于過于心切,一個月后就背上厚厚的一摞照片匆匆趕到北京拜見黑明老師,回想那次與黑明的見面,宋朝笑著說:“最開始拍得那些照片簡直太肉了。當時黑老師不但沒打擊我的自信心,還親自把我送到火車站,臨別前請我吃飯時他看出了我的失落,并安慰說‘小宋,這次也可能有相機的一部分原因,要不考慮換臺清楚點的相機試試?”
回到礦上以后宋朝和叔叔交流了黑老師的意見,隨后便在叔叔和嬸嬸的幫助支持下湊了兩萬元錢,重返北京直奔五棵松攝影器材城買了一臺仙娜4×5大畫幅相機。然后帶上新買的相機去《中國青年》雜志社見黑明,黑明看到那個沉甸甸的大畫幅箱子,心里雖有幾分吃驚,但更多的是感動于這個山東小伙子的認真和執著……
回到礦上,宋朝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反復試拍、熟悉大畫幅的操作方式及4x5頁片的沖洗方法等系列準備工作……笨重的大畫幅相機及繁瑣的操作方式需要一個固定的拍攝場地和充分的自然光源,于是,便在礦工們出井口外的一片空地上搭建起了簡易的露天攝影棚。早上他跟工友們一起下礦工作,中午從井下打電話問詢井上的天氣和光線情況,若是天公作美,兄弟們便提前幫他備好相機,搭好簡易“攝影棚”,每天上井前臨時約上兩三個工友上井現場拍攝。完事兒后,朋友們再幫他把相機設備及“攝影棚”收起來,宋朝就跟著礦下的工友們一起去洗澡更衣。其實,宋朝之前就經常為工友的家人們拍攝生活照片,原本也算是大家默認的礦區攝影師了,所以每次他招呼大伙兒“走,去照相”,對大家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了。只不過這次他們連梳妝打扮都省略了,100%原生態亮相,從攝影師到模特都是從煤井里現滾爬出來的,滿身黑煤渣,渾然煤油子味。就是這種毫無距離感的關系,礦工們在他的鏡頭前才可能留下毫不拘束,自然流露的各自狀態。后來回看這些《礦工》肖像,也算是攝影史上“濃重”的一筆。
宋朝將第一次用大畫幅拍的樣片寄給黑明時,內心忐忑不安,直到有一天他接到黑明老師的電話:“小宋,這次的片子感覺不錯”之后,2002年的大半年時間里宋朝不定期的帶著新拍的樣片多次往返北京拜訪黑明。后來黑明又帶著宋朝拜見了陳光俊(后來的百年印象畫廊創辦人),陳光俊當時很爽快地也就答應了資助整個展覽的照片制作。就這樣,在黑明和陳光俊及《大眾攝影》等同仁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2002年11月,宋朝的首次個展《礦工》系列肖像作品在北京的《大眾影廊》如期舉辦。黑明兌現了一年前對宋朝的承諾,展覽現場他邀請了很多業內同行好友,其中包括當時的平遙國際攝影節創辦人司蘇實先生和法國策展人阿蘭·朱利安先生。又在阿蘭先生的推薦下,宋朝的《礦工》系列又應邀參加了2003年7月份的34屆法國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直接進入了國際媒體的視野。
2003年,正逢中法文化交流之春,這組中國礦工的人物肖像一經展出便備受矚目,外媒的熱捧引發了國內對“宋朝現象”的關注。一時激起千層浪,稱贊、質疑、機遇等等,都隨之而來。面對別人的評論,宋朝并不介意,他知道這只是意味著來自于不同時代、不同國家,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背景和攝影出發點的攝影師,選擇了相似的拍攝方法與元素,因為技術或手段向來是輔佐于主題的。他說:“我沒有理由回避前輩大師們對自己的影響,藝術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承前繼后的延續過程,只是在這個過正中需要不斷融入屬于自己的東西而逐漸走向成熟。”
我們都是民工
2012年5月宋朝的新作品“Back and Forth”(去與留)在巴黎展出,他這次所拍攝的肖像超越了文化及職業的差異,把觀眾帶到了人性情感的舞臺,再次得到了來自國際攝影界的好評。宋朝的目光始終離不開靠土地最近的人,農民工問題已經是老話常談,他所關注中國人口流動遷徙的現象,并拍攝了一組以“民工和留守”為主題的肖像作品,又一次,將一個簡單卻又難以置信的事實展現在我們面前。一起展出的兩組作品中,《民工》與《留守》相呼應,分別呈現了外出務工者和留守在農村的家人形象。宋朝將平時閑散的時間利用起來,奔波在北京的各大建筑工地,拍攝《民工》,與此同時他萌生了新的想法。有人外出賣力掙錢,就有人在家中孤獨守候。人隔兩地的相思,親不得見的期盼,都是人性最脆弱,最動人的畫面。春節,宋朝陪妻子回廣西老家過年時,他帶著詳細的方案,到縣城周邊的村落拍攝了數十個留守家庭。接下來,他還計劃把拍攝范圍延伸到河南、山東、貴州、四川等地,在畫面中加入更多的地方生活元素。
宋朝說他不希望以純紀實的手法拍攝這組作品。通過他的主觀設計,畫面呈現出另外一種真實,這種真實或許更接近事實的核心。《民工》系列肖像畫面中試圖分別植入少許工地元素,如:腳手架、鋼筋、混凝土、荒草叢等等;相應地,《留守》的系列肖像拍攝過程中,選擇性地將家里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人物主體框取在同一幅畫面里,點到為止。如:曬晾的衣物、壓水機、干枯的盆栽、鐵門和狗等等。同時,將不必要的其它多余元素通過白背景隔離在畫面之外。他說:“嘗試用設計的思維去創作影像。就像寫文章一樣,將事件有選擇地交代清楚,表達到位即可,簡潔的語句往往更有力量。”
到底為何拍攝民工,宋朝想得很透徹,如果把民工的概念擴大,城市中生活的大部分人都可以算在其中。離開家鄉,在城里從事各種職業的人——北漂的、出國的、打工的,包括你,我——拍照片的。他說:“我和父母分居兩地20多年了,至今他們一直都還生活在鄉下老家。”內心無根,生活在懸浮的感覺中很不踏實,現在雖然有了穩定的工作,但對生活的這座城市沒有歸屬感,并時常想念在老家的家人。只有感同身受,才可能拍出真誠的作品,家中的父老鄉親某種意義就成為了他的“留守”者,為他而留,為他而守。
宋朝,以一種寬厚的心態來容納任何非議。心底里存納著知遇恩情,鏡頭下流淌著世間冷暖,他默默地在相機的幕布下注視著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宋朝,肖像攝影師,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作品《礦工》獲20屆全國影展銅獎;曾參加法國“阿爾勒國際攝影節”、瑞士洛桑“愛麗舍”博物館舉辦的首屆“50位新生代攝影師(50 ReGeneration Photographers of Tomorrow)”聯展、“平遙在巴黎”中法文化交流年——巴黎攝影聯展等;作品先后被瑞士“Elysee” 攝影博物館、上海美術館等多家國內外博物館收藏。完成的項目:與“瑪格南圖片社”合作拍攝“中國煤礦”項目;與美國《紐約時報》合作拍攝“中國當代藝術家”系列;與意大利BENETTON公司“FABRICA創意傳播中心”合作拍攝“中國海外移民”項目;與美國《時代周刊》合作拍攝了2009年度人物“中國工人”系列;與法國ALSTOM公司合作拍攝“ALSTOM工人肖像”系列等。
《空巢老人 留守兒童》
一老一小,生命的兩頭最脆弱,需要悉心照顧和呵護;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越來越多
《農民工》
他們是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產物,是我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Q=《旅游世界》 A=宋朝
Q:能否簡單談談你對于攝影的認識和理解?
A:攝影經歷了170多年的發展,傳統銀鹽工藝面臨著被數字影像全面取代的不爭事實,單從技術層面上來看可以說是攝影發展的“改朝換代”。
但無論如何發展,攝影本身畢竟只是一種工具。對于科學家來說,攝影是他進行科學研究的工具;對于一個商業攝影師來講,攝影是他謀取商業利益的工具;對于一個攝影記者來說,攝影是他紀錄報道社會事件的工具;同樣道理,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攝影又是一種個人主觀表達的工具。就這個層面上來講,照相機對于攝影師和畫筆對于畫家,樂器對于音樂家來說具有同樣的作用,特別是在觀念攝影盛起的今天,攝影的工具身份被進一步拓展了。
對于個人而言,想清楚要拿這個工具干什么事兒是首先需要明確的問題。
Q:能否聊聊關于攝影語言的局限性以及潛在的其它可能性?
A:攝影由于具有先天的紀實功能,一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擔負著紀錄歷史的使命。紀實攝影家們通過自己手中的相機拍攝了社會發展中不同時期的各個層面,相應也因此產生了攝影史上眾多不朽的攝影大師,包括羅伯特·卡帕、羅伯特·弗蘭克、卡蒂埃·布勒松及奧古斯特·桑德等等。紀實攝影的生命力也將隨著整個社會的不斷發展而愈加旺盛。但是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段,對于在攝影語言上不斷追求探索的藝術家們來說這是遠遠不夠的。
觀念攝影的發展為攝影語言表達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當觀念藝術家們利用攝影作為工具進行創作時,攝影的藝術地位最終被認可。這樣就不僅僅是拍什么的問題,而是怎么拍、怎么做的問題,從觀念上這種轉變也是革命性的……作為一種載體影像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應該是影像背后的態度,也就是藝術家通過影像想要傳達的某種看法或想要提出的某個問題。某種程度上講,藝術家的觀點和態度比作品本身更重要。
如果將藝術作品比作果子的話,藝術家的態度或觀點就可比作是果樹的根,那么,滋養根的養分便是藝術家生活中所積累的點滴信息和感受……
Q:你的影像可以游離在紀實攝影和藝術創作類攝影之間,很難定性。你怎么理解紀實攝影和自己的創作的?
A:從影像主觀表現的層面上來講,攝影的真正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它對客觀現實的復制再現,更在于藝術家通過這種媒介傳達出自己的態度或觀點并提出問題,但對于是否能最終解決問題則往往需要借助于社會的其它力量。
攝影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段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制約和影響,而借助于數字影像處理技術自然會拓展出諸多可能性,那么這正是年輕的攝影師所要尋求的……
Q:您的作品構圖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作品的畫面布局殘缺而開放,像是用力使畫面向周邊空間擴延。你是如何組織作品中的各種元素,如何決定構圖的?
A:我所理解的攝影構圖應該是根據拍攝主題的需要,通過鏡頭取舍(如:新聞紀實類的拍攝方式)或刻意組織安排(如:觀念影像的創作方式)有效視覺元素的過程。因此,選擇何種構圖方式是由拍攝主題所決定的。猶如文章寫作,一切字句的斟酌表達都是圍繞該文章的中心思想進行,同時盡量做到言簡意賅:能用一句話表達清楚的盡量不用一段話;能用一個詞表達到位的盡量不用一句話等等。那么同樣的道理同樣也適用于攝影構圖,對于表達影響主題不利的視覺元素(或者那些可有可無的視覺元素)盡可能排除在畫面之外。如此才能獲得主題突出有力的畫面效果。
另一方面,我也傾向于將影像畫面中的每一個元素當作不同的詞句,它們的存在也都是為了表達或講述的需要。當然,意料之外的情節懸念或某些不確定的因素更容易給人帶來多意的想象空間。
Q:這些年你為國內外一線媒體拍攝了很多肖像專題,你覺得他們選擇你的原因有哪些?
A:一個人的軌跡總是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而不斷改變。2004年我到電影學院上學,期間由于一個偶然的機會,開始為商業雜志拍攝肖像專題,后來合作的媒體就越來越多,包括《時代周刊》、《紐約時報》、《GQ》等等國際一線媒體。
之前,國外主流媒體很少選擇合作,對于他們來講,我是比較陌生的攝影師。但近年來,隨著中國逐漸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之一,從而對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報道也會越來越多,所以外媒也在努力地尋找中國本土的攝影師來合作,其中也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節約拍攝成本;另一方面,可能本土攝影師更熟悉中國。當然,作品是讓對方認識你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
Q:2009年在美國《時代》周刊年度人物評選結果中,“中國工人”以群體的形式入選而成為當時國內外的熱門話題。能否談談那次你們的合作拍攝經歷?
A:《時代》周刊對于“中國工人”這組題材的拍攝想法源自早期的《礦工》系列肖像,聯系我的編輯比較熟悉我的作品。拍攝的前期準備都是由《時代》的編輯提前完成,包括聯系深圳的一家LED工廠的幾名工人。由于這組工人作品針對的不是人物個體,而是作為中國工人這個大的群體概念而呈現。所以,我并沒有刻意強調人物的個性部分,而是相對客觀地展示了他們的共性特征。編輯也更想強調統一的群體概念。
這群來自深圳的普通工人成為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中國工人的代表,一夜之間,他們的笑容傳遍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