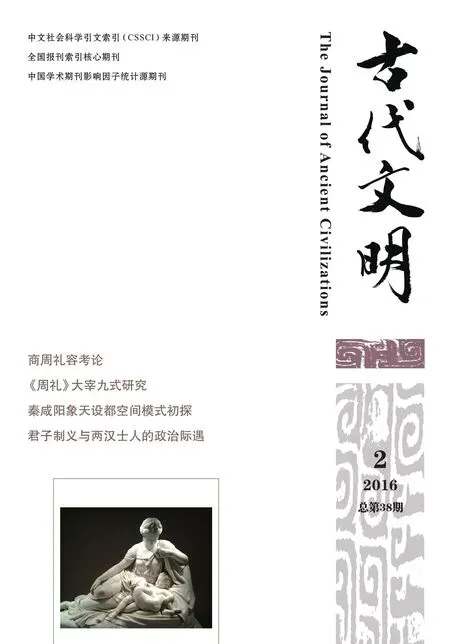由治權到帝國——從拉丁文“帝國”概念的衍生看羅馬人的帝國觀
王 悅
?
由治權到帝國——從拉丁文“帝國”概念的衍生看羅馬人的帝國觀
王 悅
提 要:現代西文中與帝國相關的所有詞匯多出自同一淵源,即古羅馬官員掌握的治權(imperium)。治權概念隨行使范圍的空間擴展而內涵延展,從羅馬官員的權力到皇帝的權力,從羅馬人民的權力到羅馬國家的統治,從區域性的統治到對整個世界的統治。imperium詞義的演變說明了羅馬國家蓬勃的發展態勢,帝國的成長與帝國觀念的更新共同演進。羅馬人在很長時間里體認的是一個權力帝國,這一權力帝國的基礎在于對其他地區和族群行使治權。羅馬人懷揣抱負,相信以軍事手段制服對手才是羅馬立國圖強的最佳出路,這與自蒙森以降視羅馬為防御性帝國的傳統觀點截然不同。
關鍵詞:imperium;權力;帝國;羅馬擴張
羅馬帝國不僅是古代西方世界統治疆域最大﹑延續時間最久的大帝國,更是后世西方人提振民族精神﹑壯大國家實力時常效仿的對象。從查理大帝到俄國沙皇,從近代的西班牙到19世紀末的英國,所有的歐洲帝國都不斷從羅馬帝國獲取榜樣的力量乃至詞匯的力量。古羅馬的許多詞匯和象征成為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國家宣示個人或黨派權威﹑彰顯國家權力的重要來源。正因為近現代對帝國統治采取與古代頗為相似的表達,又因為這些表達詞匯在近代以來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中意義重大,論者多會有意無意地將古代和近代的帝國混為一談,混淆古今帝國的獨特性格。古今觀念差別甚遠,古今帝國分野極大,羅馬帝國有專屬于自己的帝國本質和歷史變遷。1J.S.Richardson,“Imperium Romanum: Empi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81 (1991),pp.1-9; A.Erskine,Roman Imperiali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p.3-5.
羅馬帝國的建立,與傳統上羅馬帝制時代(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的劃分無涉。帝制時代的羅馬帝國無非是在政體上完成了從隱蔽的君主制即元首制向絕對君主制的過渡。但帝國無關乎政體,判定是不是帝國與羅馬是否確立起帝制沒有多少關聯,共和制也不是斷定共和國時代的羅馬不是帝國的理由。歷史學家在談羅馬國家向帝國轉型時,往往強調國家政體結構由共和而帝制的變遷,而實際上羅馬在由皇帝當政之前就已經是一個帝國了。共和國時代的對外戰爭風起云涌,羅馬人在對外戰爭中追逐國家安全與個人榮譽。戰場在古代乃至近代世界永遠是贏得榮耀的主要場合,戰爭最直接的受益者元老貴族,利用身為統治階層的各種便利合法占有或非法侵占國家資財,又通過軍功讓個人聲名顯赫,為家族增光添彩。普羅大眾投身戰爭,抵御外敵,他們也從國家的公眾福利和公共設施中獲益。羅馬在共和國時代已經是一個體量龐大的帝國了。
在拉丁文中,帝國表述為imperium,而且圍繞該詞又產生了一系列與帝國相關的表述。這些表述的演變,恰好見證了羅馬帝國的締造過程,也反映了羅馬人帝國觀念的變化。因此,通過梳理這些表述的語義變遷,可以深刻理解置身其中的羅馬人眼中的帝國樣貌,有助于辨明羅馬帝國的屬性,也會對羅馬“帝國主義”有更清晰的判斷。1“防御性帝國主義”的論點首先在19世紀下半葉由德國學者蒙森提出,20世紀早期經法國學者奧洛(Maurice Holleaux,Rome,la Grèce et les monarchies hellénistiques au IIIe siècle avant J.-C.(273-205),Paris:E.de Boccard,1921)和美國學者騰尼·弗蘭克(T.Frank,Roman Imperialism,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14)的深入論證,成為羅馬史學界的主流觀點。從20世紀70年代起,該觀點卻飽受質疑。著名古代史學者芬利和霍普金斯都駁斥了防御性帝國說,見M.I.Finley,“Empire in the Greco-Roman World”,Greece & Rome,Second Series,Vol.25,No.1 (Apr.,1978),pp.1-15及E.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羅馬史學者哈里斯的論述影響最為深遠(W.V.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他們強調羅馬社會具有濃厚的軍事氛圍,通過戰爭追逐榮譽,通過擴張取得潛在的經濟利益。此后,擴張性帝國主義的觀點在學術界成為主流,幾乎無人再否認羅馬的擴張性。但一直有學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修正,認為羅馬的軍事活動往往是非理性的恐懼心理作祟,或是羅馬人把國家安全擺在與勝利的榮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們在行動上富于侵略性,同時仍堅信是以自身安全為重(J.Rich and G.Shipley eds.,War and Society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3; S.P.Mattern,Rome and the Enemy: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Principat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一、imperium 釋義
現代西方語言中表達“帝國”的詞匯多源自拉丁語imperium,可解作“治權﹑最高權力”。2關于imperium的漢語表述素不統一:如“治權”,見[英]M.I.芬利著,晏紹祥﹑黃洋譯:《古代世界的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諭令”﹑“統治權”﹑“號令權”等,見[德]特奧多爾·蒙森著,李稼年譯,李澍泖校:《羅馬史》(第一至五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2014年;如“治權”﹑“權力”,見[意]朱塞佩·格羅索著,黃風譯:《羅馬法史》,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9年。imperium的詞根來自動詞imperare,意即“指揮﹑命令”。3J.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Rome and the Idea of Empire from the Third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57.imperium是羅馬官員的至高權力,包括軍事指揮權﹑解釋和貫徹法律的權利等。按照古羅馬文獻傳統記載,治權最早屬于統治羅馬的諸王,王的權力簡稱為治權。在最后一位王高傲者塔克文被驅逐后,這一權力轉由共和國的最高行政官員行使。
羅馬歷史上曾握有治權的官員有執政官﹑擁有執政官權的軍事長官(公元前445年—前367年)﹑大法官﹑獨裁官和騎兵長官。治權按其詞根的涵義“指揮﹑命令”,可以看作下命令﹑要求個人聽從的權力,代表著國家在處理與個人關系中的絕對權威,被授予治權的官員代表著國家行使這一權力。后來,治權也由代行執政官和代行大法官等任期延長的官員執掌。他們在擔任執政官和大法官的任期結束時被賦予新的使命,手中的治權也相應延長。羅馬歷史上擁有治權的還有獲得特別指揮權的個人(privati cum imperio)以及一些領有專門使命的人士,如負責土地分配的委員會成員等。
原則上,治權至高無上,實際上受到的制約卻越來越多。共和國初期,王被逐,由兩名被稱為“司法官”(praetor)的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執政官取而代之,他們的權力因為同僚協議和任期一年的規定而受到制約。在民事領域,同一時間內僅一名執政官有獨立行動的能力,另一名執政官的治權和占卜權處于休眠狀態,只有在出面阻止同僚的行動時他的治權才發揮作用。國家處于緊急狀態下,兩名執政官的權力可能同時處于休眠狀態,聽命于一名獨裁官。獨裁官沒有同僚,獲得6個月內的治權,6個月在理論上正是一個作戰周期的時長。上訴權也制約著官員的治權。根據《瓦萊利烏斯法》(lex Valeria,文獻傳統中記載此法曾于公元前509年﹑前449年和前300年多次頒行)的規定,對于官員的判決,公民有權上訴公民大會要求審判(provocatio),官員不經審判不得在羅馬處決公民。也許頒行于公元前2世紀初的《波爾奇烏斯法》(lex Porcia)對《瓦萊利烏斯法》做了進一步延伸,公民的上訴權擴展到羅馬之外,身居國外的羅馬公民可以針對官員的死刑裁判進行上訴。另外,任期延長的代行官員在行使治權方面也受到明確的限制。他們的治權僅能在指定的戰區或行省(provincia)內行使。如無特別批準,一旦步入羅馬城界,其治權自動失效。代行官員的治權往往只在一年內有效,或者至其完成使命時終止。當然,也出現過授予幾年治權的情況,但僅出現在共和國末年,傳統的共和政體趨于瓦解之時。
帝制的開創者屋大維也擁有治權,他曾在公元前43年先后擔任代行大法官和執政官,公元前42年—前33年間是“三頭同盟”之一,公元前31年—前23年為執政官,從公元前27年起擔任多個行省的代行執政官,這些身份都有治權作為堅強基石。公元前23年,他辭去執政官職務成為代行執政官。這時,代行執政官的治權轉變為大治權,不僅可以在羅馬城內行使,而且也囊括意大利。于是,代行官員的治權在羅馬城界內自動失效的規定到此已經廢止。在公元前27年﹑公元前8年﹑公元3年﹑公元13年已獲得“奧古斯都”尊號的屋大維,屢次獲得為期10年的治權;在公元前18年和公元前13年,他還獲得為期5年的治權。也就是說,從公元前27年到奧古斯都辭世時止,他每一年都掌有治權,之前也幾乎連年擁有治權。治權在實際上幾乎成了奧古斯都一人的專屬品,其他人的治權期限和實際權利實難望其項背。1R.Syme,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313-6.皇帝的權力源于治權,治權對皇權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通過在實踐中取消對治權的各種限制,皇帝確立起個人的絕對權威。
治權是古羅馬政治﹑軍事﹑司法領域最重要的概念。前文已經提及其囊括軍事指揮權﹑行政管理權和司法裁判權,涵蓋廣泛。古羅馬史家多把共和國官員的治權看作王權的延續,不可分割的整體,官員在某一領域的職權只是這一絕對權力的具體體現。而現代學者則多把國王的治權和授予官員的權力截然分開,認為后者受到諸多制約,與國王的權力存在著本質區別。譬如在德拉蒙德(A.Drummond)看來,古代作家之所以把共和國官員的治權看作王權的延續,不過是受到希臘政治理論的影響,急于強調羅馬政治發展的連續性而已。然而,不論官員的權力承繼自王權,還是官員的權力遠不及王權,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假定治權從一開始便完整無缺﹑至高無上。他認為,并不存在如此完整統一的治權,所謂明確定義的治權概念完全出于人們的想象,也許直到晚后,當官員離任后治權延長而成為代行官員時,治權才首先被清楚認作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整體。2F.W.Walbank et al.eds.,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ed.,Vol.7,Pt.2,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88-189.
另一位學者貝克(H.Beck)對治權的屬性提出了獨到見解。他對治權的完整性是因還是果沒有直接表明立場,反而獨辟蹊徑地指出兩者之間存在著共通之處。他指出,盡管共和國官員增多似乎使治權的威力較比王權大打折扣,但官職的增加反而強化了治權的普遍性。治權從完全的國王權力演變成為羅馬共和國公民所普遍接受的權力坐標,以此為基礎奠定了具有等級性的共和國政治制度。從前有學者把治權看作從最初完整統一的權力分解出的各項權力,抑或看作隨時間發展不斷充實的統治權,在他看來,雖然這兩種思路并不相容,但其價值在于兩者都相信治權是存在于共和制度中最核心的一種衡量力量。3H.Beck,“Consular Power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the Case of imperium Reconsidered”,in H.Beck et al.eds.,Consuls and Respublica: Holding High Office in th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77-96.各個官職是否擁有治權,或者所擁有的治權權限高低,決定了官員的上下級關系。治權的不斷演變塑造了共和國的權力機制,共和國的政治穩固與發展崛起有賴于這一權力機制的良好運作,羅馬公民也普遍接受治權對國家安定所發揮的突出作用。
在羅馬共和國時代到帝國早期的文獻資料中,對治權至高無上性的稱頌及理想或現實中治權的描繪屢見不鮮。治權之所以深入人心,其原因之一在于其神圣性。治權在實踐中是元老院授予官員的權力,宗教上則是神賦予的權力。羅馬人認為治權來源久遠。在傳說中,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建城之日,羅馬的建立者羅慕路斯進行占卜,由天神朱庇特放送12只禿鷲的鳥占卜象確認了他的權力,此后他的權力在王政時代歷任國王間傳承。治權與占卜權緊密聯系在一起,“國事占卜”(auspicia publica)的傳統一脈相承,事關國家利益的重大行動均需占卜神意,請示神的意旨﹑解釋神的朕兆成為了國王執掌權力以及共和國官員獲得權力的必要條件。1T.Corey Brennan,“Power and Process under the Republican Constitution”,in H.I.Flower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Roman Republi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36-41.
治權貫穿于羅馬歷史發展的始終,從羅馬建城時起便生生不息,它也成為羅馬最為核心的力量。治權至高無上﹑無所不容,行使治權者則大權在握﹑發號施令。但諸如一年任期制﹑同僚協議制和對公民上訴權的保護等措施規定,使得共和國官員的治權必須服膺于共和政制的結構框架,即便擁有繼承自羅馬王權的權力,作為羅馬的公職人員也必須服務于國家和人民。隨著羅馬國內國外形勢的日益復雜,管理事務和統兵之責日益增多,增設新官職在所難免,治權在重要的職能部門中廣泛分布,具有了更為普遍的意義。到帝國早期元首制確立之后,也從未切斷與共和傳統之間的聯系,治權的重要地位無可替代,于是皇帝選擇打破對治權的各種約束,從根本上確立起個人的絕對權威。
治權伴隨著羅馬歷史的變遷而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其演進呈現出共和期與帝國期兩分的特征,折射出兩個時代的本質區別。治權的權限不斷變化,而不變的是治權在羅馬國家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長期的發展演變中,治權觀念深入人心,每個羅馬人都深知治權重大而神圣,擁有治權意味著可以在國家的軍政舞臺上大展拳腳,懷揣仕途抱負的羅馬人無不把擔任握有治權的高級官員作為奮斗目標。擁有治權并擔任高級官職是個人乃至其家族的無上榮耀,是個人積累政治資本的絕好機會。擁有治權的軍事將領馳騁沙場﹑建立戰功,也為羅馬開疆拓土﹑建立廣闊帝國開辟了道路。
二、帝國觀念的衍生
imperium本指官員所行使的權力,而由官員行使權力的空間范疇視之,它又具有了地域空間的內涵,所反映的是治權在不同地理范圍內的實踐。古代文獻提及治權時常加一限定語“domimilitiaeque”(國內的和戰場的),將治權分為國內治權和軍事治權兩類。在羅馬城內行國內治權,在羅馬城外行軍事治權,由此可見治權在民事領域與軍事領域并置的特點。此即治權在空間上最基本的對分。然而,這種將治權按行使區域一分為二的傳統做法近來受到某些學者的挑戰。德羅古拉(Fred K.Drogula)認為,在正常情況下治權并不存在于城界之內,沒有國內治權一說,治權純屬外向型的軍權,軍事性是治權的惟一屬性。2Fred K.Drogula,“Imperium,Potestas,and the Pomerium in the Roman Republic”,Historia,Bd.56,H.4(2007),pp.419-452.這一解釋凸顯了治權在羅馬崛起中釋放的軍事能量,在實踐中統兵權是治權最重要的體現。銜領治權的官員在經庫里亞權力法批準后,穿過羅馬城的神圣邊界,成為統帥。隨著與外邦戰事的展開,也治權行于國外。統兵權與將領停駐地之間建立起關聯是治權在實踐中的突出特征,甚至在廣義上成為羅馬號令世界的反映。3H.Beck,“Consular Power and the Roman Constitution: the Case of imperium Reconsidered”,pp.91-4.
自公元前3世紀,羅馬已跨出意大利半島,通過戰爭在海外拓展霸權,官員下達命令和使人服從的治權也擴展到海外。4“在53年時間里,羅馬權力取得進展。羅馬的權力現在已被世界接受,所有人必須服從羅馬人,聽從他們的命令”,見Plb.,3.4.2-3,in Polybius,Vol.II,trans.by W.R.Pa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蓬勃發展并最終確立,在該時期imperium的用法也經歷變化,涵義延展,出現與之聯用的新詞匯。imperium的詞義隨歷史發展沿著兩條軌跡演變,一是本義,即羅馬官員的權力,該詞的基本用法保持不變,表示官員權力的內涵一直沿用到帝國時代;5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Rome and the Idea of Empire from the ThirdCentury BC to the Second Century AD,p.44.再則是新衍生出的空間涵義——imperium行使的空間即為羅馬帝國。
追溯帝國一詞的用法,需參照官方文獻以及修辭學讀本中該詞的使用情況。在實際使用中,該詞還出現在異族和文學的語境中,尚有其他內涵。在這里,本文僅就對羅馬崛起至關重要的政治軍事內涵加以討論。雖然imperium涵義演變的情況頗為復雜,既有意涵上的差別,也有時間上的交錯,但從對其各類用法的梳理中可以獲知其涵義演變的大體趨向。
Imperium的空間內涵出現于海外行使治權之后。羅馬帝國的官方表述首見于公元前2世紀60年代羅馬與色雷斯的馬羅涅亞(Maronea)簽訂的條約,條約文本為希臘文,上面提到了“羅馬人和他們治下的人”;這一概念的拉丁語表述見于羅馬與卡拉提斯(Callatis)有關黑海的條約,“羅馬人民和在他們治下的人民”([...Poplo Rom] anoquei[ve] sub inperio [eiuserunt ...])。1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edi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751-752,“imperium”辭條。這些異族被置于羅馬的治權之下,意味著羅馬實現了對相關地區的統治。公元前167年,在一次元老院演講中,老加圖為羅馬與馬其頓國王佩爾修斯交戰時羅德島人的行為辯解,他稱羅德島人不想見到羅馬人完全打敗佩爾修斯,因為害怕“處在我們獨一無二的治權之下(sub solo imperionostro)”。2AulusGellius,The Attic Nights,3.6.16,in Aulus Gellius,Attic Nights,Vol.I,trans.by J.C.Rolf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54.在這里,“我們的治權”指的是羅馬人民的權力,此處羅馬人民的權力等同于羅馬的統治,因為羅馬可以簡稱為“SPQR”(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為羅馬元老院和羅馬人民,羅馬人民的權力也就可以理解為羅馬國家的權力或羅馬國家的統治。鑒于治權是羅馬國家要求羅馬人民服從的權力,羅馬人民的權力也便可以看成羅馬人民要求外族服從的權力,即對外族的統治權。
前文提及imperium已具有“羅馬人民的權力”的內涵,但“羅馬人民”與“治權”兩個拉丁單詞連用的短語imperium populi Romani,直到公元前1世紀初才在拉丁文獻中出現,首見于公元前1世紀80年代的修辭學作品中。在這篇托名西塞羅所作的修辭學作品中提到:“誰會相信,有人會如此愚蠢,打算不依靠軍隊來挑戰羅馬人民的權力?”3Cicero,Rhetorica ad Herennium,4.13,in Cicero,Vol.I,trans.by H.Capla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260.此處“羅馬人民的權力”仍遵循前文提及的用法,指羅馬對外族的統治權,挑戰羅馬人民的權力意味著挑戰羅馬的統治。另外,這本書里還有一個劃時代的用法,不僅把羅馬人民的權力指向其他地域和民族,而且涵蓋整個世界:“所有族群﹑國王﹑國家一方面出于武力強迫﹑一方面出于自愿,都接受羅馬對整個世界的統治,當世界或被羅馬的軍隊或被羅馬的寬厚征服時,讓人不大相信的是,有人會以孱弱之力取而代之?”4Cicero,Rhetorica ad Herennium,4.13,in Cicero,Vol.I,p.258.羅馬依恃軍威和外交政策所向披靡,所有國家都服膺于羅馬,羅馬的統治不限于一方之地,廣納整個世界。當然,這里提到的“世界”是指羅馬人居住其間的整個地中海世界。西塞羅在另一段演說詞中同樣表達出羅馬統治世界的態勢。他提到了獨裁官蘇拉,稱蘇拉是共和國惟一的統治者,統治著全世界,并以法律鞏固了通過戰爭恢復的偉大權力。5Cicero,Pro Sexto Roscio Amerino,131,in Cicero,Vol.VI,trans.by J.H.Frees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38.在西塞羅的演說詞里,有大量把羅馬人民的權力延伸到全世界的表達。這些用法絕大多數屬于抽象意義上的,而西塞羅惟一一處可能是對羅馬人民的權力擴大到世界之邊的實指,見于《論共和國》篇末的西庇阿之夢。在夢境中,小西庇阿被已故的養祖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引領上天,在繁星蒼穹下,他既欣喜又不安。星空廣瀚﹑地球渺小,他為羅馬的統治(imperium nostri,直譯為“我們的統治”)感到遺憾,因為那觸碰到的只是世界的一小塊。6Cicero,De Re Publica.,6.16,in Cicero,Vol XVI,trans.by C.W.Key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68.這無疑暗示了羅馬人對統治廣闊世界的無限憧憬。這種宣稱羅馬統治世界的表達方式在公元前1世紀首次出現,此時對imperium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官員的權力抑或羅馬人民的權力,而是羅馬對世界的統治和世界性帝國。在共和國末葉,關于羅馬的權力無遠弗屆的認識已經司空見慣。1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p.56.
現今可見的資料呈現出imperium語義發展的整體趨勢:直到公元前2世紀末,該詞在官方文本中最主要的用法一直是賦予官員的權力;到公元前1世紀,該詞的涵義更為寬泛靈活,官員權力之意仍廣為使用,新見短語imperium populi Romani也用以指代羅馬人民對他者的權力和統治,這種權力被看成世界性的權力,可以控制整個世界,近似于orbis terrarum(意為世界)的用法。盡管imperium的詞義演變仍表現在權力擴展上,但已有空間意義的構想,認為羅馬的權力無遠弗屆,即將羅馬想象為一個無邊無際的世界帝國。此時imperium的領土意涵尚不明確,但隨著羅馬世界的擴展和時人對這個世界認識的加深,imperium增添了某種“帝國”的涵義。這一涵義后來也愈發確切,逐漸具有了領土國家的意味,最高權力演變為權力運行的地域,成了領土意義上的帝國。2Andrew Lintott,“What was the ‘Imperium Romanum’?”,Greece & Rome,2nd Series,Vol.28,No.1(Apr.,1981),pp.53-67.
羅馬史家李維敘述稱,“公元前191年在亞細亞,不久后將發生安條克與羅馬人在陸上和海上的戰爭,要么正在尋求統治世界的羅馬人失手,要么安條克失去自己的王國”。3Livy,Ab Urbe Condita,36.41.5,in Livy,Vol.X,trans.by E.T.Sag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274.另一處,“路奇烏斯·西庇阿曾征服世上最富庶的王國,將羅馬人民的權力擴展到陸地最遠的邊際”。4Livy,Ab Urbe Condita,38.60.5-6,in Livy,Vol.XI,trans.by E.T.Sag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08.從中可以看出,此時的羅馬已經放眼世界,尋求世界性的統治。這也是公元前1世紀下半葉的文獻中對羅馬統治的普遍用法。李維在另一處還記載,“安條克致信比提尼亞國王普魯西亞斯,信中抱怨稱,羅馬人正在前來亞細亞的途中,他們是來摧毀所有的王國,以便世上除了羅馬帝國(Romanum imperium),其他帝國蕩然無存”。5Livy,Ab Urbe Condita,37.25.4-7,in Livy,Vol.X,p.362.此處,Romanum imperium的地域意義十分明確,因此理解為羅馬帝國更為妥當。李維指出,羅馬已經有了統治世界的抱負,愿將羅馬的統治擴展到世界之邊,他們的目標是摧毀所有帝國,唯我獨尊。生活在共和與帝制之交的李維雖在追述古人言論,反映的卻是同時代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人們的普遍想法。因此,可以說,最遲從公元1世紀起imperium Romanum已由羅馬的權力引申為羅馬的帝國,成為了羅馬帝國的指稱。老普林尼和塔西佗的著作都使用了imperium Romanum一詞。老普林尼在描述美索不達米亞時說:“特巴塔(Thebata)和從前一樣仍在原位,這個地方也同樣標示出在龐培領導之下羅馬帝國的(Romani imperi)邊界”。6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6.30.120,in Pliny,Vol.II,trans.by H.Rackham,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28.塔西佗稱“巴塔維人(Batavi)曾是卡提人(Chatti)的一個部落,他們由于自身發展渡過河,那將使他們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pars Romani imperii)”。7Tacitus,Germania,29.1,in Tacitus,Vol.I,trans.by M.Hut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74.這兩處,imperium指代的無疑是領土意義上的帝國。
帝制時代前后,在羅馬人心目中,羅馬的統治區域無邊無際。公元前75年,羅馬的錢幣已鑄上權杖﹑地球﹑花環和舵的圖像,象征羅馬的權力散布到全世界的陸地與海洋,象征著沒有邊界的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掌權時,“帝國”(imperium)的概念已與“世界”(orbis terrarum)的所指別無二致。1世紀的羅馬政治家﹑哲學家塞內加寫道:“我們應該認識到有兩個國家,其中之一是廣闊而真正公眾的國家,神與人被懷抱其中,我們看不到它的這一端,也看不到那一端,但可以用太陽來丈量我們公民的邊際。”8Seneca,De Otio,4.1,in Seneca,Moral Essays,Vol.II,trans.by J.W.Basore,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86.2世紀,皇帝安敦尼·庇護接受“全世界的主人”(dominus totius orbis)的徽號,鼎盛時期的羅馬延續著羅馬人主宰世界的夢想。
羅馬形成帝國的領土空間概念較晚,原因之一可能在于羅馬人的思維方式與希臘人一樣,多談民族,少談地區。這種思考方式使得他們對權力帝國的理解早于對領土帝國的理解。相較于建立領土意義上的帝國,使外族外民受制于羅馬的權力,服從于羅馬的統治,才是羅馬人真正關心的問題。有時候,在迻譯拉丁文的過程中,對民族而非地域的考量往往會被忽略,用一個地名取代一個民族的名稱,統治一個民族被譯作統治一個地區,實際上在微妙處曲解了古人思考國家及國際關系的方式。比如羅馬統治希臘人截然不同于羅馬統治希臘,前者表示希臘人對羅馬人的服從關系,后者則加入了不見于早期拉丁語的領土和地理緯度。1Andrew Erskine,Roman Imperiali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6.
在imperium詞意拓展的過程中,還涉及一個重要的詞匯provincia,英文中行省(province)一詞由此而來。provincia起初為元老院分配給下年度掌握治權者的職責。由元老院分配官員職責的慣例一直延續到奧古斯都時期。到公元前1世紀初,provincia已具有了地理上的隱含意義,指代指揮官行使治權的作戰區域,即戰時官員行使強制性治權的地區,此后又演變為帝國海外領地的行政單位——行省。2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p.49;J.S.Richardson,Hispaniae: Spain and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218-82 B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3-10以西班牙行省為例,從其建立過程說明provincia內涵的變遷。從官員的職責到行政制度,provincia也同樣經歷了類似imperium的涵義變遷。provincia的本意不是治理國家的行政管理方式,而是對擁有治權者職責的界定。元老院往往將據信對羅馬安全構成威脅的地區連年指定為戰區,指派擁有治權的官員赴任。3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pp.15-17.元老院在戰區的擇定上具有主動權,在每個任職年的年初指定戰區,分派握有治權的官員。倘若元老院確有拓展邊疆的意圖,則焦點在于擴展個人的治權及所在戰場或行省的治權行使上。4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pp.43-45.在連年作為戰區或是羅馬的權力想要在此牢固扎根﹑常態化管理的地方,漸漸設立起管理政府和行省總督,行省的建制漸趨成熟。
與imperium相關的各個詞義有時疊加,有時混用,但這些詞義都在不斷豐富和細化,新衍生出的詞義沒有取代古老的涵義,各個詞義雜糅并存。從羅馬官員的權力到皇帝的權力,從羅馬人民的權力到國家的統治權,從對其他民族和地域的統治到對整個世界的統治,imperium詞義的演變說明了羅馬在地中海世界大展拳腳的蓬勃態勢,這種擴張態勢使羅馬人的國家觀念不斷更新。不論稱霸地中海所催生的帝國觀念,還是羅馬早在建立之初就具有尚武好勝的民族雄心,帝國的不斷成長與帝國觀念的更新這兩個因素相互作用,使羅馬人懷揣世界性抱負不斷擴張帝國。從權力到統治,再到統治的地域,imperium詞義的變遷見證了羅馬的帝國成長,更激發著羅馬人向遠方進發。有歷史進程中的羅馬帝國,也有羅馬人想象中的帝國,二者共同成長。
三、羅馬“帝國主義”
盡管“帝國主義”首先用于描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列強的殖民帝國,但該詞現在也經常出現于羅馬征服意大利及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世紀羅馬建立地中海帝國和歐洲帝國的語境中。
在共和國早期和中期(公元前5世紀—前2世紀),羅馬是一個軍事性社會,官員的權力具有突出的軍事特征。在仕途起步期,需列身行伍十年,1“除非已經完成十年的服役期,否則沒有人獲準擔任政治職務”,見Polybius,The Histories,6.19.4,in Polybius,Vol.I,trans.by W.R.Pat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310。惟有在戰場上樹立卓越功勛才能贏得凱旋式的殊榮。公元前5世紀和前4世紀早期,羅馬與埃魁人﹑沃爾斯奇人及埃特魯里亞人交戰;前4世紀中期與拉丁人和坎帕尼亞人交戰,并與薩謨奈人和南部意大利人交戰;之后波河以南意大利的絕大部分地區被羅馬控制。一些共同體融入羅馬人民中,余者被歸入同盟者,有義務提供軍事援助。所有納入羅馬控制的意大利地區中,唯有具有羅馬公民權的地區可以恰如其分地稱為羅馬國家的一部分。
在兩次布匿戰爭期間(公元前264—前241年和公元前218—前202年),羅馬在同盟者的支持下經過海外戰事,建立了意大利之外的羅馬帝國。羅馬的將領由元老院授以兵權,分駐海外戰區。這種戰區主要不是領土意義上的,也不是永久性的,但在想要通過駐軍落實長期控制的地方,元老院定期指定戰區或行省。公元前2世紀上半葉,在與地中海東部的希臘化國家交戰的背景之下,羅馬帝國采取了不同的統治形式,不直接設立行省,而是遠程遙控。在戰事結束時,羅馬沒有在這里建立長期的行省,而是通過條約和外交手段,以一種遠程的方式對這些地區加以控制。對于在公元前2世紀下半葉撰寫《通史》的波利比烏斯來說,這代表著羅馬霸權從地中海西部擴展到地中海東部,世界服從于羅馬,“誰會無動于衷或是不想知道羅馬人在不到53年的時間里,以何種方式并以何種政治制度使幾乎整個人居的世界服從于羅馬一個政府?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事。誰會興致勃勃于其他的場景或研究,而認為有比獲得這一知識更偉大的時刻?”2Polybius,The Histories,1.1.5-6,in Polybius,Vol.I,trans.by W.R.Paton,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pp.2-4.盡管在自稱佩爾修斯之子的安德里斯庫斯(Andriscus)奪取馬其頓王位的嘗試失敗后,馬其頓在公元前149年才成為一個長期的行省,而在波利比烏斯看來,羅馬人對地中海東部的統治與對地中海西部更為直接的統治相差無幾。
在公元前1世紀,龐培打敗本都的密特里達提六世(公元前66—前62年),之后平定東方,吞并了大片領土,凱撒在高盧征戰(公元前58—前49年)也兼并了廣闊領土。奧古斯都統治時期,他不僅完成了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也增設了沿多瑙河一線的新行省萊提亞﹑諾里庫姆﹑潘諾尼亞和默西亞。只是因為公元9年瓦魯斯在日耳曼前線的慘敗,才停止了進一步征服萊茵河和易北河之間的日耳曼地區的腳步。此后除了克勞狄在公元42年征服不列顛南部,惟有圖拉真一人在97年—117年間開疆拓土,其繼承人哈德良又回歸戰略守勢。
羅馬帝國主義的圖景十分清晰,從臺伯河邊的小邦逐步發展為地中海帝國和歐洲帝國,但羅馬人的擴張動機卻是一個聚訟紛紜的話題。自蒙森以來,人們相信羅馬人的擴張目的主要是防御性的,只是偶然成了擴張主義者。現代學者則駁斥該觀點,認為有其他的動機,包括對經濟收益和領土擴張的期望等。3參見第14頁注釋1。羅馬帝國建立過程異常復雜,也許任何單一的解釋都不會是全然正確的。
就分析羅馬擴張的實質而言,從擴張結果出發要比從動機出發更切合實際。譬如,公元前264年羅馬入侵西西里,是羅馬擴張歷史中的重要轉折點。不管羅馬元老的預期目標如何,這都引發了羅馬與迦太基的首場戰爭,此后,羅馬邁開了建立海外帝國的步伐。羅馬邁出這一步的動機難以捉摸,元老院表現得左右為難﹑遲疑不決。波利比烏斯的史書從該時期開始記載,整部史書都有一個先入之見,認為羅馬早已把統治世界當做自己的奮斗目標。“無論統治者自身還是評論他們的人士都不會把行為的結束僅僅看作征服或使他人屈服于自己的統治,因為有識之人不會僅僅為了打敗一個對手而與他的鄰居為敵,就像沒有人漂洋過海就只為渡過海洋。事實上甚至沒有人僅僅為了學知識而從事藝術技藝的研究,所有人做事情都是為了取得快樂﹑好處或用途”。4Polybius,The Histories,3.4.10-11,in Polybius,Vol.II,p.12.羅馬的征服舉動背后一定隱藏著明確的動機。雖然,在敘述羅馬猶豫是否出兵墨西拿時波利比烏斯也會犯難,但他從不懷疑羅馬創建首個海外行省是入侵西西里的重要結果,羅馬善于利用戰爭帶來的豐厚收益。
此后數世紀中,西西里行省給羅馬帶來諸多收益。西塞羅在狀告西西里前任總督維列斯(Gaius Verres)時指明西西里行省的重要地位:“西西里是第一個成為羅馬忠誠朋友的海外國家,第一個得到行省之名者,帝國王冠的第一枚寶石,第一次教會我們的祖先統治外族是件大好事”。1Cicero,Against Verres,2.2,in Cicero,Vol.VII,trans.by L.H.G.Greenwood,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96.統治外族﹑建立世界帝國使羅馬獲益良多,無論第一步的動機為何,羅馬抓住時機加以利用,卓有成效地取得進展,這正是西塞羅所說的好事。
第一次布匿戰爭戰后的3年間,羅馬又攫取了撒丁島。撒丁島和西西里被納入羅馬掌握后,被要求每年向羅馬交付貢金,接受羅馬官員,容許羅馬在當地建立至少一個海軍基地。羅馬在拓展治權行使區域和管理海外屬地方面踏出了重要一步。從重組意大利所采用的同盟制度到未來的行省制度,面對局勢的變化,羅馬靈活應對。不管羅馬是否早已預見到帝國的益處,他們在軍事行動上無疑毫不妥協,當機會出現時,他們絕不放過。
公元前264年后的兩個世紀中,和平變得異常珍貴,沒有超過十年的和平時期。就參戰人員而言,據布倫特(P.A.Brunt)估算,從漢尼拔戰爭到第三次馬其頓戰爭的半個世紀中,約有10%甚至更多的意大利成年男性年復一年地投身戰場,2參見P.A.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C- AD 1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425,公元前200年—前168年意大利陸海軍人數圖表。E.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Vol.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4.這一比率在公元前1世紀增加到每3名男性中就有1人置身戰場。當時士兵入伍沒有規定的服役年限,一場戰事延續多久,他們就要服役多久。軍隊的規模也根據戰事的危急程度而有變動。公元前2世紀早期,所有公民中有超過一半的人在軍中平均服役7年。3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p.30.共和國最后兩個世紀戰事連年,這時,羅馬公民列身行伍的比例頗高,服役時間在前工業時代的所有國家中也是最長的。4Hopkins,Conquerors and Slaves,p.11.這些都說明在對外戰爭的問題上,絕大多數羅馬人表示贊同,文獻中也鮮見反對意見,即使偶有異議,也只存在于戰略戰術等細枝末節上,而不是對戰爭的合理性存有異議,他們覺得以武力建立帝國理所應當。
羅馬史學起步于公元前3世紀末,中期共和國的文獻資料相對匱乏。由于文獻資料付諸闕如,無法根據同時代的相關論述分析當時羅馬人的帝國觀。但由全民動員﹑同仇敵愾視之,羅馬人的擴張精神是毋庸置疑的。這些鮮活的事實比文字論述更具說服力,更利于洞察羅馬人對國家擴張的支持程度。羅馬社會各階層都決心讓其他國家服從羅馬的統治,他們認為對周邊地區的控制才是羅馬圖存強大的最佳途徑。羅馬的戰事之所以曠日持久,就在于民眾的堅持,在于民眾對光榮的向往。5P.A.Brunt,“Laus Imperii”,in P.D.A.Garnsey and C.R.Whittaker eds.,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61-4.
從公元前3世紀到前1世紀早期,羅馬的影響力突破了意大利半島,逐漸覆蓋整個地中海地區。如公元前2世紀波利比烏斯在《通史》開篇中所言,幾乎整個世界都收歸羅馬的統治之下。6Polybius,The Histories,1.1.5,in Polybius,Vol.I,pp.2-4.這一發展首先被看作是權力的擴展,而不是占領領土的增加。的確,羅馬有時把某地長期指定為行省的做法要比羅馬士兵首次踏入該地區的戰事要晚得多,譬如羅馬在公元前241年從迦太基人那里攫取西西里島,公元前238年攻取撒丁島,但羅馬的大法官從公元前227年才被定期派駐到那里。西班牙的情況類似,盡管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戰爭一開始西班牙便是一個provincia,但從公元前196年大法官才定期被派駐到此行省。1Richardson,Hispaniae: Spain and Development of Roman Imperialism,218-82 BC,pp.1-2.
理查德森(J.S.Richardson)認為,從羅馬人用以描述自己軍事活動和政府結構的語言來看,他們所謂的統治與對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兼并和殖民沒有關聯,他們最為關注的是如何控制其他國家或民族,或者說他們的帝國要從利用權力施加控制的角度來認識。這并不意味著元老院和羅馬人民不是帝國主義者,抑或他們對其他國家或民族采取防御性政策。但,他們所看重的是羅馬人的權力或統治,尤其是以將領開展戰事為突破口壯大國家實力,因此帝國的形成也并非以兼并領土的方式實現的。這種帝國主義和隨之產生的帝國在公元前1世紀早期這個階段還迥異于以建立一片世界性領土為目標的帝國,或者說不同于帝制時代羅馬皇帝所統治的帝國。2Richardson,The Language of Empire,pp.61-62.
羅馬人在很長時間里體認到的是一個權力帝國。在這個權力帝國中對其他地區和族群的統治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而控制方式又有直接與間接之分。公元前396年攻破維伊后將之歸入羅馬土地(ager Romanus),這屬于直接統治。羅馬利用公元前338年后重新組建的拉丁同盟對拉丁人進行間接統治,一些從前的同盟者并入其中,一些仍在法律上保持獨立。羅馬以這種拼雜的統治方式實現了對鄰邦的控制,獲得了所需的兵力資源,從而有能力在公元前3世紀中期征服意大利其他地方。
以強制弱是古代國家生存競爭的通則。羅馬人在對外戰爭問題上團結一心,這才能解釋何以有如此眾多的羅馬人投身戰爭,卻沒有發生重大的軍事嘩變。恰如一名雅典使節在斯巴達人面前的講話所言:“如果我們接受一個獻給我們的帝國不放手,我們沒做與人性相悖的異乎尋常的事,因為我們將受到恐懼﹑對尊重以及收益的期待的強力驅使。我們也不是這一做法的首創者,強者應該統治弱者,那是永恒的法則。我們理當強大,在你們看來也一樣,至少在你們把私利和正義的言辭合而為一之前。”3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1.76.2,in Thycydides,Vol.I,trans.by C.F.Smith,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64.
四、余論
羅馬的治權隱含著讓其他國家和人民歸附羅馬﹑將世界納入羅馬掌握的意味。羅馬對外征服帶來的后果不僅形成了一個地域意義上的帝國,而且羅馬人也獲得帝國帶來的收益,他們覺得建立帝國是制服對手﹑維護國家安全的有效手段。盡管在領土擴張和建立行省的過程中不一定總能帶來諸多的經濟收益,統治成本有時遠遠高于來自當地的收益,不時發生的叛亂消耗掉羅馬的大批兵力,羅馬也不總是積極備戰。但從總體上說來,羅馬國家包括羅馬各階層人民都贊成羅馬的擴張政策,有這樣的全民支持度才能理解羅馬為何能夠發動取之不盡的人力資源進行對外戰爭。
羅馬帝國是擴張性帝國還是防御性帝國的討論,不能僅從外在的擴張過程判斷,需從帝國建立的動機來判斷帝國的屬性。由于缺少羅馬元老院決策過程的記錄﹑外國辦事機構的檔案文件以及重要人物的書信和日記,而且古代著作家沒有完整的相關記載,羅馬大征服的目的和動機也無法確知。除了資料所限外,還因為動機﹑行動和結果并非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付諸行動之前絕不可能對整個形勢了如指掌,也不可能完全預見到行動的結果,做出決定后也不見得堅定不移,而且偶見的歷史記述中也提及當事者的懷疑﹑猶豫﹑失算,上述種種使得理清當事者的動機更是難上加難。從結果雖不可直接推測出動機,從如何利用結果卻可察明動態的動機。芬利認為,羅馬帝國建立的動機即使不明,羅馬帝國卻無疑善用對外征服的結果,對外征服雖然不能說明羅馬在每一場戰爭中都運籌帷幄﹑醞釀著征服世界的大戰略,但羅馬卻有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堅韌。1M.I.Finley,“Empire in the Greco-Roman World”,Greece & Rome,Second Series,Vol.25,No.1 (Apr.,1978),pp.1-15.
羅馬元老院也曾試圖避免實際的領土兼并,這也被認為是元老院在整個共和國中期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原則。實際上,這一行為準則與羅馬人想要擴張帝國的愿望并非勢不兩立,因為他們不把帝國看作對領土的直接兼并,而是對這些地區行使統治權。2Harris,War and Imperialism in Republican Rome 327-70 BC,pp.2-3.理解了治權,就能懂得羅馬為何有時不急于建立行省,也不急于進行經濟開發,因為只要維持對其他地區的實際控制,便可鞏固羅馬的國家安全,兼并領土進行直接統治并非羅馬急于實現的第一要務。
羅馬人的擴張并非從一開始便懷抱建立一個世界帝國的想法,但權力觀念早已深入人心。他們在國內服從擁有治權的行政官員的權威,還關注擁有治權的將領在海外戰區能否勝任使命。羅馬人的帝國觀念萌芽于羅馬人的治權觀念,隨著治權行使范圍的空間延展,羅馬的帝國觀念也逐漸成型,還理想化地希望將羅馬的權力伸張到整個世界,把羅馬帝國擴大到整個世界。羅馬可在統治地區開發資源﹑殖民籌建﹑賦稅征繳﹑司法裁判之權,但這些都不算是羅馬最初采取軍事行動的動機,許多地區沒有如此多的回報,甚至統治成本甚高。但羅馬人打心底里仍期望其他地區和族群服從羅馬的統治,屈服于羅馬的權力,3Brunt,“Laus Imperii”,pp.162-5.這都是羅馬人的帝國觀念使然。
羅馬帝國開始于共和制之下,在城邦體制下已囊括其絕大部分的帝國疆域。在帝國最終確立起一位皇帝的統治之后,羅馬對其他國家行使治權的步伐放緩。稱呼羅馬是帝國主義者也許不甚恰當,羅馬曾對其他國家和人民施加權力,進行統治,依照的卻是一套極為松散的管理標準,在軍事擴張中并沒有建立起一套組織嚴密的國家體系。羅馬帝國在羅馬人心目中是一個權力帝國,治權是維系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至關重要的紐帶。
羅馬人對帝國的自我認知充分說明了羅馬帝國擴張的性質,即使沒有立即兼并某地,也以統治權塑造了迎合自己的帝國,因為他們最先理解的是一個權力帝國而非領土帝國,哪里服從于羅馬的治權,哪里便是羅馬統治的一部分。通過還原imperium的本意,追蹤官員治權向羅馬人民治權的變化,再到羅馬帝國的權力拓展和空間延展,我們看到羅馬帝國在共和國時代蓄勢崛起﹑蓬勃發展。羅馬人服從權威,崇尚權力,他們相信以軍事手段制服對手,對外族行使治權才是古代社會國際競爭的通則,也是羅馬立國圖強的最佳出路。帝國的收益是對外戰爭的結果,不能解釋羅馬人的擴張動機。一方面從羅馬人如何利用戰果能夠很好地理解羅馬的擴張,另一方面從他們的帝國觀念也能夠深入理解羅馬建立帝國的動機。羅馬人眼中的帝國源自軍事屬性突顯的治權,他們的帝國觀念與軍事活動密切相關,帝國并非若干行省的集合體,而是治權延伸的范圍,羅馬人的權力觀念和帝國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羅馬帝國主義的內在動因。
[作者王悅(1979年—),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上海,200241]
(責任編輯:劉軍)
【中國先秦史】
[收稿日期:2015年11月10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