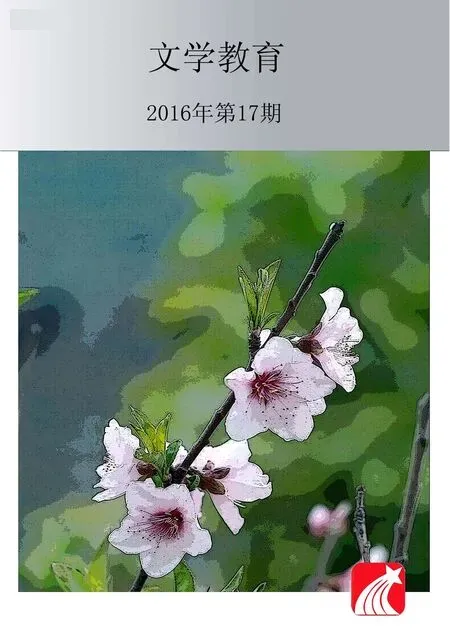新媒體藝術是什么
蘇也
新媒體藝術是什么
蘇也

作者近影
一
與沙發和坦克一樣,當代藝術這個概念也是個外來詞。早在一百多年前的1913年,杜尚就已經把車轱轆安在了木椅子上邊,而紐約也開始了如今赫赫有名的“軍械庫藝術展”(The Armory Show)。所以說,當代藝術在西方世界已有正統的百年歷史,藝術理論水平,藝術表現能力,大眾審美水平都得到了時間和數量的重重歷練。而在他們看來已經司空見慣的,甚至是已經不再新鮮的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在中國大陸還是知者甚少。不少在學校研修新媒體藝術專業的學生,也不知道該如何向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解釋自己到底在學些什么玩意兒。
那么,新媒體藝術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首先,新媒體藝術已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范疇,屬于當代藝術的一種新型表現形式。顧名思義,新鮮的媒體技術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專業解釋來說,新媒體藝術主要指——那些側重利用現代科技、新媒體形式和新的觀看方式,去表現作品主題的藝術作品。而這個新媒體藝術的概念又可以按照媒介的不同來細分成許多具體分支,主要的有:數碼藝術(digital art) ,電腦圖繪藝術(computer graphics) ,電腦動畫藝術 (computer animation) ,虛擬藝術(virtual art) ,網絡藝術(Internet art) ,互動型藝術(interactive art) ,電子游戲藝術(video games) ,電腦機械藝術(computer robotics) ,3D打印藝術 (3D printing) ,還有利用了應用生物科技的藝術作品(art as biotechnology)。
以上密密麻麻列出的這一組概念,每一個都可以單拿出來做一個專業課題。在西方藝術院校,通常也會用一個學期的專業培訓和藝術實驗去研究某一個表現形式。復雜、精準、有效的細分,正好說明了西方當代藝術在新媒體藝術表現形式里的發達程度;這就跟好萊塢電影工業一樣,每一個工種的專業化分程度,直接代表了整個工業的良性發展水平。
這其中,有很多媒介分支都有所交集,而一般的新媒體藝術作品也會采用多重技術,利用觀者的多項觀感,涉及好幾個專業領域。因此,在較為粗放的理解里,人們也通常把新媒體藝術作品統稱為“數碼藝術”(Digital Art);或者按照另一個更為時髦的定義來說,新媒體藝術也屬于“時基藝術” (Time-Based Art)。在“時基藝術”這個定義里,藝術作品把時間這一概念引入了作品的創作和理解過程之中。在我們三維的、立體的生活里,還有一個看不見的維度其實也在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這個無形無影、但無處不在的“第四維作用力”,就是時間。
二
時間,一直以來都是各種科學家和人文藝術家所研究的主題。在天體物理里,時間是一個具體的單位,而在人文科學里,時間多半是個感性的概念。看不見、摸不著,但無時不刻地影響著個體的生命和人類的歷史。隨著現代藝術的發展,和科技對人類理解力的影響,視覺藝術家也開始越來越普遍地意識到時間這一客觀單位的存在,于是越來越多的視覺藝術作品把時間和時間的影響力作為了自己表達和討論的內容。
目前,國際上重要的現當代藝術機構,例如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古根漢美術館,還有倫敦的泰特美術館都已經將“時基藝術”列位了他們的常規藝術媒介分類。“時基新媒體”(Time-Based Media)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藝術概念里,已經和繪畫、雕塑、攝影、裝置等常規藝術種類一起,并駕齊驅,被視為了藝術收藏、藝術編輯、藝術理論研究的一個大方向。而中國內地的大眾對這個概念可能還非常陌生,那么,這個聽起來科幻感十足的時基藝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依照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給出的定義來看,時基藝術是,“包括視頻、電影、幻燈片、音頻和以電腦科技為基礎的當代藝術作品;這些新媒體藝術作品把時間作為一個作品的創作維度,并且通過時間的流逝讓觀者參與其過程之中。”[1]在這個定義里,我們就可以看出時間的流動性,以及觀者的參與性在時基藝術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傳統的藝術分類中,我們可以簡單地將藝術分類為二維作品和三維作品。二維作品應該最好理解,多為我們熟知的架上作品,包括繪畫,攝影,拼貼,印刷品等;而三維作品則會從墻壁上走下來,在長寬高的世界里延展,例如雕塑和裝置藝術。而時基藝術則是在三維藝術的長寬高之上,又加入了時間這一抽象的坐標軸。把時間的流逝,觀者的參與,身體的感知,這三大要素引入了當代藝術的表現形式和創作方式之中。
這么聽起來,描述時間的時基藝術似乎還是有些玄而又玄。但實際上,新媒體藝術基于其自身新奇的表現力和觀者的參與性,應該是最容易被理解、最容易吸引人的藝術形式之一。這里,就要涉及到人類觀看方式的改變。
三
在長期的藝術史里,人類對于藝術的解讀和觀看都是被動的。就拿我們最為熟悉的油畫來說,藝術家將它們創作出來,可以選擇讓它們永不見天日;而那些被藏家、藝術機構拿出來展覽的油畫作品,也是安靜而正經地待在雪白的墻壁上,保質保溫,且不動聲色。觀眾來到它的面前,也只感小心翼翼地觀察,搜腸刮肚地去揣摩,用眼睛和腦子去想象,不能與之觸碰,更別想和它對話。這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藝術觀看方式其實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投入,是十分被動的藝術審美體驗。我們在自己的腦子里絞盡腦汁,胡思亂想,試圖了解藝術品背后的用意和故事,但這么多的努力其實還不如藝術家本人的一個詞,或是藝評家的一段話。
然而,隨著新的科技進步,新的人類交流方式的產生,新媒體藝術正在打破這種被動的藝術欣賞方式,一種交互的、對話式的觀看方式正在出現。借著影像聲效的吸引,搭著時間的橋梁,時基藝術作品正在把觀者的參與和互動帶入到當代藝術的語境里。如果說,傳統的藝術作品是靜態的,那么新媒體藝術就是動態的;如果說,傳統的藝術表達是單向的,那么新媒體藝術的溝通則是雙向的。
在這種雙向的觀看方式里,時間成為了新媒體藝術的關鍵語境。時間的流逝,觀者投入在一件作品里的時光,在這段時光里光線、聲音、空間、活動對于觀者的影響,都是一件時基藝術作品所需要掌控和展現的。所以說,觀看一件新媒體藝術作品的理想型,應該是一次四維的、雙向的、全身心的體驗。
因此,現在當代藝術的發展中,新媒體藝術創作的一大趨勢就是在時基媒體,數碼藝術,和裝置藝術的基礎上利用時間的作用和人類的感官這兩大重要元素,突出藝術作品的“對話性”和觀者的參與感。于是,交互藝術(Interactive Art) 這一新媒體藝術分支在各大藝術商覽和藝術年展上大放異彩,也有越來越多的專業院校和藝術機構把作品和觀者的互動性 (interactivity)作為了一個專門的課題來研究,來討論。而對于那些不懂藝術理論和藝術流派的普通大眾來說,互動性的藝術作品也是十分有趣的,它們要么是用突出的視覺效果和聽覺效果吸引著來往的觀眾,要么是用先進的科技完成與觀眾的交流。總之,作品本身的互動性總是會讓是新媒體藝術快速地吸引眾人,在單獨或者集體的參與活動中傳達藝術家所要表達的主題和情感。
這種藝術的“互動性”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做出一只機器人的手臂跟每個前來的觀者握手,這是一種直接的、可視的互動;但藝術家也可以營造出一個視覺幻像,用空間和體驗去迷惑觀眾的神經和感知。顯然,第二種類型的互動顯得較為“隱形”和“詩意”,是我更為欣賞的藝術表達方式,但同時,這種潛移默化的互動性藝術對體驗者也有一定的要求,作品意義的完整需要觀眾的適當參與,審美基礎和思辨能力。但無論是哪一種交互形式,大部分的新媒體藝術都是利用時間的作用,身體的參與和我們的感知能力來實現意義和內容的交流與互動。

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Eliasson)的"天氣計劃"2003-2004年,Tate Modern,London
四
時間的流逝,觀者的參與,身體的感知,這三大新媒體要素在不同的藝術作品里所占有的比例各不相同,或者說,所采取的步驟是不一樣的。越復雜、越大型的新媒體藝術所需要的觀者投入比例更大。例如,一部視頻短片作品,用顯示屏展示給觀眾,觀眾所需要的投入就是站在顯示屏跟前,花上幾分鐘的時間去觀看這部作品,在時間的陪伴和流逝下,逐漸理解藝術家的意圖;而許多新媒體互動裝置作品所需要的觀眾投入則顯得更多,你不僅需要時間去體驗藝術家營造的環境,甚至還需要真刀真槍地去觸碰、去操作、去完成一個裝置,最后還要根據自己的眼耳口鼻手所獲得的信息去消化得出這一段體驗中所蘊含的意義。
那么,就觀眾投入的比例由淺到深的順序來看,新媒體藝術發生的早期作品,包括錄像藝術、幻燈片藝術、音頻藝術,到后來的視頻藝術,都還只是需要觀眾的觀看和收聽,利用我們的視聽感官;而到了當代的藝術現場,越來越多的新媒體藝術大面積、大規模地動用觀者的各方面感官,甚至有些作品沒有了觀眾的參與根本就不存在。這些觀者參與性的比重加強,一個是新媒體科技的交互創新所帶來的,二個也是隨著大眾媒介、網絡環境、社交媒體的不斷興盛,現代人的觀看和體驗方式已和幾十年前大為不同。藝術家一方面用作品傳達著這類的訊息,一方面又讓觀眾在體驗式的觀看行為中意識到這樣的時代和文化變遷。
不過,現在再回首新媒體藝術產生的初期,許多藝術家在七十多年前就已經預言了如今的媒體觀看模式。例如,2006年去世的韓裔美籍藝術家——白南準(Nam June Paik),他被美國人譽為“錄像藝術之父”(Father of video art),也是當之無愧的新媒體藝術先驅。白南準在其1972年撰寫的文章中,就預視了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信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他也代表了早期新媒體藝術家的一個共同特質——醉心于鉆研科技的潛力和新的視覺表達語言。他們這一批被后人稱為“圖像工程師”(image technician) 的藝術家終日埋首實驗室,研究新的圖像技術和新的播放技術對藝術的直接影響。例如,白南準與日本籍工程師Shuya Abe合作開發的錄像合成器,就利用了電臺頻道控制的錄像裝置,成功的將影像透過電子方式加以重組和處理,并結合及時的電視訊號來進行藝術創作。同時,白南準還將當時十分時髦和先進的手持錄影設備融入到藝術當中,與傳統的文化符合和觀看方式產生了有趣的對話,創作出了一系列例如《電視大提琴》 (TV Cello,1971)、《電視佛陀》 (TV Buddha, 1974)、 《電視羅丹》(TV Rodin,1978) 等重要作品。其中,以他的《電視佛陀》最為著名,白南準采用了一套SONY錄影設備,制作出了封閉循環的錄影作品,將他自己的古董收藏——一個佛陀的佛像,擺放進入了一個極具后現代風格的語境之中。一架SONY錄像機對著閉目禪修的佛陀,拍攝下的影像出現在了一個極具摩登風格的圓型電視機中,結合及時播放的錄影影像,讓真實生活里的佛像與閃爍的電視螢幕中“倒映”的佛像產生了有趣的面對面。這是一幅極為沖突但又透露出禪意的作品,讓人們不斷去思考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在、真實與再現等重要藝術主題。
除了錄像、及時播放、電視顯示屏,還有一項技術常常被運用到新媒體藝術的創作里,那就是投影技術。1957年出生于紐約的美國藝術家托尼·奧斯勒(Tony Oursler) 就是一個長期利用圖像投影技術的藝術家。雖然他的作品包括繪畫、雕塑、行為藝術,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他的投影裝置作品。在奧斯勒的創作里,他常常將人臉和五官的一部分投影到自制的雕塑表面,讓一個奇形怪狀的物體展現出栩栩如生的喜怒哀樂,再借助投影環境的燈光效果,奧斯勒的投影雕塑往往會給人十分驚愕的視覺效果。那種刻意為之的視覺張力、人類器官的熟悉和不安、怪異的生命力都形成了奧斯勒的藝術語言。通過造型的疊加和投影帶來的動態和聲音,奧斯勒制造的新生物、新噩夢、新童話都是生動而夸張的,利用觀者的感官認知和理性的不安和不適表現了當代生活中的焦慮和奇思。
相較于奧斯勒而言,美國女權主義者、概念藝術家,珍妮·霍爾澤(Jenny Holzer)的作品則顯得更為內斂和嚴肅。她的大部分作品也利用了圖像投影技術,在公共場所,場館內部,或者建筑的外表上大面積地實施文字投影,用滾動播放的標語改變一處公共環境的視覺表面和文化景觀。在霍爾澤初涉藝壇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興起時期,作為一種對傳統藝術形式物質化和造型性的反叛,觀念藝術強調藝術的“非物質化”的過程。于是,許多觀念藝術家都通過各種聲音、文本、語言等媒介方法來表達個人的藝術思考,而像霍爾澤這樣的觀念藝術家也將語言、文字的存在和意義作為其藝術作品的主要議題。在公共環境里實驗大面積的投影活動,她的作品影射了廣告牌、霓虹燈、電子屏這樣的公共環境信息輸出方式,抓住了普通大眾的視線;而用這種公開的、直播的、文字的藝術作品展現了一個已被現代人淡忘的問題——文字的控制力。霍爾澤討論女性身份,藝術價值,信息的不對等。在我們看似繁榮的信息圖像環境里,霍爾澤提出了關于文化的歧義、政府對信息的監管、知識公平、權利對等等社會問題。對于其作品的理解需要觀眾投入一定的時間讀完她所播放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語言能力,更需要一種反思的理解能力。霍爾澤依托在投影技術之上的新媒體作品,是一種基于語言文字的直接對話,也是一種敞開心扉與觀者互動的行為。

如果說,上面談及的幾個作品只是利用了我們的視覺和聽覺來完成藝術表達,那么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的許多作品則是利用了我們的視覺、聽覺、嗅覺、方向感等許多感知能力。他的代表作《氣候計劃》“WeatherProject”,用新媒體手段在倫敦的泰特藝術館內制造出了倫敦人久違的太陽。把一種日落的美好和天氣的影響力引入到嚴肅的美術館內。前來參觀的觀眾一時間會忘記自己身在何處,看見頭頂的暖陽,會自然地席地而坐,聊天說笑。除了制造特殊的光線、空間和溫度,埃利亞松還專門加重了展廳里的空氣濕度,并在空氣中混入了一種由蜂蜜和糖調制的芬芳,從視覺、觸覺、嗅覺全方位打動觀者。在時間的流逝中,觀眾是懷著享受的心情完成著這種藝術的體驗。也許,新媒體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讓觀眾忘記所有的技術手段,自愿地、全身心地、放松地融入到一種環境和體驗當中去。
注釋
[1]“Contemporary artworks that include video,film,slide,audio, or computer-based technologies are referred to as time-based media works because they have duration as a dimension and unfold to the viewer over time.”
蘇也,留美博士,《布林客BLINK》主編,現居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