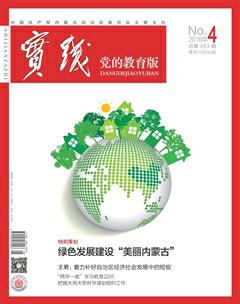從讀者作者到編者
如果把人生的每次相遇都歸于緣分,我與“黨的教育”結緣已經50多年了。50多年,我從讀者、作者到編者,一路走來,從內心深處感受著她的溫暖親切、嚴謹求實和博大精深。
上世紀60年代初,父親常帶回一些報刊學習,其中就有 《黨的教育》,當時是32開本的小冊子。封面上“黨的教育”幾個字特別醒目,每次看到我都急切地想看看其中的內容。印象中,那時《黨的教育》的文章都比較短小,語言生動,通俗易懂,插圖形象。聽父親說,《黨的教育》是作為黨員提高思想覺悟的學習資料,而對于一個不諳世事的小學生,我常被其中的一些小故事所吸引,從中學習許多道理,這讓我受益匪淺。
歲月更迭,情懷不變。上世紀80年代初,我寫了一篇2000字左右的人物通訊,說的是一個農村女青年沖破重重禁錮,積極參與農業科學實驗的故事,稿件投到當年《黨的教育》農村版。當時的美術編輯為了做到圖文并茂,特邀我去她的住處為稿件配插圖。幾易畫稿,反復排版,嚴謹認真的精神讓人感動。她還受編輯部委托,與我核實文中的數字、時間等。見微知著,雜志社編輯們的敬業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緣分是機遇的把握與選擇。1998年,我有幸調入《黨的教育》成為農村版的編輯。與其同呼吸、共命運,直到退休。雖然現在離開了工作崗位,但在當年工作時的歷歷往事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深處。編前會上的激烈爭辯,編輯過程的增刪取舍,校對時的小心翼翼,挑燈夜審的激情亢奮,如此種種,像錚鳴的號角漸行漸遠,卻歷久彌新,仿佛如昨。
最難忘的是2001年,我國經過15年的努力,加入了WTO。是時,國人歡欣鼓舞,WTO成為熱門話題。但是,WTO的具體內涵是什么?我國加入WTO的意義何在?這一系列問題,很多人都不甚了解。鑒于此,我提出開設解讀WTO專欄的想法。為了增加欄目的知識性、權威性和可讀性,我邀請當時自治區法制辦副主任劉繼春作為專欄作者,為我們提供稿件。因為《黨的教育》的讀者主要是基層黨員干部,為了讓文章既通俗易懂,又有理論高度,既全面系統,又重點突出,我與作者多次溝通,反復斟酌,最后確定既要把學術性的語言通俗化,又要力求語言生動,事例精彩。這個欄目一經推出,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后來,《黨的教育》與《實踐》雜志合并,我在《實踐》雜志黨的教育版負責“和諧社會”和“文化采風”欄目,因為是新開辦的欄目,面臨“稿荒”,盡快培養高水平的作者成為當務之急。為了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隊伍,我在一大堆自然來稿中,篩選出文筆較好的作者與其聯系,探討欄目所需文章的內容、體裁、風格,提出具體要求。同時,我還積極與盟市旗縣組宣部門及廳局委辦的工作人員聯系,向他們約稿,詳細探討稿件的內容、題目、切入點,甚至每一個段落都字斟句酌。久而久之,作者隊伍壯大,一大批高質量的稿件紛至沓來。
回憶我與“黨的教育”的點點滴滴,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如一股暖流,在我的記憶深處激蕩。遲暮之年,唯愿《實踐》雜志黨的教育版越辦越好。
(責任編輯/麥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