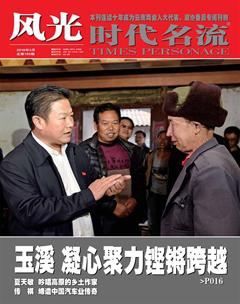深扎土地 擁抱生活
劉建忠

初冬的北京,略顯寒冷,而中國現代文學館內卻暖意融融。
2015年11月5日,沈洋長篇小說《萬物生》研討會在這里舉行,這是繼上半年作家楊莉的報告文學在北京研討之后,昭通作家的又一次高規格文學研討會。與會專家用了三個多小時,以他們獨到的眼光,對《萬物生》進行了深度的“望聞問切”,對作品中優秀的地方給予了肯定,也對存在的不足給予了善意的批評。
一個好的作家只有放下身段、深入到基層,才能寫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和有泥土味的文學作品。作為一名“70后”的昭通作家,沈洋從2009年就開始深入昭通市昭陽區永豐鎮三甲村體驗生活,2012年被任命為永豐鎮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隊長,一直持續到2014年初。在這5年里,他走村串戶,遍訪農家,成了村民們的朋友。2015年,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和見聞,創作了反映新農村建設情況的長篇小說《萬物生》,并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當天上午,中國作協創聯部副主任邢春,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云南省作協副秘書長胡性能分別主持了研討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中國藝術報、中國文化報、中華讀書報、中國作家網、作家通訊、昭通日報、昭陽新聞中心等多家媒體關注了研討會。
白庚勝(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沈洋通過長期深入生活,獲得了對農村發展的深切認識。長篇小說《萬物生》寫出了一個村莊在掙扎中蛻變的軌跡,張揚了中國農民百折不撓、敢于創造的拼搏精神。作者把工作隊隊長文雅琪的形象塑造得尤為生動、可信,她既理想又務實、既有原則又不死板,勇敢而智慧地與村民們一同面對村莊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難,小說緊貼大地脈搏,富有生活趣味和時代氣息,同時又有歷史滄桑的縱深感,是一部弘揚主旋律、傳遞正能量的優秀作品。當然,這部小說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部分的敘事節奏過于平穩、語言不夠節制等。希望沈洋能以長篇小說《萬物生》為新起點,克服不足,再接再厲,再創佳績。也希望有更多的作家朋友深入基層生活,從廣大群眾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以優秀作品回報時代、奉獻人民。
`
葛笑政(作家出版社社長):沈洋的作品是以一個叫文雅琪的工作隊長走基層為主線來寫的。大家都知道,現實農村題材其實非常不好寫,具有很大的挑戰性。既要通過作品表現出正能量,同時又要能對中國的現實有深刻的思考和批判,我覺得難度很大。而沈洋的小說《萬物生》基本上做到了這一點。中國作協關注基層一線的作家,鼓勵他們深入生活,創作出反映基層生活,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會起到一個導向性的好作用。
雷達(中國小說學會會長、著名評論家):作為長篇小說,《萬物生》的結構獨特而有特色,沈洋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藝術的概括生活的路徑,通過文雅琪這個下派干部,讓讀者知道了蘋果村,伴隨著愛情故事貫穿全文。作品是雙線敘述,工作和愛情兩條線,相互糾纏,展開的是兩族的較量,是父輩甚至祖輩的恩怨在新一代摒棄前嫌,并且產生了愛情,這個概括絕對是文學的,不是流水帳。還有一系列的懸念,產業升級能否正常進行,蘋果園的改造能否順利,文雅琪他們的愛情是怎么萌發的,有沒有基礎,最后到不顧一切的后果,甚至與骨灰盒結婚,這些都會引起讀者濃厚的閱讀興趣,很抓人。另外,作者在寫作中,方言的寫作非常生動,很善于抓特征。
總體來說,這部小說是成功的,值得肯定,同時我也感覺到還是有點遺憾。小說在處理文雅琪與宗澤和康夢的愛情方面,顯得弱了一些。不過,沈洋對藝術有很好的品質,很有潛力,相信他在下一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會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梁鴻鷹(《文藝報》總編):我覺得《萬物生》這個作品原生性和生活的質感,都是非常強的,作者對生活的捕捉,源于對土地的深厚感情。我能看得出來,他小說里面描寫的山山水水,都懷著對于這塊土地深厚的感情,作者特意寫到主人公的書架上擺的書,把昭通人的書全部植入了,他非常熱愛這塊土地,熱切地關注著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事。而當前也確實在我們的新農村建設當中,需要這樣的新生力量。
不足之處就是,第一,我覺得小說寫得太密了,都是事,對人的心路歷程描寫和人物刻畫還不夠。第二,一共十六章,我覺得也沒必要這么長,每段還可以更短一點。
施戰軍(《人民文學》主編):沈洋的這部小說出了以后我又看了一遍,確實是有不少話要說,重要的是,這部長篇找到的架構很有意思,這個架構是什么呢,就是新的一代年輕人,這位文雅琪,她遇到她的心上人宗澤這個人,但是他們上幾輩都像有世仇一樣,對象都是宗家,他們這一家人,幾輩人結下來的一種緣分,這個緣分也不是什么好緣分。整個小說的基本架構非常高明,長篇小說是需要一個東西支起來的,沈洋這一點找得準。只有好作家才能看到這個架構的。還有一個就是,它如何寫這個舊時代的恩怨對新時代發生的作用,又要體現新時代人的擔當,這個從精神層面講,也是難度非常大的,沈洋在努力使這些東西形象化。
當然沈洋還不算一個經驗十分豐富的作家,處理這樣的題材,對年輕的沈洋來說,困難不小。文雅琪怎么能夠負擔起這個細節來,宗澤在里面起到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在有仇的父輩,心愛的女人中間怎么糾結,這個寫的還不夠,處理得相對來說有點單薄,但這也不是什么大問題,畢竟沈洋的寫作之路還很長。
胡殷紅(中國作協辦公廳主任):長篇小說《萬物生》的敘事主線,是以選派青年干部文雅琪到鄉村掛職碰撞一系列困難的故事來完成敘述的。應該說在結構作品時,作家特意抓住女性的生存狀態來挖掘線索,是最容易接近社會矛盾本質的,作品對待女性的態度,標志著作家本人對社會有足夠的認知度和識別度。
沈洋的作品把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市場經濟對農村生活的沖擊的外部因素作為敘事內容,抓住了農村改革題材需要挖掘的關鍵地帶。沈洋深入農村,和老百姓建立了感情,因此也積累了帶著溫度的素材,同時找到了適合這部小說接地氣的語言,富有生活情趣和特點。
王山(《中國作家》主編):就小說創作而言,我覺得新農村建設這個題材確實是一個非常難寫的題材,很難把握,但沈洋把這個題材寫得很成功,給人以希望。就深入生活而言,我覺得沈洋確實是一個身體力行的寫作者,扎根人民,全身心地去擁抱生活。真正的非常具體的體察到了生活的真實,包括強拆的過程,寫得活靈活現。
但我也非常坦白地說,我是注意到了小說有些扁平化的感覺。作為長篇小說來說,它畢竟是一個語言的藝術,是一個敘事的藝術,因此,寫作中更要充分考慮人物和事件設置的合理性。
徐忠志(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中國作協組織定點深入生活,通過這個舉措展現出《萬物生》這樣一個成果,令人欣喜。
就作品本身來講,文雅琪這個人物給我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這個人物可以說是比較成功的,文雅琪的成長很令我興奮,她的成長完全不是淺表化的,概念化的,她跟我們現在所有的通過讀書就業的青年一樣,非常具有普遍性。讓人讀了之后,這個人物確實是給人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
我很欣賞沈洋的這種敘事風格,很樸實,有充分的寫作的鋪墊,也很流暢。但有的時候他習慣于用一種筆法,以后要引起注意。小說中還有一些細節問題,也還有斟酌的余地。
王干(《小說選刊》副主編):沈洋這個小說,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品,寫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復雜性,艱難性。好的小說可能不是簡單的,最簡單的小說就是新聞報道,最復雜的小說就是《紅樓夢》。所以我覺得《萬物生》是有根的寫作,因為有根,萬物才能生起來。我們更應該鼓勵這種有根的,能夠接地氣的,能夠把大地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文學的需要放到自己作品中的作品。
楊曉升(《北京文學》雜志社社長兼執行主編):《萬物生》應該說是一部主旋律的小說。縱觀整本小說,我個人認為寫的比較出彩的是第十章。這章無論是故事敘事,情節,場景,細節,人物心理活動等,都把握好了主線,這個寫得很有水平。但小說總體上缺少對當代農村和當代現實生活復雜性的深入把握和思考,雖然對年輕的沈洋來說,太過苛刻,但相信他會在以后的創作中做的更好!
顧建平(《長篇小說選刊》主編):《萬物生》是一部直接全面呈現新農村建設的現實主義作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個口號已經提出許多年了,但是社會公眾對于什么是新農村的概念是很模糊的,這是第一次有人從新農村建設工作隊,新農村指導員這個角度,直接去寫新農村的建設,確實讓人大開眼界。
這部小說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文雅琪建設新農村的這種英雄形象。文雅琪沒有被機關所污染,但她又不同其他的知識女青年,她顧全大局不任性。小說把時代英雄這個角色放置在文雅琪這樣的軟弱的姑娘身上,人物得到了讀者的認可,小說就成功了一半,剩下的就是情節描寫了。作品不足的地方是,第一個沒有充分寫出新農村建設的復雜性。另外,就是小說的結尾稍稍欠妥,不太合乎情理。
郭艷(魯迅文學院教學部主任):首先,這部作品是一部特別有生活的作品,我特別贊賞。對于沈洋而言,這樣的鄉土寫作,也必然面臨著新挑戰,是有難度和風險的。可以說,作者沈洋非常有勇氣的挑戰了這個關于新農村的題材。
作為苦難時代長大的一些人,我們的青年作家,如何面對現實和歷史,值得思考。如果建構好自己的長篇小說文本,你就必須要有前后雙向的突破,這樣才有可能對于當下復雜的中國現實,有著更為有力的表達。
俞勝(《中國作家》文學編輯部副主任):《萬物生》以優美的文字為當下農村題材小說塑造了一位充滿正能量的女掛職干部形象,這是一大亮點。
《萬物生》人物關系盤根錯節,蘋果村村支書劉孝恩是文雅琪的表叔;村主任宗官員是主持鎮政府工作的副鎮長宗澤的父親,宗官員家與文雅琪一家有兩代“世仇”,宗澤后來又成為文雅琪的男友。小說的情節在充滿張力的矛盾沖突中向前發展,跌宕起伏,故事性很強,好看、耐讀。這些人物形象塑造得生動飽滿,入木三分,展示了作者深刻扎實的藝術功底。《萬物生》的意義還在于為人們打開了了解當下農村的一扇窗口。通過這扇窗口,人們看到,當下的農村出現了不少新的元素,呈現出一些新的動態。
《萬物生》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譬如,結尾部分宗澤不幸遇難后,文雅琪仍然決定與其舉行婚禮,婚禮上,紙扎的宗澤能鞠躬能下跪的描寫,都消弱了故事的真實性。文雅琪最后辭去鶴鎮黨委書記一職,也不大符合人物性格發展的邏輯,顯得作者是為了避免人物塑造上的高大全之嫌,在有意拉低這個人物的形象。另外,對其他掛職干部描寫,只集中在有限的幾次會場,在扎根農村建設和發展方面,著墨似嫌不足。但終歸瑕不掩瑜,《萬物生》是一部描寫當下農村題材的優秀著作。
劉瓊(《人民日報》文藝理論評論室主編):《萬物生》特征性非常強,是深入生活,來自于生活經驗的作品。我認為,這是一個比田園牧歌更接近于當下現實的一個鄉土文學作品。
作品寫到了各種各樣的事例,寫到了農村社會的現狀,同時還寫到農村社會經歷的各種考驗,這種考驗有生態的,包括具體的生態,也有社會生態。他寫出了新農村建設的走向,雖然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準確的,但實際上我們體現的生態文明的東西,就是這樣一個農村的文化的態勢。
不管怎么說,沈洋對于新生事物的判斷,雖然有解讀有反思,最后還是通過任務的結局和結論,給出了力量。跳過藝術性講觀賞性,我認為跟作者的經歷有關,我想這個小說特別適合拍成電視劇。
宗永平(《十月》編輯部主任):我試著換一個角度來講,就是小說藝術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大伙都知道,中國現在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就是鄉村的城市化。也有不少文學作品表達過這方面的內容,比如留守的狀態,很多人都去了城里,使鄉村呈現荒蕪,應該說沈洋的《萬物生》對當前農村狀態的描寫和把握是很到位很深刻的,有其獨到的視角。但不足之處在于,小說結尾略顯突然,他們為什么用遺像結婚,這是一個值得再思考和斟酌的問題。
夏天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昭通市作協主席):非常高興來北京參加沈洋的《萬物生》研討會,他在《萬物生》作品里面,前半部寫的那些事,實際上我一看就是他做的事,寫的非常實在。后半部他寫的蘋果改造升級,是他的一個夢想,這在山區的地方是沒有的。但是我覺得他把在村里做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體驗結合起來,去表現兩個夢想,一個是物質文明建設,一個就是精神文明建設。同時他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就是把那個地方變成一個非常富庶的,讓老百姓都能幸福生活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這個作品的后半部分帶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寫得更好一些。總之,他這部作品,我覺得是花了大力氣的,因為他下去后非常扎實的工作,在體驗生活方面做出了表率,是真正意義上的體驗生活,也是扎根人民的寫作。
沈洋和我們昭通的很多青年作家一樣,他有的是生活,缺少的是理論修養,或更廣闊的視野,現在他正在向這個方面靠近,所以我相信他會寫出更好的作品來的。
宋家宏(云南大學教授、云南文學研究所所長、云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如何建設新農村?在這一過程中農村、農民、農業發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上至各級政府,下至新農村建設的工作隊員,應該給予農村,給予農民哪些切實的幫助?在這一過程中,農村、農民將面臨一些什么樣的矛盾與沖突,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將要發生那些變化才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沈洋以他的長篇小說《萬物生》試圖以自己的理解回答上述問題。
沈洋盡管已經有一些長篇小說的創作經驗,但是對長篇小說的藝術結構認識仍然有所不足。《萬物生》的矛盾沖突組織不夠合理,也就是結構線索的安排未能使小說呈現出波瀾起伏的狀態,小說有前輕后重之感。這其實反映了作者對這些沖突隱含的內容理解不夠深入,對人物性格與心理把握也有所不足,有的甚至也是不敢更深入直面現實。
潘靈(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副秘書長、《邊疆文學》總編):沈洋的長篇小說《萬物生》,就是這些年沈洋在深入生活的河流從中淘洗出的沙金。作為農民的兒子,是不可能對發生在身邊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運動熟視無睹的。農村艱難的蛻變過程,農村在城鎮化進程中如何守住青山綠水和鄉愁,堅守幾千年形成的鄉村文明,都是激發作者創作的動力。沈洋在《萬物生》這部書寫新農村建設的作品中,成功塑造了一個鮮活、生動、飽滿的新農村建設工作隊長的形象。這是沈洋心目中理想的新農村人物形象,摒棄性別因素,這個人物身上,有太多作者的影子。
當然,沈洋的寫作,還有稚拙之處,在長篇小說創作中,如何解決結構問題,如何從容駕馭幾十萬字,都是他今后要面臨的問題。
呂亞平(昭通市文聯主席):作為一名下派到農村工作的文藝工作者,作家沈洋牢記宗旨,用心工作,用情體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僅以實際行動幫助村民辦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好事實事,還以飽滿的熱情,深情的筆觸創作了長達三十余萬字的長篇小說《萬物生》,值得肯定。我們將會把今天會議的研討成果帶回昭通,總結經驗,正視不足,拿出更切實有力的激勵措施,鼓勵昭通作家再接再厲,再創佳績,為“昭通文學現象”和“昭通作家群”添磚加瓦,增光添彩。
責任編輯:吳安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