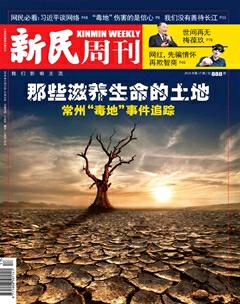思南讀書會:因為愛
李偉長
因為愛文學愛閱讀,才有思南讀書會一周年,文學閱讀的“周播劇”才能持續下去。文學名家成就了思南讀書會,思南讀書會又在反哺年輕人,未來的文學名家就在他們中間。
上海有很多讀書組織,在思南讀書會出現之前,我關注較多的是“星期天讀書會”,創始人是文學編輯何家煒和安小羽。它就像一個“流浪者”,走過城市的多個角落。不斷移動,是它的特點,也是它迷人的地方。跟著它旅行,不僅讀了書,也讀了城,兩全其美。當時豆瓣正熱,“星期天讀書會”的活動信息每周都會通過豆瓣同城發布。那時的我從未想到,不久以后,我也會有幸參與一個更引人矚目的讀書會——思南讀書會。
由來:國際文學周的常態延伸
2013年,上海國際文學周首次將部分活動放在“思南文學之家”——這是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和上海作協聯合創設的文學空間,坐落于被譽為優秀歷史建筑露天博物館的“思南公館”,由諾獎得主莫言先生題寫匾牌。文學周活動精彩紛呈、熱鬧非凡,但遺憾的是時間很短,只有一周,剩下的300多天怎么辦?
文學周結束后,闞寧輝和孫甘露兩位老師召集了一個座談會,感慨文學周成功和熱鬧的同時,商議在文學周結束之后如何繼續做一點事情,讓好不容易形成的閱讀氛圍持續得更久一些。每周六舉辦書集和讀書會的想法就此生成,不僅得到了黃浦區委宣傳部的支持,國企思南公館也熱忱響應,愿意每周六免費提供“思南文學之家”的場地。2014年2月15日,第一期“思南讀書會”開張了。
兩年后的現在,回頭去看,才知當初的這個創意有多瘋狂。不曾想過將來會有多少困難,連如果辦不下去了怎么收場的退路也沒想過,整個方案就是簡單幾頁紙。一群熱愛讀書的人在幾位創始人的帶領下,興致勃勃就開始策劃第一期活動。要是沒有當初的“沖動”和闞寧輝、孫甘露、李崟等創始人的熱情,也就沒有今日為人關注的思南讀書會。事在人為,想干就干了,要是想東想西,瞻前顧后,也許就錯過最好時機了。
還記得思南讀書會第一期的情形——請的文學嘉賓是作家孫颙先生,對話嘉賓是上海作協主席王安憶。讀者的熱情超乎我們的想象:活動開始前一小時,讀者就排起了長隊,等候嘉賓入場。現場真是座無虛席,有很多讀者站著聽完了講座,更有讀者索性席地而坐。與此同時,場外的“思南書集”也傳來了好消息,400多本作家簽名本被讀者一搶而空。活動開了一個好頭,給了組織者很大的信心和鼓勵。對于大多數活動策劃者而言,最苦的不是工作,而是無人問津,沒有回響。第一期不但有響,響聲還很熱烈,讓參與者們感到欣喜和激動。
空間:找到了容易被接受的表達
每一期,每一個周六,對思南讀書會而言,都是新的累積和重新開始。一邊做,一邊摸索,在行進中不斷總結,慢慢梳理經驗,形成有效的流程——新聞出版局作為政府進行主導,上海作協作為文學專業機構進行運作,黃浦區作為東道主負責后勤保障和推廣,思南公館提供現場服務。孫甘露老師作為總策劃,東早的石劍鋒、九久的彭倫和我參與內容策劃、前期預告、素材整理和嘉賓的聯絡,后來,青年小說家王若虛也加入了策劃團隊。
不親身經歷活動,就無法預料會有這么多的瑣事。把一期活動做好不難,難的是一年50多期,期期都要做好。工作量之大,細節之瑣碎,磨練人的耐心,也錘煉人的細心。幸在幾位創始人都很寬容,對青年人犯下的許多錯誤、失誤都給予了大度的理解,有時候出現了一些小失誤,主動承擔責任的是他們。最焦慮的就是——原先安排好的嘉賓突然有事來不了,策劃團隊就得連夜商量對策。
思南讀書會能夠被認可,和國家推廣全民閱讀的天時有關,和思南公館充滿歷史文化底蘊的地標性建筑有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使來自不同幾方的人群,在同一個空間里面完成了有效的相互交流。比如作家,有個人習慣的文學語系和文學思維習慣;大學里的學者教授,有自己的理論體系、說話方式和表達習慣;媒體記者也會有自己的興趣點和新聞意識;還有讀者,會有個人的聽講期待——把這四方人聚集在一起,就會發生一個明顯的化學變化——一旦臺下有了讀者,不管是20個還是200個,要讓溝通有效,就要為這些讀者說清楚,所以嘉賓會有意識舍棄過于個人化的語系,找到大家能夠共同理解的表達方式。關于這一點,作家奈保爾說得更為清晰,即:再獨特的思想,也得找到易被讀者理解的表達方式。而思南讀書會就是這樣一個空間,它形成的是一種專家、作家、讀者和媒體都能明白的話語體系。
2015年2月,讀書會一周年的時候,我們策劃了一場特別活動,主題叫“因為愛”。因為愛文學愛閱讀,才有思南讀書會一周年,文學閱讀的“周播劇”才能持續下去。兩年多來,300多位文學嘉賓,真是名家薈萃,少長咸集。有國際大牌如前諾獎評委會主席埃斯普馬克,有學術巨擘如馮象、李歐梵、樊樹志,也有文學名家如韓少功、賈平凹、畢飛宇等;少壯派也來了不少:張新穎、路內、小白和毛尖,還有更年輕的力量如周嘉寧、張怡微、三三等……這份名單很長。文學名家成就了思南讀書會,思南讀書會又在反哺年輕人,未來的文學名家就在他們中間。這就是文化生態,通過讀書會,不分少長,彼此鏈接。
讀者:從傾聽者到參與者
如何定位讀者,是任何讀書會都要考慮的問題。思南讀書會不把讀者作為單純的聽眾,而是定位為重要參與者。這也就是為什么思南讀書會不會刻意為讀者定制什么口味,更不會迎合讀者。如果只是為了討讀者喜歡,為了積攢人氣,多做“輕”內容即可,比如有明星效應的作品作者。相對于娛樂讀者,提供有品質的內容,才是思南讀書會的追求。如孫甘露所言,讀書會畢竟不是演唱會,不是人越多就越好。
打個比方,如果說整場讀書會是一場完整演出的話,那讀者也是演員,雖然扮演的是聽眾角色,也要參與進去,和學者和作家進行交流。主講嘉賓是一個講述者角色,主持嘉賓是追問人的角色,媒體朋友則是傳播者角色。讀者作為參與者,是整場活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有效傳播的一個基底,而不僅僅是被服務的對象。思南讀書會創設了“年度讀者”模式,每年會選出5位年度讀者和1位年度榮譽讀者,已經連續做了兩年。
好幾位年度讀者都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一位是許樹建先生,稱思南讀書會是他的大學。每期讀書會前,都會買好書,做好功課。第二位是公司職員岑玥,她愛朗讀,專業水平,曾于一周年活動時朗讀冰心的《寄小讀者》,極富感染力。第三位就是80多歲的老翻譯家馬振騁先生,一個熱愛新鮮知識的老前輩。有一期嘉賓是裘小龍、陳保平和陳丹燕,談起了文學翻譯和雙語寫作的難題。馬先生很風趣,說:“很多菜名其實是沒辦法翻譯的,比如腌篤鮮、咕咾肉、木樨肉,怎么翻呢?帶外國朋友去中餐館,就說這是牛肉、豬肉和雞肉就可以了,多解釋沒有用。”提到怎么翻譯“鮮”字,馬先生笑著建議:“應該直接譯成very xian,就像pizza一樣,時間長了,外國人也就懂了。”老人家說起這些時候,孩子般的笑,很是可愛。為了向老先生表示敬意,在思南讀書會兩周年活動時,我們向他頒發了年度榮譽讀者的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