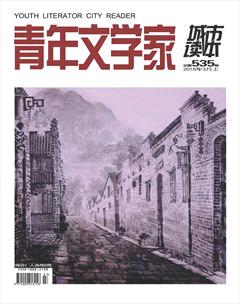笑不露齒與行不露足
常常想起小時候,父親對我開展的以“笑不露齒與行不露足”為主導的女德女容教育。讓那一段不念貧寒、少有憂愁的歡樂時光倍受拘束。
那時,常常因為小開心而放聲大笑,而父親就會嚴厲呵斥,而我的笑聲也會如急剎車一般戛然而止,迅速演變為“笑不露齒”。所謂行不露足,是指古時的女子因為穿著曳地長裙,走路時應該小步若趨,緩緩而行,曳地的裙邊也是緩緩顫動。倘大步流星就會露出腳來。少女時代的我不僅大步流星,還時常歡呼雀躍,著實難以遵守父親的規定。于是每每看電影,父親會指著電影里的日本女人對我說,這才是做女人的樣子。我會瞪大眼睛看著日本女子垂頭挽手,小步若趨,跟在男人的身后,心里不甘地想,為什么女孩子就要這樣做呢?
因為對于“笑不露齒、行不露足”執行不當,父親著實下了一番功夫。一次,問我知道女人為什么戴耳墜子嗎?我茫然。父親說,那是對女子的警戒,當女子不注意婦容,放蕩大笑而顫動耳墜,耳墜就會打她的臉,警醒其注意婦容。還說,女子走路時不僅要緩緩小步,神態安詳,而且即使有人突然叫你,也要緩緩轉身,而且不能猛然回頭,要“頭隨身轉”,做到耳墜不打臉的才是名門閨秀。我聽得如醉如癡,想象著朱門閨秀的款款可人,心向往之。但是從此不敢扎耳朵眼兒,直到出嫁之日現扎耳朵眼兒,但是一直只肯戴上小小耳釘,多年來,無論多么流行、多么漂亮的耳墜子,從未打動過我,全因對耳墜打臉一事心生恐懼。父親的教育也算成功罷!
少年不知愁滋味,隔窗梳理秀發成為我的樂事,善于挽成各種發髻,用發卡固定,常博得他人詢問學習,心中甚為得意。一天又被父親叫去,告知發髻是已婚婦女的發式,小女孩兒不允許再梳,否則剪掉長發,重新做人!于是從此再不敢挽發髻,婚后也從不挽髻。幼時父母對于生活細節的規范,讓傳統文化教育在我心中落地生根,雖然在生活中也堅強勇敢,但是于舉手投足的細節還是心有規矩、行有尺度,絕不越雷池半步。
如今,女兒正值豆蔻年華,也學父母的樣子把她叫到身邊,告知其“笑不露齒……”,話音未落,她早將小嘴里潔白如貝、密齊如石榴籽的牙齒露出兩排共計16顆,我生氣要走,她就圍著我轉圈讓我看她“笑就露齒”。我準備發揚光大的女容教育也只好到此為止。而她,正在步入一個形象致勝的時代,不露齒的完美微笑應該倡導,而不露足的要求似乎應該與時俱進、與時諧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