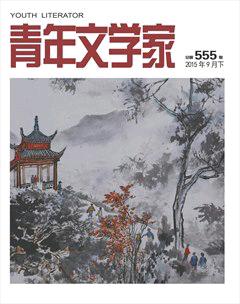戴望舒詩歌和其譯詩互文性現象的原因探究
沈菲
本論文為安康學院高層次人才專項項目“戴望舒詩歌創作與其譯詩的互文性研究”研究論文,項目編號:AYQDRW201225。
摘 要:戴望舒的詩歌和其譯詩在意象塑造和詩歌結構方面存在互文性現象,也因此人們常認為戴望舒的詩歌受西方文學影響頗深,但這一觀點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戴望舒作為創作主體本身的主觀選擇。本文嘗試從主體選擇角度來解析戴望舒詩歌和其譯詩出現互文性現象的原因。
關鍵詞:戴望舒詩歌;互文性;原因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7--01
戴望舒詩歌和其譯詩在意象塑造和詩歌結構方面均存在互文性現象,即“一個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納入自身的現象,這種關系可以在文本的寫作過程中通過明引、暗引、拼貼、模仿、重寫、戲擬、改編、套用等互文寫作手法來建立[1]”,比如戴的《煩憂》和耶麥的《天要下雪了》,戴的《古神祠前》和波特萊爾的《高舉》,戴的《我的記憶》與耶麥的《膳廳》。也因此人們常認為戴望舒的詩歌受西方文學影響頗深,是一定程度西化的產物,但在筆者看來,這種影響論過多強調了被動學習的關系,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戴望舒作為創作主體本身的主觀選擇。本文嘗試從主體選擇角度來解析戴望舒詩歌和其譯詩出現互文性現象的原因。
一、個人的藝術審美追求。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詩壇,伴隨著“五四”的新詩運動,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新詩宣告誕生。在以胡適為代表的早期白話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現代新詩呈現出了有悖于傳統詩歌的獨有特色。或是側重于客觀寫實,以白描手法真實再現具體的生活場景或自然景物;或是以托物言志的方式,表達內心的情感與思索,在詩歌形式上則脫離傳統詩歌的范式,呈現散文化傾向。在這種背景下踏上詩壇的戴望舒,對于新詩卻有著自己的見解與思考。對于表達直白的白話詩歌,戴望舒并不感興趣,相反,他覺得這種詩已脫離“詩味”,不再富有詩歌豐厚的內蘊與質感。在詩歌情感的表達上,他仍然傾向于傳統的斂與收,但如何能夠突破傳統范式,以新的形式來表達這種審美訴求——既有飽滿的詩情充盈沉淀在詩作之間,又不著古詩窠臼的痕跡;既不同于早期白話詩的直白,也不同于李金發象征詩派的晦澀與拗口。這一追求成為戴望舒在詩歌創作過程中必須思考的問題,他需要一種外在的力量給予他指導和方向。本身兼具詩人、讀者、譯詩者三重身份的戴望舒,于是將目光投向了西方詩歌,希望能夠有所收獲。
二、良好的外文基礎與廣泛的閱讀量
良好的外文基礎與廣泛的閱讀量,為戴望舒的詩歌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無論是在震旦大學學習期間,還是赴法留學之后,戴望舒對于學習的態度一直非常通脫,他并不拘泥于學校的規定課程,而是大量閱讀法國、美國乃至南歐詩人的作品。扎實的外文基礎,使得戴望舒無需借助翻譯,能夠直接欣賞并學習這些優秀詩歌的創作技巧。依靠著這種勤奮和努力,同時伴隨著個人藝術審美追求的積淀與成熟,戴望舒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詩歌藝術觀念。在此基礎上,他又以此為依托,繼續閱讀尋找符合自己審美追求的作品。在自我情感表達趨于內斂的中國傳統詩歌語境中,在西方詩歌的啟迪下,戴望舒的詩歌創作在內容與情感上都呈現出有別于中國傳統詩歌的西方現代色彩。需要注意的是,戴望舒對于西方詩歌的借鑒和學習,按照互文性理論來分析,即是戴與原作者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二者在主觀認識上達成了一種一致性。真實的詩情仍是戴望舒最為看重的地方,將傳統文學的積淀與西方詩歌技巧緊致結合,在此基礎上摸索和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藝術方向。
三、詩歌翻譯與詩歌創作的關聯性影響
戴望舒兼具著詩人、讀者、譯詩者三重身份,這在他的整個詩歌創作生涯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1926年到1945年,戴望舒共創作詩歌九十余首,但他的詩歌翻譯數量卻達到了兩百多首,寫詩與譯詩成為他詩歌創作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在詩歌創作道路中,戴望舒一直試圖為自己制作“最適合自己走路的鞋子”,以真摯詩情作為詩歌的核心內容,在表達形式上同時兼具中西方特色。帶著這種藝術審美追求,作為讀者的戴望舒,自然會選擇更符合自己藝術需求的詩篇進行閱讀、借鑒與學習。再從翻譯的角度來看,閱讀是翻譯的基礎,翻譯是譯者的又一次創作,大量翻譯外國詩篇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提升和鍛煉他的詩歌技巧與思維。作為讀者兼詩人,符合他審美要求和契合他心理需要的詩歌更容易進入他的視野范圍,在此基礎上進行翻譯,并與自己的詩歌創作對照和結合起來,使得二者齊頭并進,互為補充。無論是詩歌創作還是詩歌翻譯,戴望舒都在這個過程中實踐自己的詩歌創作理念,他力圖通過自己的詩作與譯詩來摸索中國新詩內容和形式的發展方向。
對于詩人而言,詩歌是其豐富精神世界的再現,詩情的表達與隱匿程度是詩歌質與味的關鍵點之所在。在戴望舒的藝術審美世界里:詩情是詩之精髓,詩是由真實經過想象而來,在表達自己與隱藏自己之間;要去除掉韻律、詩形等外在結構對詩歌的束縛,抽取出最純粹的情感,依照詩情的起伏抒寫詩篇。正因為如此,他在自己的創作過程中有傾向性的學習西方詩歌藝術同時結合中國詩歌傳統加以吸收和改進,選擇意象與結構為切入點進行具體的創作實踐。從實際的創作效果來看,雖未能完全實現其審美追求,但也基本使其理念在詩篇中得到了體現,這也是他的詩歌與其譯詩出現互文性現象的原因之所在。
參考文獻:
[1]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J]﹒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3月.
[2]王愛英.試論戴望舒的西方詩翻譯對其創作的影響 [J].中文自學指導,2008年第6期.
[3]郭思妍﹒法國象征主義詩歌藝術手法在中國的移植和再創造——以李金發、戴望舒為例[J]﹒考試周刊,2009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