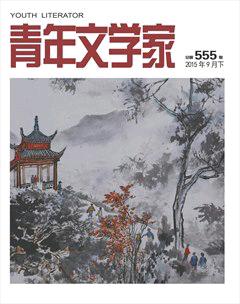從《西游記》與《神曲》中看中西近代世俗化人文觀對比
李博聞+++張子康
摘 要:《西游記》和《神曲》分別是東西方近古時期重要的文學著作,各自在創作過程中都采用了大量的宗教題材,同時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近代“人”的思潮的影響,作品中宗教形象出現了世俗化,反映了不同面貌的“人”的思想覺醒的特征。本文試圖從《西游記》及《神曲》所反映的近代宗教世俗化現象進行對比,從而可以有助于從文化上對中西交流進行把控,同時也有助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進行的東西方的政治經濟交融進行文化層面的分析。在文學層面上,同樣可以對《西游記》和《神曲》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為更好的挖掘兩部作品的文化價值,思想內涵提供助益。
關鍵詞:《西游記》;《神曲》;宗教;世俗化;近代人文思潮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27--03
1、彼此的旅程:救贖之旅與修心正道
1.1由地向天的升華和三教合一的“修心”
《神曲》中的旅程歷經了三個階段——地獄、煉獄和天堂,地獄為違反基督教各教律而被懲罰的罪人,煉獄是罪過較輕的應急懺悔的靈魂升入天堂的必經之路,天堂為神居之地,至高無上。而詩歌中的但丁則是在世的開頭交代為35歲時(人生的中途)誤入一座黑暗的森林(象征罪惡),由此陷入困境,經人指引完成地獄、煉獄、天堂的旅程。而維吉爾和貝阿特里切的指引則象征著由理性的指引擺脫人生的困境,最終超脫理性和上帝之愛合而為一的心靈路程。解除迷誤的良方最終還是轉向永恒的神來救贖。
而《西游記》則不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游記》的升華是通過修“心”來完成的。事實上,與其將《西游記》的故事看作是師徒四人西天取經的故事,不如把《西游記》歸為修心正道的經歷來的妥當。在《西游記》中主角孫悟空在章節標題中常以“心猿”來指代。但在第一章中,孫悟空海外求仙的經歷在章節標題被表述為“心性修持大道生”,學成歸來則被稱為“斷魔歸本合元神”。而孫悟空從“靈臺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獲得長生之道,從山門名字就可以看出與“心”有關“靈臺”“方寸”皆為心的別稱,“斜月三星”正是由“心”字拆解。最后孫悟空被封的也是消除傲慢,保持本心的“斗戰勝佛”,戰勝的除了取經途中的妖魔鬼怪,還有自己的傲慢和偏執。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西游記》更強調的是對“心”的修持。
當然因為同為戴罪之身,也有學者認為而這同為救贖之旅,學者王敏就這樣認為:“從民族文化層面看,《神曲》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是罪感文化,注重救贖過程;是內省式救贖, 強調理性判斷和懺悔的力量。《西游記》所代表的民間佛教文化則是樂感文化,反映了對富足自由極樂世界的向往;是外求式救贖,注重感性信仰”將而這同歸于救贖之旅,也很有道理,就原因而言兩者確有趨同之處。但是,不論是過程還是結果,二者都是不相一致的,所以還要區別看待。
1.2當“七宗罪”遇上“八十一難”
《神曲》中的煉獄由九層組成,除去凈界山和地上樂園,就是按七宗罪劃分的七成煉獄。較之于地獄,煉獄是已懺悔且罪過較輕的人洗脫罪孽的地方。和在地獄接受懲罰的人不同,煉獄更強調的是對悔罪者的磨練,借此擺脫罪惡,干干凈凈地升入天堂。在凈界山頂的地上樂園,維吉爾隱退,貝阿特麗切出現。象征著理性的力量還是有限,無法指引但丁直達天堂。在基督教教義中,這些惡行最初是由希臘神學修道士提出八種損害個人靈性的惡行,分別是貪食、色欲、貪婪、暴怒、怠惰、傷悲、自負及傲慢。到了六世紀后期,教宗艾文略一世將那8種罪行減至7項,傷悲歸入懶惰,自負并入傲慢,然后加入妒忌。他的排序準則在于對愛的違背程度。其順次序為:傲慢、嫉妒、暴怒、懶惰、貪婪、色欲、饕餮。總的來說還是教廷認可的宗教定義。
《西游記》八十一難和《神曲》中的地獄和煉獄中的受難如上文所述一樣屬于贖罪的過程,但和煉獄中單純的懲罰不同,“八十一難”還負有一個傳播佛教經典拯救處于蒙昧中的大眾的光榮使命,本身是用以將功折罪的“功德”。“八十一難”則是完成“功德”必備的磨難,單個的“難”不一定非得有明確的象征意義。除了唐僧犯的罪為輕慢佛法,孫悟空的罪過是攪擾天庭,豬八戒是調戲嫦娥,唐僧是輕慢佛法,沙僧只是打碎了琉璃盞,白龍馬燒了夜明珠就被告了個“忤逆”。比較基于品格而劃定的“七宗罪”,這罪過倒是清楚無比,各不相同,不過似乎并不妨礙他們被合在一起去取經。而且除了唐僧以外,其余四人都是天庭降的罪,完成佛門的功德也可以抵罪,可見佛道兩家在《西游記》并不顯得涇渭分明。“八十一難”也不一定能洗刷掉取經的四人一馬的什么“原罪”或劣根性,在西行的末尾,豬八戒在收服玉兔精后依然要找嫦娥敘舊,到了西天受封時還因為沒成佛而不平,可見原本的劣根性并未隨著取經的過程而消除,卻不妨礙他獲得功果。這就和《神曲》有所不同,《神曲》中煉獄通過“懺悔”得以進入的機會,通過“贖罪”得以通過,升入天堂。《西游記》幫助唐僧師徒度過八十一難的是他們自己,雖然可以借助神佛的幫助,但從根本上來說是唐僧四人一馬的不斷努力,才得到九九歸真的圓滿結局。
2、各自的對手:直刺教廷與神佛的異化
2.1東西方“神”的觀念的對比
在《神曲》中,天堂和地獄的形象描繪截然不同,地獄,煉獄的景觀十分具象化,但天堂的形象則明顯出現了虛化。如貝阿特麗切的形象就“盡管那條纏有米內瓦的枝葉的面紗已從她的頭上垂下”,卻“仍然不能令人看清她”,神圣得讓但丁無法直視。連歷史確有其人的查士丁尼帝在宣講古羅馬事跡時也是如此:“我說了這話, 轉身去向那第一個對我說話的精靈;看到了我這樣,他發出了比剛才明亮得多的光。好像熱氣把濃霧的屏障一塊一塊地啃去了以后,太陽由于光的強烈令人不能逼視,那個神圣的由于歡樂的煥發就像那樣隱藏在自己的光里,而且在這樣被光裹住,裹住時,如下一歌中所歌詠的那樣回答我。”全然不見清晰的實體。
在天堂的頂端,上帝的形象也只是一閃而逝,諸神和先賢也只是虛幻的靈體。這正是反映了天堂的神圣而純潔,上帝是一切的本質,上帝之愛是天堂一切運動的共同本源。陷于困境中的但丁最終也是依靠貝阿特麗切所代表的上帝的永恒的愛獲得最終的救贖。但上帝本身處在一種“不可說”的境界,至善至美的天堂也和人間大相徑庭。
《西游記》中的天庭又另有一番景象。書中寫道:“……只見那南天門,碧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寶玉妝成。兩邊擺數十員鎮天元帥,一員員頂梁靠柱,持銑擁旄;四下列十數個金甲神人,一個個執戟懸鞭,持刀仗劍。外廂猶可,入內驚人:里壁廂有幾根大柱,柱上纏繞著金鱗耀日赤須龍;又有幾座長橋,橋上盤旋著彩羽凌空丹頂鳳……”學者姜岳斌就如此評價:“《西游記》天界的具象性更表現為它實際上已是一個運作中的人類社會;作品正是按照中國的倫理原則把人間的一切搬上了天堂——它實際上就是封建時代的中國宮廷以及與之相關的其他社會生活場景的翻版”。天庭猶如人間的朝廷一般,是維持三界正常運轉的政府般的存在,任務就是依據“天條”維持世界的正常發展,本身談不上救贖眾生。真正起到“救贖”責任則另有西牛賀洲的西天佛界。如果說天庭是秩序和權力的中心,西天就是信仰中心。但這信仰中心也并非全然純潔無瑕,“八十一難”中就有菩薩的坐騎、童子因主人的疏漏下界為妖,為禍人間。就連法力無邊的佛祖也為阿儺,伽葉索要“人事”的行為開脫,又用“受用的品級”哄豬八戒“人”氣十足。天庭更是不堪,被孫悟空鬧了個天翻地覆,只得請佛界救場。當然《西游記》中的神佛自然高人一等,修為不易,佛祖就以玉皇大帝歷經無數次劫難才成為天帝,孫悟空卻沒修行多久來對鬧天宮的孫悟空加以勸阻。但這些神佛畢竟是靠修持和心性才成的功果,比不得基督教的上帝是世界的本質,唯一的至高神。甚至神和妖怪的界限也并不明顯,《西游記》作者吳承恩就借觀音之口說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可見神仙之于妖怪的不同,就在與心境的高低。師徒四人能成佛做菩薩,一是功德圓滿的回報,二是心靈境界達到一定層次。皈依佛門只是獲得積功德的機會,還需保護唐僧西去取經才能成佛,而修仙倒是只要有“九竅”就可以修
2.2.東西方近代“人”的觀念的思潮對各自舊觀念的沖擊
在這兩部作品寫作的時期,商品經濟在中國和意大利都分別迅速得到發展,城市的進一步繁榮激起了對市民階層的娛樂需求的滿足。一些肯定現世享樂,反對禁欲主義的思想開始流行。其中,“人”的觀念是兩部作品相通的地方。
但丁在詩中借貝阿特麗切對他的談話表示,他之所以要寫作《神曲》,就是“為了對萬惡的社會有所裨益”。故而這部作品本身是一部具有強烈傾向的作品。他將教皇和一些自己痛恨的佛羅倫薩人打入地獄,又在詩中闡述自己的見解,發揮基督教對世界的認識,質疑教士品性的同時又對教廷在解釋教義上的專制權力進行攻擊。除了具體內容外,用意大利與寫作本身也是對教廷表達自己的不滿。《神曲》中對人的重視還體現在對人物的刻畫描寫上,詩中的人物一反中世紀的刻板和僵化,呈現出極為生動的人物形象。在《地獄篇》第十首詩中,但丁將基白林黨魁法利那太描繪為墳墓間傲然挺立的形象:“他把胸膛和臉孔昂挺起來,似乎對地獄表示極大的輕蔑;我的導師用大膽而敏捷的雙手把我從墳墓中間向他推去,說道:‘你的說話要簡短。當我站在他墳墓旁邊的時候,他望了我一下,然后幾乎輕蔑地問我道:‘你的祖宗是些什么人?”這位人中豪杰盡管身困地獄,卻不曾屈服,反而顯得更為高大。
《西游記》則不然,它的傾向性模糊到學界對其主旨進行了持久的論爭。魯迅和胡適甚至認為它是“游戲之作”,即其創作傾向受到強烈的懷疑。《西游記》更多的是走了中國古代文論的一貫路子,展現了現象,卻不一定給予定義和回答。因而它雖然安排了唐太宗游地府借人情世故機緣巧合增壽二十年,西天對香火孜孜以求的設置,卻并沒有予以批判,甚至,他對這些神仙中的人情世故也不一定持否定態度。相反,在當時,和西方的人文主義一樣,東方“人”的思想同樣開始影響社會,而中國對于人的重視就體現在對“人”的“心”的探究。在吳承恩所處的明代的中后期,一批思想家提出重視“心”的觀點,有力地抨擊了當時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如泰州學派創始者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同為泰州學派的羅汝芳則提出順應本心,即符合天理之善,后期的何心隱更是進一步提出“育欲說”;同時期的思想家李贄則提出“童心說”,公安派的袁宏道也有“不拘格套,獨抒性靈”的論點。學者田同旭據此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吳承恩和明中葉以后一大批反理學的思想家、文學家是同時代的,他不可避免地受到明中葉以后反理學社會新思潮的影響。”而這種對于“心”的探尋正是近代“人”的思潮的體現。《西游記》很明顯受到了這些觀點的影響,神仙妖怪的法力來源于修持,但正如上文所言,成仙還是做妖怪,看的是心靈境界。性靈的提升在于頓悟,而不是死守經義,在《西游記》末,唐僧取到了無字經文,不禁大哭,孫悟空倒看得開,認為世界上本無圓滿之事,反過來勸唐僧。在這個情節里,孫悟空的覺悟就比經院派的唐僧高得多。
3、從《西游記》與《神曲》中看近代思潮下中西世俗化的宗教觀
但丁本身對地獄中的人也并非完全持否定態度,他對地獄中的帶審判的古代異教徒就十分尊敬。對于地獄中的受懲罰者也有自己的認知。但本質上還是將信仰和基督教教義放在首位,不脫中世紀神學窠臼。學者姜岳斌據此就論述為:“但丁在整部《神曲》中確實經歷了理性的輝煌,也確實找到了更高尚更美好的世界,只是信仰被推向極端時便排斥了理性而導致自身的悖論,這是但丁在天堂里的迷誤。”事實上,但丁所貫徹的是中世紀一以貫之的神學思想,盡管反對暴君和教廷的虛偽,但他的信仰是沒有發生動搖的。暴君和教廷也是后來早期人文主義者主要反對的對象,但無論是宗教改革還是人文主義,基督教的信仰是不變的。
《西游記》則正好相反,講的是神魔鬼怪,完全沒有對三教教義的遵循。孫悟空的師父菩提老祖講道是也是“說一會兒道,講一會兒禪,三教相合本如然”,傳下來的經文最后也說“功成隨作佛和仙”。仙和佛之間也相處融洽。就單一的道教或佛教而言,全然不遵經義,信仰就更談不上。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是三教合流的影響,二就是上文論述的人文思潮。
中西在人文思潮下文化層面的表征截然不同,歸根到底還是共同認知的差異。一直以來歐洲大陸就是合少分多,能夠將歐洲人聯系起來的只有基督教思想,中國則正好相反,自東漢佛教西來,道教建立,信佛信道的哪朝都有,真正能統一的只有政權。同時佛道兩家自身也在不斷改良,漸漸合二為一,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故而但丁因《神曲》成為“新時代最初的一位詩人”,西游記揶揄宗教,卻沒有就此翻起什么浪花。
4、結語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神曲》和《西游記》同為人文思潮下的產物,但各自基于中西文化差異而各有不同。《神曲》反對教會的虛偽,暴君的殘忍;而《西游記》則由“心”肯定人,強調信念而非信仰的堅持。兩者都客觀反映了各自文化領域下近代人文思潮的發展狀況和當時的思想面貌,
《西游記》與《神曲》分別是東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時期問世的著作。在有關神曲的研究中,相關研究呈現多元化態勢,從最早的人文主義思想觀到宗教觀、心理分析和西方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挖掘,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不小的提升,但在各個新開掘的層面如天堂觀,西式邏輯文化分析還有較大的探究空間,整體上還處于廣度有余,深度不足的階段。
而《西游記》作為我們中國著名古典小說,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重點關注的對象,在許多研究領域已經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從其文本各個方面的剖析到分析文本之后的作者意圖之爭(始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寫作社會背景、世俗化的中國式智慧和東方宗教觀分析,以及探究資本主義萌芽下的人文思潮等等向歷史,人文地理,政治,哲學等多個人文科學方面發展的多元研究,再到本世紀初逐漸興起的對以電影《大話西游》為代表的對《西游記》再詮釋文本的研究興趣,《西游記》的研究可以說是“浩浩蕩蕩,波瀾壯闊”。目前西游記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已經相當完備,許多學者由文本轉向研究《西游記》是基于以其文本為框架的神怪文化進行研究,難以出現革命性的顛覆性的研究成果,故而現階段單純的文本研究暫時沒有令人矚目的成就。對于《西游記》研究工作的繼續進行,在現階段暫未取得革命性成果的前提下,一般為“開源”發掘新領域繼續研究。
但在我國,將兩者串聯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還相對稀少,相關論文在中國知網的相關檢索中只檢出了不到十篇,完全不成單獨體系。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兩者文體,行文風格差異較大,兩部作品時間跨度也相對長一些;另一方面是由于神曲的中國讀者群相對薄弱,相關研究雖然有了長足發展,但整體依然稍顯不足。學界這種研究面貌并不是說對《西游記》和《神曲》進行比較文學研究是為時過早甚至缺乏研究價值。事實上,兩者的題材和內容都有很大的相似處,而它們之間敘述方式及思想傾向的不同正是涉及到東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性。在早期資本主義關注人性,面向世俗的思潮下,分析東西方文人對于各自神的看法,從而對東西方思想差異管中窺豹是完全可行的。還希望有關學者予以重視。
參考文獻:
[1]王敏.<神曲>與<西游記>救贖意識之比較[J].西安外國語大學學報. 2009(31).
[2]姜岳斌.<神曲>:理性的輝煌與迷誤[J].外國文學研究.1994(4).
[3]田同旭.<西游記>是部情理小說[J]. 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2).
[4]姜岳斌.<神曲>與<西游記>中天堂觀念的比較[J]. 外國文學研究.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