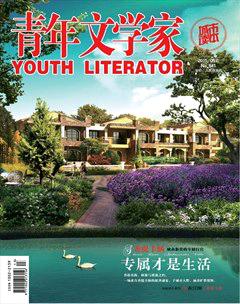劉慈欣:科幻小說與宇宙情懷
丘濂
隨著影片《星際穿越》的熱映,再加上《三體》小說的第一部英文版在美國上市,《三體》電影版進入前期籌備,劉慈欣再次成為科幻文學圈子里最令人矚目的作家。
2010年,《三體》第三部出版,將近150萬字的三部曲全部與讀者見面,劉慈欣已然奠定他在中國科幻文學中的地位。他被譽為“以一己之力將中國科幻文學提升至世界級水平”的作家。科幻文學研究者、北京師范大學吳巖教授告訴我,劉慈欣的成功離不開前人的努力,而他的確是金字塔的塔尖。“這是中國科幻文學里最長的一部作品,它一改我們過去作品線索單一、情節簡單、細節密度小等缺陷,呈現出波瀾起伏的面貌。中國的科幻小說一直被批評不夠成人化,不能擺脫歸類于兒童文學的尷尬,劉慈欣替我們實現了夢想。”劉慈欣1989年開始嘗試寫科幻小說,至今已20多年。他是科幻作家中為數不多的工作和生活在小地方的人。那是在山西陽泉的娘子關發電廠,劉慈欣擔任電腦工程師直到發電廠2009年關閉。一位去過那里拜訪他的記者這樣記錄:“那里四面環山,下午4點天就黑了,距離最近的大城市陽泉仍有40分鐘車程。不過因為運煤的大貨車動不動就堵成長龍堵上個三天兩夜,最好坐火車,兩個小時。娘子關北面有一片小山和一片小湖,旅游景點名叫‘張果老洞,河北人逢年過節喜歡過去轉轉。但是煤渣覆蓋在樹木與房檐上,天空時常陰霾。一切的一切和他小說里所描繪的浩瀚宇宙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我的工作可沒你想的那樣枯燥,也是需要創造力的。”劉慈欣對我說。由于精通電腦,他曾經設計過一個寫詩的小程序。“只需要輸進幾個參數,就能出詩歌,一秒鐘一首,比朦朧詩押韻。”他還編過一個軟件,在這個軟件里,宇宙中的每一個智慧文明都被簡化為一個點,最多時候,他在10萬光年的半徑里設定了30萬個文明,然后讓那臺286計算機花了幾小時來計算這些文明的演化圖景,這是他在《三體》中“宇宙社會學”觀念的雛形。身為電腦工程師,這讓他在90年代中期接觸了互聯網,“從此身在哪里并不那么重要,反而那里的幽靜能讓我安于創作”。
劉慈欣身邊的人很長時間都不知道他在寫小說。2001年,他的小說《全頻帶阻塞干擾》獲得中國科幻銀河獎一等獎的時候,還有同事對他說:“劉工,有個寫小說的和你名字一樣。”進入新世紀后,劉慈欣進步迅猛。“每一篇小說他都希望能有不同的嘗試。2002年的《朝聞道》實驗宏大的科技構思能不能搞,2003年的《詩云》探討美學問題,2004年的《球狀閃電》他看看自己能否駕馭長篇的結構。然后2005年他開始寫《三體》第一部,2006年在《科幻世界》上連載。他的長篇小說之所以能夠包羅萬象,是因為他能把以前短篇小說所磨煉的技能全部匯聚在一起,一個創意連接一個創意,讓我們驚嘆,你把整個宇宙都寫完了,其他作家該寫點什么呢?”吳巖這樣說。
劉慈欣白天上班,晚上時間寫作。支持他寫下去的是作為科幻迷對這種文學體裁的強烈愛好。“記得20年前的冬夜,我讀完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出門仰望夜空,突然感覺周圍一切都消失了,腳下大地變成了無限延伸的雪白光滑的純幾何平面。在這無垠廣闊的二維平面上,在壯麗的星空下,就站著我一個人,孤獨地面對著人類頭腦無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從此以后,星空在我的眼中是另外一個樣子了,那感覺像離開了池塘看到了大海。這讓我深深領略科幻小說的力量。”劉慈欣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而什么樣的科幻作品才算得上優秀呢?劉慈欣也繼續給出了答案:在忙碌和現實的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目光大都局限在現實社會這樣一個盒子中,很少望一眼太空。我曾問過10個人白天會不會出月亮,除了一位稍有猶豫外,其他人都十分肯定地說不會。現代社會同樣造成了人們對數字的麻木感,沒有人認真想過,1光年到底有多遠,而150億光年的宇宙尺度在大多數人意識深處同150億公里沒有區別。對宇宙的麻木感充斥著整個社會。科幻的使命是拓寬人們的思想,如果讀者因一篇科幻小說在下班的夜路上停下來,抬頭若有所思地望一會兒天空,這篇小說就十分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