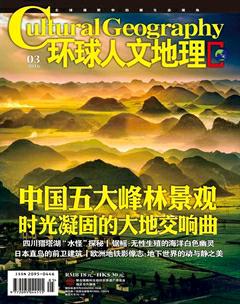日本直島的前衛建筑 自然與藝術就這樣完美結合
汪洋
直島上的“橢圓體”也被稱為“全球最難訂到的山頂別館”,據說至少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成功預訂到一間客房。
在“藝術之家”項目的著名作品“護王神社”中,樹影中搖曳的陽光,一下子灑滿全身,光明與黑暗,在空間轉換中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屹立在直島碼頭的小路盡頭、眺望著瀨戶內海的“南瓜”,可以說是“波點女王”、“日本藝術天后”草間彌生心境的真實寫照……

在日本瀨戶內海,點綴著三千多個各具特色的島嶼。盡管這些島嶼大多杳無人跡,但有一個卻顯得鶴立雞群,那便是堪稱完美結合了自然與藝術的直島。
1987年,日本倍樂生集團董事長福武總一郎投入巨資,買下了直島的南部地區,并攜手著名建筑師安藤忠雄,力圖打造一個屬于世界的文化村。從此,這座原本默默無聞、僅有3000多人的小島,開始了華麗變身。經過5年時間的打造,一所兼具美術館和旅館功能的“倍樂生之家”出現在世人眼前,建造這座奇特旅館的目的,旨在讓人們“在某一個場所,由時間來培育藝術”。而這顆藝術的火星,也迅速在這座美麗的海島上燎原。
在接下來的20多年里,受到“倍樂生之家”創作理念的影響,來自世界各地不同領域的藝術家紛紛踏上直島,創造出了一件又一件只屬于直島的藝術作品。
無數藝術大師的靈感,在這座睡夢般靜謐的海島上,迸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眾多充滿藝術氣息的前衛建筑,與海天一線的自然風光巧妙契合,令來到這里的每個人,都情不自禁地發出由衷的贊嘆……
全球最難預訂的山頂別館“植”于地下的建筑
直島位于日本香川縣北部,是日本瀨戶內海國家公園的一部分。數百年來,島上原住民一直以捕魚為生。1917年,三菱財閥在此修建了“金屬銅制煉所”,這才使直島迎來了繁榮。可是好景不長,由于煉銅廠產生了大量工業廢氣,污染了島上的土地和植被,無奈之下,居民們只好紛紛離家,外出打工。
蕭條和落寞籠罩著整個島嶼。不到幾十年,島上居民便銳減至3000多人,直至1987年,日本倍樂生集團董事長福武總一郎斥下巨資,打算與至交安藤忠雄一起,共同打造一個屬于世界的“直島文化村”。



“當代社會正淹沒在物質與信息之中,于是,我想創造一片遠離城市、遠離喧囂的天地。在這里,人們可以細細品味‘樂活的意義。”福武總一郎說,“與其去領略那些已被事先設計好的價值,不如讓人們與藝術直接連通,從而找到屬于他們自己的意義。”
“倍樂生之家”就是這樣一處“不食人間煙火”的心靈桃花源,它是直島上唯一的酒店,而整個酒店僅有十間客房,卻被譽為“人生終極之旅中,不可錯過的13家酒店之一”。這里的每間客房,均以清水混凝土打造,是典型的“安藤式”建筑風格;面朝瀨戶內海的落地窗加陽臺的設計,以及不安裝電視機的用心,則是為了讓住客能更好地體驗建筑、藝術與自然三者合一的心靈境界。

組成酒店的4座建筑物,分別被命名為“博物館”、“橢圓體”、“公園”和“海灘”。它們分別散落在直島的南部,且每座建筑物內都有可供留宿的房間。其中,最特別的“橢圓體”位于山頂,住客需要乘坐單軌纜車,才能從山腳前往山頂的別館。這里也被稱為“全球最難訂到的山頂別館”,據說至少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才能成功預訂到一間客房。
如今,20多年過去,“倍樂生之家”這處由安藤忠雄親手打造的新銳藝術聚集地,儼然成為了“現實中的超現實主義理想國”。
“倍樂生之家”當然不是安藤忠雄在直島上的唯一作品。2004年,由安藤忠雄設計建成的“地中美術館”,同樣是直島上最核心的建筑藝術作品之一。與立足于地面的傳統建筑設計有所不同,“地中美術館”有近70%的建筑主體被“植”于地下,并配合山丘坡度修建了入口,與周圍的自然環境近乎完美地融為一體。


縱觀整個美術館的外形,你會發現除幾何形狀的天窗之外,再無任何突起之物,這源于安藤忠雄的創作理念——建造一座從外面完全看不出建筑外形的地下建筑。此外,館中還特別設計了一個開放式的庭院,讓人從地底下抬頭,仍然可以看見天空。
奇特的是,整個“地中美術館”,只向人們展示了3位藝術家的作品,分別是:印象派大師克勞德·莫奈的《睡蓮》系列畫作、美國光影大師詹姆斯祇塔瑞爾設計的空間作品,以及美國藝術家瓦爾特·德·瑪麗亞的作品。

在通往“地中美術館”的公路兩側,以莫奈本人在法國吉爾韋尼的公寓花園為模板,再現了約400 平方米的“莫奈庭園”,這無疑與美術館的鎮館之作——莫奈的《睡蓮》系列畫作遙相呼應,同時也是為了更好地向大師致敬;而詹姆斯·塔瑞爾的《開放天空》,則讓人可以看到被“剪裁”出來的天空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幻的景象;在最底層,是由美國藝術家瓦爾特·德·瑪利亞所創作的空間藝術裝置——《時間、永恒、沒有時間》,展廳里安置了一個直徑2.2米的球體,以及27座貼金木雕,從日出到日落,作品會隨著光線的變幻,展現出不同的樣貌,讓觀者能在此展開對時空與生死的思考。
廢棄房屋的另類新生“藝術之家”的個性與自由
乘坐島上唯一的交通工具——迷你巴士,可以到達直島東部的本村。由于島上的年輕人大都選擇外出謀生,就連一些老人也搬往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本村內許多老房子便被空置下來。而這座被廢棄的鄉村,在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眼里,自然成為了一座寶藏。經過藝術家們的精心改造,一間間空置的房屋演變成了一件件極具個性的藝術作品,而直島上的“藝術之家”項目也由此悄然展開。
從1998年日本藝術家宮島達男創作的第一個藝術之家項目——“角屋”開始,在本村里所進行的,就不再是簡單重復的房屋改造了,而是將每一個空間都設置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并且還要與日本的傳統美學相結合。無論是大竹伸朗的“牙醫診所”,還是杉本博司的“護王神社”玻璃樓梯,抑或是“安藤博物館”,莫不如此。傳統與現代藝術的碰撞,使得直島上的建筑群綻放出別樣的魅力。
“角屋”是“藝術之家”項目的伊始。該建筑本體約有200年的歷史,藝術家宮島達男將原為榻榻米的地面挖成了一個淺坑,里面注入清水,并在水中放置了125個數字LED燈,以不同頻率進行倒計時。這些LED燈都是由島民自己調節的,表達了每個人心中對時間的看法。

“藝術之家”項目的另一座著名作品“護王神社”則是由一座廢棄的神社改造而成。“護王神社”在山上,是一座略顯神秘的吊腳樓小屋,由一排冰錐般的玻璃階梯連接,階梯上有一股細流緩緩流淌,讓整排階梯看起來猶如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山。這排階梯還有半截被藏于地下,但要進入地下密室,則需要繞道而行。密室的通道,狹小得只容一人通行,昏暗的密室中,可以看到剩下的半截流淌著涓涓細流的玻璃階梯。而從密室里往外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身后是狹小陰森的密室,眼前卻是開闊澎湃的海洋。樹影中搖曳的陽光,一下子灑滿全身,光明與黑暗,在空間轉換中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另外,由安藤忠雄親自設計,同時為了紀念他本人的作品而建造的博物館——“安藤博物館”也坐落于此。通過安藤忠雄的全新設計加改造,無疑為這座百年木造民居注入了新的生命與活力。過去與現在的呼應、木頭與混凝土的交融、光明與黑暗的對立,都將安藤忠雄在直島上的建筑精髓完美地融為了一體。事實上,在直島上,由于安藤忠雄的作品數量實在太多,因此對很多日本人來說,直島也被叫做“安藤島”。
“藝術之家”項目,除了向人們展示藝術家的作品,同時也大力呼吁島上的居民及游客保護日本的古建筑遺產。而在本村,不僅有著那些后現代式的藝術建筑,還有許多保留完好的江戶時代的老街及樓房。

波點女王點染的象征擁抱“世界盡頭的南瓜”
2014年,“波點女王”草間彌生的作品集在上海展出。其中,有一件被命名為“世界盡頭的南瓜”的作品,讓人印象深刻。而事實上,這顆散發著奇異氣息的巨大南瓜,最初被安置的地點,就是在直島上一條延伸至大海中央的小路盡頭。
著名藝術家草間彌生被稱為“日本藝術天后”,但她最聲名在外的稱呼則是“波點女王”,因為幾乎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充斥著密密麻麻的五彩波點。據悉,草間彌生如此熱愛波點,是由于她孤獨的童年。草間彌生從小便患有神經性視覺障礙,因此她所看到的世界仿佛隔著一層斑點狀的網。因為疾病的原因,草間彌生還常年飽受幻覺困擾,這甚至引發了她的自殺傾向。不過,當她握起畫筆后,世界便豁然開朗,而那由于神經性視覺障礙而造成的視覺影響,也被她充分利用起來,成為其一生的藝術主題。

都說天才與瘋子之間只有一線之差,用這句話來形容草間彌生再適合不過。從小飽受疾病折磨的她,唯有靠藝術來治愈自己,而面對外界對她作品的抨擊,她也坦然說,她承認自己是一位“精神病藝術家”。
自“藝術之家”項目展開以來,草間彌生便開始在直島上源源不斷地創作,而她那極富辨識度的作品,也一直是直島的象征。其中的典型,便是那顆小路盡頭的巨大“黑色波點南瓜”,在舊房子和舊草簾的烘托下,仿佛提醒著所有來訪者,直島不只是一個傳統民居保留地,更是一個新銳藝術聚集的理想國。
草間彌生之所以選擇用南瓜作為主體,是因為她在童年時期雖看不清世界,卻對世間萬物充滿好奇,她常常閉上眼睛,用想象力還原真實的世界,她最常想到的事物是光暈、鮮花和南瓜。從此,圓潤茁實的南瓜便成了草間彌生的最愛。她每天堅持在以紅黃對比色為背景的紙上畫圓點圖案,又將這種圖案用到造型類似南瓜的雕塑上,便成了著名的草間彌生風格。

屹立在直島碼頭的小路盡頭、眺望著瀨戶內海的“南瓜”,可以說是草間彌生心境的真實寫照:明黃色的背景圖案上點綴著黑色波點,再配合波浪般的形態,無疑還原了草間彌生心中那清晰又柔軟的世界……
在這個多少顯得有點與世隔絕的小島上,草間彌生的代表作品,在一片空靈的天地之間,安靜而鮮活地宣揚著“直島倍樂生藝術之地”的主題:藝術、建筑與大自然,將以最新穎的方式,巧妙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