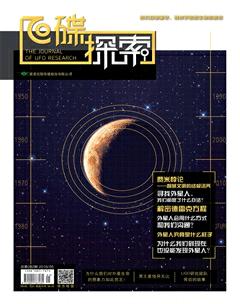費米悖論
陳厚尊
對中國的科幻迷來說,過去的201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劉慈欣先生的小說《三體》英文版終于為中國人捧回了科幻
界的圣杯。與此同時,《三體》系列小說中的許多概念與設定,比如三體問題、黑暗森林狀態、維度打擊等,都在網絡上引發了廣泛議論。透過這些議論,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那一條隱藏在整部小說背后的著名的科學悖論。對科幻界來說它就像是一個白洞,能夠不斷吐出激動人心的文學點子;而在科學界,它更像是一個黑洞,盤踞在人類文明的前方,使我們無法看清自身遙遠的未來。
費米悖論其實是一個早已存在的命題。早在1950年,著名的美籍意大利物理學家恩里克·費米在與人討論飛碟和外
星人的問題時,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Where are they? (它們都在哪兒?)要理解這個疑問的來由的確要費些口舌。在物理學界,費米先生一向以驚人的估算能力聞名,這為他留下了諸多逸聞趣事,比如,估算芝加哥有多少位調琴師,或者根據原子彈爆炸時產生的聲浪吹動紙片的距離估算原子彈當量等。正是憑借出色的估算能力,費米才脫口問出了那句話。他當時意識到的問題是:銀河系的尺寸只有區區10萬光年,而它的年歲已有100億年。智慧文明哪怕以光速的千分之一對整個星系展開探索和殖民,也只需要1億年(實際上人類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航行技術)。然而,所有的地質學和古
生物學發現都證實地球的生物圈已經自行進化和繁衍了數十億年,其間極少受到來自外界的干擾(恐龍的滅絕應該算一
個)。作為物理學家的費米顯然無法接受這樣一個矛盾,他覺得一定是哪里搞錯了。
究竟是哪里搞錯了呢?這便是60多年來科學家一直試圖回答的疑問。如今,我們列舉了形形色色的可能性,卻沒有一種得到觀測的證實。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科幻文學的幸運,因為它的每一種解決方案都可以催生出一大類科幻小說。劉慈欣先生給出的答案是:智慧文明彼此處在一種缺乏交流和信任的黑暗森林狀態。作為一名鐵桿《三體》迷,筆者承認這的確是一個能夠孕育出好故事的設定,但僅此而已。從現代天文學的角度看,這樣的設定站不住腳。要知道,從遙遠的地方判定一顆恒星是否孕育出了高等智慧文明其實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情。受制于熱力學第二定律,文明要生存下去必然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大規模的能量攫取手段(例如戴森球)難免會影響其所在恒星的光譜模式。即使是人類這樣的初等文明建立的天文臺(比如中國的郭守敬望遠鏡),也能夠同時測量數以千計的恒星光譜,并據此建立起完備的數據庫。此外,恒星物理學是一門相對成熟的學科,它差不多可以解釋我們接收到的任何恒星的光譜類型。相關工作與計算機結合后,自動化程度極高,完全無須人力介入。還有,美國航空航天局在早已報廢的開普勒空間望遠鏡的數據庫里發現了許許多多的類地行星,這些行星不僅在體積和質量上與地球接近,而且也運行在母恒星的宜居帶內。考慮到開普勒空間望遠鏡僅僅考察了銀河系的冰山一角,且手段單一、靈敏度差,銀河系中的類地行星的數目豈不是多得可怕?于是,這樣兩個截然矛盾的天文發現令費米悖論變得更加古怪和費解。這就好像我們在懵懂之間誤闖了一間屋子,那里本該有許多人,此刻卻一個人也沒有。身處這樣一間神秘的屋子,我們一定也會脫口而出那句話:“他們都在哪兒?”
也許,作為費米悖論最直接的推論,承認我們的宇宙的確處于某種大寂靜的狀態是符合奧卡姆剃刀定律的。后者指
出:任何不利于此推論的結論都將逼迫我們做出某些額外的假設,而這些額外的假設將在數學上大大降低那些結論的可靠性。比如《三體》里的黑暗森林假設,它給出了一幅貌似處于“大寂靜”狀態、實則擁擠不堪的外星文明觀。為此,劉慈欣先生給出的額外假設是猜疑鏈和技術爆炸。我們暫且不論這兩個假設在外星文明間的可靠性有多高,單就技術爆炸這個概念而言,就帶有濃濃的西方科技發展史的味道。
言歸正傳,我們回到“大寂靜”的話題上來。說到“大寂靜”,這個詞還是來自人們對“奧茲瑪”計劃執行多年后得出的無奈結論。“奧茲瑪”計劃由美國天文學家德雷克(即德雷克公式的提出者)主導,旨在通過無線電波尋找臨近太陽系的生物標志信號。該計劃自1960年4月正式啟動,監聽工作斷斷續續開展了三期,卻沒有獲得有價值的結果。盡管后來又實施了諸如“米塔”、“鳳凰”、SETI等計劃,也都一無所獲,不了了之。宇宙的這種不尋常的無線電靜默狀態似乎在向人們展示某種暗藏在寒冷星空背后的廣袤與荒涼。這樣的結果甚至極大地改變了20世紀許多天文學家對生命和智慧的認知。
難道說宇宙中真的只有我們在呼喚和尋找嗎?人類文明真的代表了銀河系最先進的生產力嗎?講到這里,我們不得
不提及所謂的“大篩選”理論(the Great Filter),它給出了一個造成“大寂靜”的可能原因。為此,讓我們嘗試考慮一個類似阿西莫夫筆下的銀河帝國那般宏偉的智慧文明。它是如此龐大,足跡遍及無數行星系,以至于尋找其文明的發源地都成了一個考古學難題。對那樣的文明來說,我們所能設想到的任何天災人禍似乎都不太可能觸及其根基。也就是說,那樣的文明幾乎堪稱不朽。不過很遺憾,費米悖論告訴我們,那樣的文明就好比是18世紀人們幻想出來的永動機,現實中并不存在。永動機不存在自然有熱力學的定律來保證,但費米悖論呢?“大篩選”理論認為,在銀河帝國文明的發展初期,必然存在一個或者多個“大篩子”,而智慧文明能夠跨越這些“篩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的文明是否已經跨過了那些“篩子”?為此,大篩選理論的提出者羅賓· 漢森給出了9個可能的備選項,依照時間順序它們分別是:①合適的行星系(即前面提到的類地行星);②可自由復制的遺傳大分子(如RNA 和DNA);③簡單的單細胞生物;④復雜的單細胞生物;⑤性繁殖;⑥多細胞生物;⑦能夠運用工具;⑧我們所在的水平;⑨星際殖民。
其中第八條是人類文明所處的水平。于是我們先前的問題變成了:那些“大篩子”究竟來自前面列舉的7條,還是盤
踞在第八條與第九條之間?考慮到人擇原理,我們完全不可能察覺到那些已經被我們跨越過的“篩子”。在這一點上,行星物理學的某些發現會變得格外危險,因為它允許我們看清那些被人擇原理遮蔽起來的重要信息。例如,開普勒空間望遠鏡的發現已經基本排除了第一條就是“大篩子”的可能性,因為它證明了類地行星在銀河系里絕非罕見。這是個糟糕的消息。更糟糕的是,類似的發現每時每刻都可能重現在火星的探索任務之中。如果哪天美國航空航天局突然宣布他們的火星車在火星表面成功發現了某種原始的多細胞生物化石,即便它只是顯微鏡下相當模糊難辨的一瞥,我們的處境都會大大不妙。因為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多細胞生物僅僅在太陽系里就中了兩票,若放眼廣闊無垠的星河,外星生物的種類簡直堪比恒河沙數!于是,傳說中的“大篩子”要么就是第七條,要么它正盤踞在人類文明的正前方,對我們虎視眈眈。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外星生物探索領域,沒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大篩子”處于人類文明前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毋庸置疑,目前我們的文明正處在一個快速變革的時代,而且該過程具有不可逆的性質,即使些微的減速與倒退對人類來說都會是一場災難。人類的智者不斷揭秘未知的科學領域,這個過程就好比人類與上帝玩的一場不能反悔的摸球游戲,每做出一項科學發現,便相當于從上帝的袋子里摸出一顆帶顏色的球,不同的顏色代表了不同性質的科學技術。其中有基本無害的綠球,比如太陽能技術、計算機技術;也有中性的白球,比如火的使用;還有代表危險的紅球,比如克隆技術、核技術等;當然,更有代表死亡的黑球。眼下人類還不曾抓到黑色的球,但這并不代表黑球不存在。一旦黑球現世,便是所謂的“大篩選”降臨的時刻。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危險、中性甚至是無害的球,一夜之間忽然變成了黑球,令我們措手不及。這樣的可能性的確存在,比如最近一直很火的人工智能技術。
到這里,我想很多讀者對費米悖論產生的原因已經有了自己的答案。沒錯,這本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開放性話題。不過換一個角度想,也許事情原本就沒有那么復雜,僅僅只是智慧文明間難以逾越的巨大時空距離造就了如今的“大寂靜”狀態。設想此時此刻,銀河系的另一端剛好有一個智慧文明在向太陽系的方向發送信號,我們要接收到它怎么也得等到8萬年以后了。人類文明能延續那么久嗎?只需看看眼下我們給地球的生態圈帶來了什么,不難發現這可能真的是一個問題。
基于同樣的考慮,某一時刻兩個文明之間要達成單向的對話,須滿足至少兩個條件:第一,足夠高的文明產生率;第二,足夠長的文明壽命。這里定義的文明壽命自文明掌握射電技術的時刻算起。在這個標準下,人類文明目前只存活了110年。非常不幸的是,目前我們對第一個條件的數值范圍仍然一無所知,就連第二個條件,我們也只能根據自身情況給出一個可能的下限。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極度簡化的數學規劃模型,在稍加分析后竟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無論宇宙間的文明產生率如何,文明都必須高于一定的壽命才可能達成單向對話,這個壽命的下限大約是1000年。我們可以定性地理解這個結果:兩個壽命過短的文明同時存在且達成對話的可能幾乎不存在,因為在信號尚未抵達時,其中一個就先滅亡了。可是,這樣簡單的結果忽然拋給我們一個巨大的疑問:費米悖論是否意味著智慧文明的平均壽命遠遠短于1000年?對人類文明來說,這個結果更加令人不安,因為它似乎暗示著那個致命的“大篩子”就盤踞在我們不遠的將來。
當然,以上這些討論完全有可能在無知的人群間引發某種末日的恐慌情緒,但這并非是我們討論費米悖論的本意。
相反,它應該變成一口警鐘,長鳴于每一個人類智者的心里,時刻提醒自己要尊重自然,居安思危,有所敬畏。古人云: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宿命論、機械論已被丟入歷史的垃圾桶,放眼未來,我們的文明無可限量。聯系當下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至少有一點會變得非常明確:如果人類社會還遲遲不改變自己的能源結構,繼續在碳排放的問題上玩弄政治手腕,相互推諉不作為,恐怕我們都將在有生之年目睹自己文明的“大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