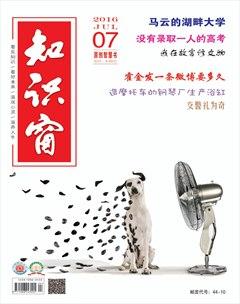我在故宮修文物
柯玉升
大多數人認為,修復文物是一件近乎復制古人創作的過程。這樣說沒有錯,至少在故宮的中生代匠人中還殘留著這種痕跡。而生于1978年的屈峰就不那么“規矩”了:“我不愿悶下頭來一輩子做匠人!較之匠人,我更愿做一名學者。因為匠人的工作更接近復制古人的創作,缺乏自我表達的空間。 ”
2006年,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碩士畢業的屈峰被招聘進故宮。進故宮修復的第一件文物,是給一個玉山子底座補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不一會兒工夫,他就做完了,師傅的評價卻是:“你做得太快了。”最不適應的是,他著迷于想象力和創造性,修復文物卻必須嚴格按照規律來,有時這近乎是一種限制。木器組修復的大多是實用性家具,有些審美價值不高。一件丑陋的家具,還得按照它原本丑陋的方式修復,如果修改了,就不是文物了。盡管有那種“改”的沖動,他也只好在內心說服自己:丑陋也是一種存在!我們做的工作是修復,而不是創造。修復,就得尊重前人的創造。
2016年4月,屈峰作為科長面試新一撥年輕人,給畢業生的提醒就是:“你們知道這個工作的性質嗎?想過自己的性格合適嗎?”一位年輕人說:“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觸文物,就心潮澎湃!”屈峰說:“這個地方可不能心潮澎湃,一心潮澎湃就麻煩了,而是要冷靜。”
屈峰從骨子里認同,文物修復的理念還得有“創造”的因子:不希望修復文物只按照傳統套路——體現人的價值。復活的意義,是要了解當時的時代審美是什么。格物格物,物是人創造的。傳承文化,要傳承這個。
因此,每進來一件文物,動手之前,屈峰都要和同組人先激烈辯論,這件文物要保留的到底是什么,再制訂修復方案。如某件文物破了個口,影響它最重要的審美價值,是補還是不補?他以日本修寺院為例,日本每隔三年就把這些寺院全拆了,重建一個,它的修建觀念是另一種認識觀——保留的是技術。
在屈峰看來,故宮的慢和外面的快,匠人工作的守和藝術創造的破,并不對立。真正的大師一定要接受所有,有海納百川的胸懷。
鑲嵌組的羅涵,本科就讀于中國地質大學珠寶鑒定專業,后在中山大學讀研。她進故宮工作的愿望是從事古董珠寶研究和評估,這樣的選擇多少讓身邊人難以理解,同學們嘆息如果她去珠寶行可以賺更多,父母希望她在離老家福建更近的廣東工作。
月薪幾千,羅涵沒法在衣服上花費太多。應邀參加同學會,她翻了一整晚衣柜,精疲力盡,一無所獲。這樣的時刻,羅涵也會羨慕那些從事珠寶商貿工作、年薪數十萬的大學同學。在故宮文保科技部工作,年輕人穿得最多的就是一件靛藍色的大褂工服,或者是系一條右側印有紅色字體“故宮博物院”的黑色圍裙。
2013年聯合國總部裝修,羅涵參與到19世紀70年代中國贈送給聯合國的象牙雕作品《成昆鐵路》的搬運項目中。《成昆鐵路》由八根象牙組合而成,雕刻非常精細,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現問題。羅涵負責材料的加固工作,這份重任是一般人“扛”不住的。
相比不“扛”,羅涵更愿意去“扛”事。“追尋心里最想要的,才是事。”這是羅涵近年來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故宮里外的世界截然不同,外面在變,故宮文物科技部固守的是不變,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我沒有迷失——現在我能跟那些浮動的欲望保持距離。”
2016年3月18日,兩岸三院同人書畫交流展開幕,墻上掛著一幅臨摹師陳露畫的紙本設色畫《蝴蝶》。羅涵在朋友圈貼了這張圖,并寫道:“跟文物在一起,生命被延長了。”
《我在故宮修文物》作為故宮90周年獻禮的紀錄片,在豆瓣獲得了9.5分的好評,甚至超過《瑯琊榜》,并正式登陸天貓魔盒。一部記錄故宮文物修復工作日常的紀錄片卻意外地在“90后”中走紅,1989年出生的制片人程博聞一語道破天機:“大國工匠需要的就是這種‘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吃大苦,甘寂寞,耐長期,還要敢于破與立的精神!這些,在這批年輕的故宮文物修復者身上都體現出來了,這也是為什么紀錄片能在‘90后中走紅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