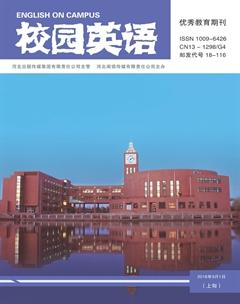淺析《到燈塔去》中的意識流技巧
劉鑫
【摘要】在《到燈塔去》這部小說中,伍爾夫很好的掌握了對意識流的創作技巧,同時在現實與回憶,當前與過去的穿插描寫中過渡自然。整篇小說從側面展現出了莉麗具備了作為畫師的靈活思維和豐富的想象力,充滿著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同時作者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伍爾夫本人所具備的縝密思維和創造力。
【關鍵詞】意識流 《到燈塔去》 布里斯庫
意識流是一種心理學的詞匯,它是19世紀由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創始人、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創造的,指人的意識活動持續流動的性質。他在1884年發表的《論內省意識流心理學所忽略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人類的思維活動是一股切不開、斬不斷的“流水”。他說:“意識并不是片斷的連接,而是不斷流動著的。用一條‘河或者一股‘流水的比喻來表達它是最自然的了。此后,我們再說起它的時候,就把它叫做思想流、意識流或者主觀生活之流吧。”后來,他又在《心理學原理》(1890)一書的第九章中加以詳盡的闡發。意識流這一思想為小說家運用意識流手法來展示人的內心世界,并通過展示人物的意識活動來完成小說敘事提供了理論依據。漸漸地,意識流就成為了一種表現人物內心意識的文學創作手法,通常以自我獨白的形式出現。西方現代小說史上,如弗吉尼亞·伍爾夫、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等都是擅長使用意識流手法創作的著名作家。伍爾夫最著名的意識流小說代表作之一《到燈塔去》就充滿著意識流的蹤跡
弗吉尼亞·伍爾夫曾以其熟練的意識流寫作技巧在世界文壇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英國著名的意識流作家。《到燈塔去》是伍爾夫的代表作之一,該作品全篇充滿著意識流小說寫作的痕跡。而在本文中著重對作品的重要角色之一——莉麗·布里斯庫分析其中所蘊含的意識流小說寫作技巧。
作者在《到燈塔去》中對莉麗的描寫充分展現了明顯時空交錯的景象,這是一個典型的意識流寫作手法。在小說開頭處,我們可以從對莉麗的輕描淡寫中了解到這是一名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莉麗在剛開始從事著繪畫這個職業的時就已經 33 歲了,而且在當時,這個職業是被看做是男人專利的,基本沒有女性選擇這個職業。“女人不可以畫畫,女人也不可以寫作”,縱使查爾士·塔斯萊反復強調,莉麗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他為拉姆齊夫人作畫的這份職業。與此同時,我們通過小說了解到莉麗一直不結婚,“夜晚已經消逝,晨曦揭開了簾幕,小鳥不時在花園里啁啾,她拼命鼓足勇氣,竭力主張她本人應該被排除在這普遍的規律之外;這是她所祈求的命運;她喜歡獨身;她喜歡保持自己的本色;她生來就是要做老處女的”。通過這些描寫,我們就可以感受到作者意識流的寫法技巧,黑夜和黎明交替出現,日子卻一天天過去,鳥兒在花園里鳴叫,而莉麗一個人在屋里做著她摯愛的工作,同時在心理上卻堅守她心目的這個一個,通過以上種種,產生了時空交錯的意象。
單純的從內容上看,伍爾夫對意識流文字和敘述的操控能力在寫作中體現出淋漓盡致,帕格森的“心理時間”理論也反復出現在小說的多處敘述之中,過去與現在抑或同時交錯,在別墅這一空間之中,或者是在其他場景中和莉麗腦中無盡的遐想互相碰撞,這些交替出現的場景更加迸發出了虛幻和現實的意境,從而把意識流的寫作手法很好的展現出來。在《到燈塔去》該小說中,即便作者想描述的內容以及人物沒有同一個時空里,但是這并不影響伍爾夫的場景描寫,仍然可以讓讀者提取和分辨出其中的信息,不會因為時空的交替出現而影響讀者的閱讀,此種寫作手法的確高明。
在小說第三部分“燈塔”中,作者對于對莉麗的描寫,意識流特征最為明顯也最為精彩。當她站在草坪邊望向海灘回憶拉姆齊夫人并試圖繼續創作夫人的畫像時。莉麗徜徉在她自己心目中的兩個時間里。伍爾夫將現實的場景與莉麗的內心世界完美的融合到一體,使得讀者對這種雜糅交錯的印象深刻。她心中的客觀時間貌似是在當下,而她心中的主觀時間卻早已回到飛到了十年前的場景。“你還記得昔日的情景嗎,卡邁克爾先生?” 莉麗問卡邁克爾,她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帶到了回憶里:“她又想起了拉姆齊夫人坐在海灘上的情景,那只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桶,隨著波濤一上一下的晃動;那一頁頁的信紙隨風飄散”;“正在從容不迫地作畫的莉麗覺得,似乎有一扇門戶打開了,她走了進去,站在一個高大而非常陰暗、非常肅穆,像教堂一般的地方默默地向四周凝視。從一個遙遠的世界,傳來了喧嚷的聲音。幾艘輪船化為縷縷輕煙,在遠處的地平線上消失了。查爾士在擲著石片,讓它們在水面上漂躍。”隨著思緒的慢慢回歸,從十年前漸漸回到了現實。這一段描述從觸覺、視覺、聽覺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地描述了在莉麗的心目中拉姆齊夫人的形象。倆人都處于默默無言的狀態,但是倆人之間的關系卻有一種朦朧美,通過這種時光交錯從而塑造出拉姆齊夫人在莉麗心目中不可玷污的、疏離卻又親近的形象。
伍爾夫提到莉麗用紅色以及灰色在畫布上以此來體現,這兩種顏色似乎就在暗示著拉姆齊夫人輕盈、纖細、扎實的性格,與此同時也暗示了自己脆弱、堅強的個性。這樣的顏色運用還包括了藍色代表著莉麗心目中拉姆齊夫人的一點點瑕疵,綠色代表著拉姆齊夫人試圖撮合但結局糟糕的雷萊夫婦。利用顏色、畫布還有莉麗的回憶,伍爾夫嫻熟地構造出了一幅意識流中客觀時間和主觀時間交疊的畫面,更加清晰地體現出了莉麗對于拉姆齊夫人的那種復雜情感,表現出莉麗在面對繪畫,面對拉姆齊夫人的時候既脆弱又堅強的敏感個性。諸如此類的意識流描述還有很多,它們就在莉麗和她的畫布之間靈活地進行著轉換,也同時提示著讀者客觀時間和主觀時間的變換。
最后,莉麗沒有失望,在她的翹首期望中,拉姆齊先生和他的孩子們到達了燈塔,也就是到達了整篇小說的核心意象———拉姆齊夫人的形象不僅代表著燈塔,與此同時,莉麗也完成了她的最后一筆,小說最終達到了高潮。“畫好啦,大功告成啦。是的,她極度疲勞地放下手中的畫筆想到:我終于畫出了在我心頭縈回多年的幻景。”
莉麗從來沒有考慮過她的作品會被掛在閣樓還是被漸漸遺忘,在她的心中,只有到達燈塔才是重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心愿,這才是她一直關注的。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莉麗成功地畫出了她心目中理想化、幾近完美的拉姆齊夫人。對于繪畫這個男性職業來說,莉麗也從來沒有因為繪畫是男人的專屬而影響自己的創作,最終她完美的到達了燈塔。
伍爾夫在《到燈塔去》這部小說中,對于意識流創作技巧的把握和掌控非常成功,并且自然的在主客觀時間,現實與回憶,當下與過去中來回穿梭,穿插描寫。整篇小說展現出了莉麗無窮的想象能力以及靈活的動腦能力;與此同時他也從其他角度充分說明了伍爾夫本人所具有的創造力和縝密思維。因此,從意識流寫作技巧的角度對莉麗進行全方位的賞析,從而能夠讓讀者真正領略到伍爾夫筆下這個充滿幻想而又栩栩如生的角色。
參考文獻:
[1]James,William.What is an Emotion?[J].Oxford:Mind, 1884(9):188-205.
[2][法]柏格森.吳士棟譯.時間與自由意志[M].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135.
[3]伊麗莎白·鮑溫.小說家的技巧[J].北京:世界文學,1979(1): 276-310.
[4][英]弗吉尼亞·伍爾夫.瞿世鏡譯.到燈塔去[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5]Rachel Bowlby.Virginia Woolf:Feminist Destinations[M].Oxford:Basil Blackwell Ltd.,1988.
[6]李森.評弗·伍爾夫《到燈塔去》的意識流技巧[J].外國文學評論,2000(1):62-68.
[7]秦紅.永恒的瞬間《到燈塔去》中的頓悟與敘事時間[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2):37 -40.
- 校園英語·上旬的其它文章
- Vege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s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last 28,000 yrs: A high—resolution pollen record from Valikhanovsection, Kazakhstan
- 論國際商務英語翻譯的多元化標準
- Work Ethics and General Morality
-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Edible Landscape in Rural Tourism: A Case of Dendrobium Landscape in Pu’er City
- 創傷理論視角下的《藻海無邊》
- 從格萊斯的會話含義理論的角度分析《當幸福來敲門》中的人物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