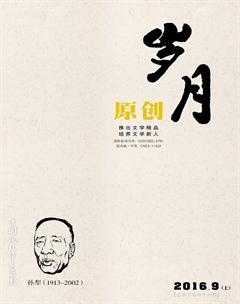老家三集鎮的那些記憶碎片
陸勤方
大通,作為一個地名,緣起于清乾隆年間由同里募款建造的三孔石板橋——大通橋。作為一個行政區域名稱,1950年5月劃歸嘉善縣建鄉,因鄉政府駐大通橋集鎮,故名。1956年,雙溪鄉并入。所以,在我的記憶中鄉里有三個集鎮:大通橋、雙石橋(雙溪)、潮泥灘。
自小到大,除了大通橋,因為從小學到高中,幾乎每天都在那讀書,對其他兩個集鎮的了解其實是很少的。只曉得,雙石橋有個廟,逢著日子,祖母、母親她們要去燒香。即便是在狠抓階級斗爭的歲月,她們也會偷偷摸摸地去。
大通橋作為鄉政府駐地,其實位置不是很合適的。一河之隔就是平湖縣境了,估計是原屬平湖所轄的原因,我們讀中學的時候,大通中學里有一部分的學生是從隔壁平湖縣秀溪鄉來的。集鎮很小,就南北一條街,原來是鋪石條和石板的,后來都改用小的水泥方磚。每到下雨天,小方磚不平整,不當心會濺起一腳污水來。
我家的屋后菜地里,因天天下雨,母親就深挖了幾條溝排水。沒曾想挖到了一層鋪墁得挺整齊的青磚,翻開來,竟有不少的銅錢,大大小小的散落著。所以,我們就趁著農閑,偷偷地把房屋前后左右的菜地全翻了一遍,還真挖著了小半抽屜的銅錢、銅版,也有幾片雕鏤著人物的銀質插頭。我偶爾抓一小把銅錢去舊貨店賣了,就為午飯時到煙雜店買什錦菜、蘿卜干吃。直到今天,腦海里還能清晰記得店主是一個胖胖的叔叔,眼睛圓圓,掛著很明顯的眼袋,不笑,遞過稱盤讓我放了銅錢,稱了稱,二角一,他說著就端著走進身后的一個小門,一會出來,點了錢給我,然后又在柜臺的本子上記上。
在小鎮上,還有一家文具店,也是書店。除了去買鉛筆、本子外,買得最多的是小人書連環畫。那些銅錢換了一段時間的什錦菜、榨菜外,而今算來最值得的是換了幾十本小人書,有八個樣板戲的,還有《半夜雞叫》《半籃花生》《敵后武工隊》等。那時,我們把這些小人書都當寶貝似的,整齊地藏在床底下的抽屜里。床是老式的雕花床,母親說是上代人留下來的,還跟父親計較沒睡過新床呢。
再去大通橋,石橋早沒了,小水泥方磚的街道都鋪澆成水泥地了。學校,從小學到高中讀書的學校,一半改建成廠房,一半改做集貿市場了。可以認領的,只有兩株高大的銀杏。一直很奇怪,怎么會有這樣兩棵大樹。記得校園的角落里還有幾株后來曉得叫黃洋的,葉子小小的,用力一折會有“叭”的一聲,清脆。估計這地方原來是大戶人家的,或者是寺廟什么的,是個好風水的地,前面一個寬闊的漾心,自南而來的河道和東西向的石碑涇交融后,一直往東幾百米再北折。
還是說說潮泥灘吧。在姑母出嫁之前,我對潮泥灘是陌生的。堂哥去賣過幾次泥鰍,換了點赤砂糖回來,兄弟幾個都用手指頭蘸著解饞,真甜。堂哥要比我們大得多,因為家庭成分高,啥好事都輪不到,只能翻地皮做農民。其實,堂哥很能干的,家里養豬、河里捉魚,都行。堂哥要結婚那年,我跟著去捉魚。每天月上柳梢,我們就去野圩頭的河灣里,撥開水葫蘆,用竹竿把一串串的麥弓塞到河底,再灑一把油香的菜餅。第二天天沒亮,我們就領了個撈魚的海斗,一串一串去收麥弓了。堂哥張的是大麥弓,裝在弓上的是南瓜葉子。本事在蘆圈上,選有韌性的蘆竿,切成圈圈,晾幾分干,然后卷了南瓜葉,套在用毛竹竹枝削成的弓上。一串麥弓五個,每天去放十來串,所以,天天早上都能撈到魚的,而且都是不小的草魚、鯉魚。最多的一次,一串麥弓上掛著三條三五斤重的大魚。堂哥辦喜酒,桌面上的紅燒魚塊都是我們一起捉來的。
姑母出嫁的時候,我們兄弟幾個是作為娘家人跟著去的。天氣挺好,比堂兄結婚時候又多了放百響、爆竹,陪嫁也是用船載的,多了臺縫紉機。噼里啪啦一陣百響爆竹以后,我們就出發了。姑父家在潮泥灘集鎮附近,所以,吃了午飯后就跟著幾個大人一起去逛街了。好像也沒有啥新鮮的,跟大通橋差不多的一段街,幾家店,不是賣布的就是賣扁擔、籮筐的,不一會就從街的這頭逛到那頭。
高中畢業以后,我就離開了老家。多年來偶爾會乘坐途經潮泥灘的客船,直到客輪航線改道,再后來是修路通了公交汽車,就再沒有去潮泥灘的街上走過。記得在學校做老師的時候,也不知是怎么說到潮泥灘的,有個學生問了這樣的問題:在潮泥灘能看到大海嗎?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問,他說暑假在乍浦的海灘上他看到了大海,而且是好大好大的海,不過海水是渾黃色的。
在潮泥灘能看到大海嗎?好有趣的問題,有趣得至今都忘了我當時是如何解釋和回答的。前段時間回家,聽母親說表弟翻建了新樓房,準備去吃進宅酒。到時候倘若有空,真該再去潮泥灘的街上走走,看看已經衰落了的老街舊房,聽聽已經漸行漸遠的時光和鄉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