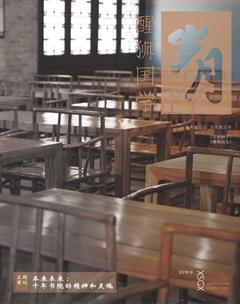傳統文化到底怎么了?
徐川
傳統文化怎么了
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形成了很多思維定勢,一提中華文明就是源遠流長,一提中國版圖就是地大物博。其實無論是歷史還是版圖,我們都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論文明,我們更加無法進入前三甲。第一名是現在日子過得不太平的地方伊拉克,第二名也不是中國,是尼羅河邊上的埃及,第三名是印度,第四名才是中國。但是,最早輝煌不代表持續輝煌,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中華文明就這么一直笑著。埃及和兩河文明已經煙消云散,古代印度不知所終,只有中華,綿延至今,一脈相承,成為唯一。我們這里提到的一脈相承有兩個含義,一是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是子孫相繼的,不是中途換人了,甚至膚色都換了,這就不叫一脈相承;二是這片土地上的文化習俗、語言文字是彼此聯系的,字形有變化,類型沒區別,比如繁體字到簡體字,這是簡化,不是顛覆,更不是從表意文字變成了表音文字。
從傳承的種族到文化的內容。我們就是那些曾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的先民們的直接后裔。我們仍然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是華夏兒女;我們使用的是流傳千年的漢字,文化的基因沒有發生變化。夏朝的家國一體,如今還是;商朝的祖宗崇拜,如今依然;西周的宗法制度,影響猶存。盡管在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過多次民族融合,但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構架從來沒有發生過改變,以華夏文明為主體的文化結構也從來沒有產生過動搖。所有與華夏文明接觸、碰撞和沖突過的少數民族文化,最后都被融進到華夏文明中,成為推動和豐富華夏文明的動力與新鮮血液。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突然有一天,我們引以為傲的傳統文化就成糟粕了,我們就開始討厭自己的傳統了,就開始憎惡自己的文化了,于是開始跟傳統算賬,開始跟文化決裂。
中國傳統文化經歷過兩次大的清算,面臨著一個大的困境。所謂兩次大的清算,一次是新文化運動,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所謂一個大的困境,是指在市場經濟時代,傳統文化沒想好何去何從。我們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根植于我們腳下的土地,因為我們是農耕社會,所以我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所以我們聚集而居,重視血緣,重視倫理,所以我們安土重遷,講究葉落歸根,所以我們有家庭、家族、民族、單位、集體、組織。但是如今不是小農經濟的時代,市場經濟也不是脫胎于農耕文化,是商業,是交換,是貿易,強調的是個體,是私人,是財富,是資源,所以我們的傳統文化需要去思考如何去對接另一種文化類型上誕生的經濟形態和價值標準。
傳統文化怎么看
百花齊放是當今世界的主題,然而我們的問題在于目光一直盯著西方,全然忘卻了手中的饕餮盛宴。其實,吃的經驗告訴我們無論是熱狗還是煎餅果子,是否心滿意足不是看著對方的咀嚼和吞咽,是看自己的胃口是不是適應,是不是溫暖,是不是妥帖。確實,世界這么大,應該去看看。熱狗之所以好像比煎餅好吃,往往是因為沒怎么吃過熱狗。真的走遍世界了,也許就沒那么偏激了,沒那么極端了,一山望著一山高不是動物才有的虛幻和假象。
說三個比喻,來說說兩次清算和一個困境。
第一個,關于倒臟水。民間有個說法,叫潑臟水連孩子一起潑掉了。這本是玩笑話,但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就是如此。倒澡盆不但把臟水潑掉了,順帶把孩子也倒掉了,最后干脆把盆給扔了。其實我們缺少點兒反思,所謂的臟水,就是真的臟么?臟與不臟,標準在哪里?以別人的眼光或者視角為標準么?那么問題又來了,我們何以憑借臟水在那么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一枝獨秀?莫非很久以來,別人的水還不如我們?
第二個,關于器官移植。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出了問題,血液有問題,有人說那就透析吧,有人說這治標不治本,還是要換器官,這樣才能保證血液不再有問題。后來發現只換一個器官還是不能保證血液的純正如一,有人說那就全部器官都換掉,最后發現,我們成了第二個別人,這就是我們想要的答案嗎?還有,即使想成為別人,就可以成為別人嗎?劉邦曾經給老父親在長安按照老家豐邑重新復制了一個村莊取名新豐,連從老家運來的雞犬都能找到各自的門戶,“雞犬識新豐”傳為佳話,然而這個一模一樣的村莊還是沒能成為第二個豐邑,很快消失在長安的建筑特色里。
第三個,關于樹葉對比。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如果是比較兩株樹,不會有人讓你一片樹葉一片樹葉去比較,因為每片樹葉的紋理都不相同,所以每換一片樹葉,就會下一個結論,這就是沒有看到本質。真正的比較要看深刻一點,要看到樹葉形狀不同、樹干也不相同,然后再深刻一點看到樹根不相同,種子不相同,土壤環境也不相同。因此,觀測我們的傳統和文化,永遠不能脫離生長于斯的土壤和土地,這是得出客觀結論的基本前提和邏輯起點。
傳統文化怎么辦
先說說反面素材,再說說正面未來。
只要在風景區的大門口處給父母磕個頭,全家人就可以免門票——如此別致“一景”,出現在河南駐馬店,引起了大家的熱議。景區這一做法的初衷無可厚非,一方面是為大眾提供公益性的福利,讓大家能夠免去門票,欣賞風景;另一方面弘揚傳統文化,重新激活“孝道”傳統,重現傳統文化的魅力光澤。但是給父母磕個頭本是平常事,現在卻需要用利益去驅使,成為博人眼球的噱頭。我們不得不思考:傳統文化是不是離我們生活已經有點遠了?我們是不是已經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
無獨有偶,再看一個工程。2010年10月30日,由中國倫理學會慈孝文化專業委員會開展的“中華小孝子培養工程”在北京啟動。該工程計劃用五年的時間在全國培養百萬中華小孝子,為全國億萬孩子樹立道德榜樣。輿論又是一片嘩然,孝子竟可“批量生產”?孝行竟然“工程立項”?孝心竟要國家培養?五年過去了,這樣一項工程無疾而終了,或者從起名叫“孝子工程”的時候就注定要失敗了。中華小孝子工程“看起來很美”,但不符合孝心孝行培養的現實,沒有家長的以身作則,沒有社會風氣的弘揚引領,沒有內涵的與時俱進,沒有孝道的土壤環境,放衛星大躍進式的孝道教育只能是徒勞無功,甚至徒增笑柄。
目前,國家已經把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列為法定節假日,讓我們能夠有時間思考、琢磨和討論這些傳統的節日。然而,在節日氛圍的營造上尚需我們去下點功夫,千萬不能讓“中秋節”變成了“月餅節”,“端午節”變成了“粽子節”,文化節變成了旅游節。端午時節,一家人攜老扶幼看看龍舟比賽,給孩子講講屈原的故事,讓孩子學學“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守;中秋時節,和老人孩子小小團聚,一起賞月分享親情,如此的潛移默化和言談舉止之中,尊老愛幼的種子已經悄悄萌芽生長……
我們不可能在別人的歷史里找到自己的出路,一個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在別國的文化里找到精神家園,我們當然也永遠無法拋棄與生俱來的傳統基因和文化烙印。當《功夫熊貓》《花木蘭》風靡全球的時候,當含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題材被反復引用的時候,當關于國學的書籍持續暢銷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國人復歸文化本源的現實表象和自覺選擇。黨的十七大報告也指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鑄造中華文化新輝煌,必須依托歷史、立足現實,尊重過去、面向未來,善待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通過挖掘整理和科學揚棄,使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得以延續,始終保持中華文化的鮮明個性和獨立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