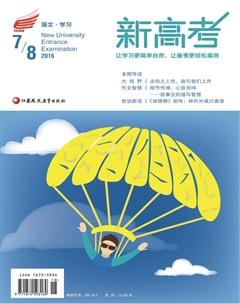初冬,我從壟上走過
孫青松
初冬,我從壟上走過,微寒的野風撲面而來。我又撲進了原野的懷抱。農田、農機、井房、河流、溝渠、村莊、石橋、坑塘、土路、林木、秸稈、荒草、野鳥、羊群、牧人……這些我熟悉的鄉野元素,構成了簡樸的鄉村冬日圖景,烘托出秋收冬藏的農業時令氛圍。這片鄉風濃郁的天地里,沒有都市彌漫的商業氣息,沒有超市和購物中心討價還價的嘈雜人語,沒有高分貝的音響鼓噪。在開發商看來這里荒涼不宜居,沒有開發的前景,沒有升值的空間,而在我眼里這里是一處風清氣正的歸屬身心之地;在生意人眼中這里沒有值錢的東西,沒有稀奇的物什,而在我心里這些土里土氣的風物,清靜的鄉村慢生活……
初冬,我從壟上走過,視野多么開闊!沒有城市樓群參差不齊的空間切割,我又看到了久違的地平線,看到了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的朝陽和從地平線上緩緩沉沒的落日。置身于壯觀的日出和輝煌的落日交替的平原上,我胸懷坦蕩,豪情萬丈!身為鄉村游子,踩踏著羊腸小道上軟綿綿的干枯落葉和毛茸茸的沒足黃草,呼吸著泥土的氣息,俯視淳樸的大地,仰望純凈的天空,我有回歸田園的感覺。這樸素的鄉路上,沒有人流、車流的洶涌裹挾,沒有紅、黃、綠信號燈的頻繁指令,沒有電子眼防不勝防的窺視與偷拍,沒有交警膽戰心驚的攔截盤查,我行我素從容不迫;這蜿蜒的土路旁,沒有水泥森林的逼仄擠兌,沒有商業廣告的聲浪嚷擾……
初冬,我從壟上走過,目光和心靈被鄉風鄉韻洗禮著。躑躅在這原生態的阡陌上,我又有了腳踏實地的體味。一塊一塊的炕地,陽光下泛著溫暖的土色;一方一方的冬麥田,排列成精致的垅行。霜凍下依然蔥綠的麥壟,詩意地彩繪出大地優雅的肌理,流淌著農耕文明的韻致。暖色的土壤上,長著青青麥苗兒,這是多么美妙的搭配,多么默契的組合,多么動人的景觀啊!立于地頭,我沒完沒了地徘徊;進入田間,我永不厭倦地瀏覽。每株麥苗,都讓我愛撫有加;每垅麥行,都讓我觀賞不夠;每方麥田,都讓我陶醉不已。鄉村是我的故鄉,田同是我的追尋,冬麥是我的“秀兒”。多日未雨,天干路響,土地龜裂,冬麥干渴,下一場大雪該有多好!那些曾經被秋季青紗帳遮蔽著的墳塋,在當下空曠的平原上凸現。已作古的村民,就長眠在這饅頭狀的土墳里,他們的亡靈安詳地堅守著這片積淀著農耕文明的田野。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葬于斯,也許是村民最推崇的生命軌跡。我對曠野里這些聚散有致的土墳,充滿緬懷和敬意。農作物不絕,農耕不止,農業不休,農耕文明不息。
初冬,我從壟上走過,趁著黃昏我返回蝸居的城郭,活像一只投火的飛蛾。歸途上,我沒有荷把鋤頭在肩上,沒有老牛同伴,也沒有聽見牧童歌聲和短笛吹響,卻仿佛聽到張明敏那純情的歌唱在鄉野飄蕩——哼一曲鄉居小唱,任思緒在晚風中飛揚,多少落寞惆悵都隨晚風飄散,遺忘在鄉間的小路上。返程中,我沒有看見天邊飄過故鄉的云,身邊只吹過鄉野的風,卻感覺好像費翔那蒼涼的唱腔在耳際回響——歸來吧,歸來喲,浪跡天涯的游子;歸來吧,歸來喲,我已厭倦漂泊。我已是滿懷疲憊,眼里是酸楚的淚。那故鄉的風和故鄉的云,為我撫平創痕……
(選自《華夏散文》2015年第11期)
亮點品味
文章的特色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匠心獨運開篇新,用“初冬,我從壟上走過”,開宗明義,總起全文,激發讀者的興趣,引起讀者思考,有下筆引人之效;“微寒的野風撲面而來”,猶如初展之冬色,為全文設置了詩意的背景,令人一見鐘情。二是緊扣現實巧開掘,文章沒有停留于對壟上生活的回憶與贊美上,而是重點寫壟上景色,通過這一景物形象,展示了那個時代農村質樸、純真的生活,也贊頌了農村互助團結、和諧相處的美好品質,傳達出作者對自己的故鄉、黃土地以及農村溫馨生活的感悟。這種擇取重點的表現技法,很值得我們學習。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托物言志”的寫法,一方面增強了散文的含蓄美。含蓄,即富有暗示性、朦朧性,意在言外,給讀者留下豐富的想象的空間。散文中描寫的事物,已經不是那樣一個具體的個別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具有哲理性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