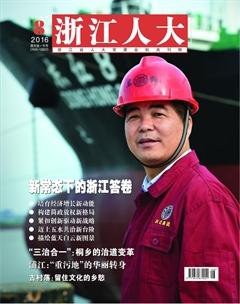特定問題調查回眸
文宗
2016年6月8日,江西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江西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成立食品安全生產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攤販問題調查委員會的決定》。在省級層面開展特定問題調查,有評論稱江西人大此舉“開省級人大先河”。
特定問題調查是監督法確定的人大常委會7種監督方式之一,被稱為人大監督的“重磅武器”,一般不輕易使用。與人大審議報告、執法檢查等不同的是,特定問題調查需要提請人大常委會成立專門的特調委,作為調查實施主體并獨立開展工作。到目前為止,全國人大常委會尚未成立過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
議會對政府的調查起源于英國,有的研究者稱之為“國政調查權”,有的稱之為“議會調查權”,主要指議會所進行的有關國家重大事宜的調查,區別于行政或司法部門所進行的一般調查。國外許多國家的憲法都賦予議會調查權。如德國的憲法規定:“聯邦議會有權利、并在四分之一議員提議下有義務設置調查委員會。”在美國,對涉及總統和行政機構的重大事件,國會有權組成“特別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即使缺乏憲法的明示規定,該項權力也被認為是立法機關的一項隱含憲法權力。
特定問題調查權早在建國伊始就被引入我國憲法。1954年憲法第35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必要的時候,可以組織對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遺憾的是,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刪除了這一規定,直至1982年憲法才恢復這一法定職權。在憲法和有關法律繼續賦予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特定問題調查權的基礎上,1986年地方組織法,增加了一款條文:“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組織對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的陳斯喜,就曾撰文指出,特定問題調查不是一般的調查研究,而是對某些重大問題所進行的法律調查。陳斯喜認為,“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這一程序一旦啟動,監督就必須要有結果”,“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是一種有很大威力的、有效的監督手段,是深化人大監督的重要措施。遺憾的是,法律規定的這一易于取得成效的監督手段,目前在實踐中卻得不到重視,使用得很少”。
“使用得很少”的特定問題調查權,遲至20世紀90年代方才啟用。據《人民之友》梳理的“地方人大常委會特定問題調查案例”顯示,整個20世紀90年代,在湖南省范圍內,有“1993年3月,湖南沅江市人大常委會就教育問題組織特定問題調查;1995年3月,沅江市人大常委會成立棉花購銷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等8起特定問題調查。
特定問題調查一經“發力”,往往能取得較好的監督效果。
較早引起社會較大關注的特定問題調查,出現在1997年。是年,湖北省荊州市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雜交水稻種子經營情況進行調查。通過調查委員會的調查,該市人大常委會認為地方政府及其部門在雜交水稻種子違法經營過程中存在制止不力、執法不嚴的行政責任,因此責令相關部門分清責任后嚴肅查處。
2000年,合肥市人大常委會首次設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對“汪倫才案件”實施監督,查清了“汪倫才案件”的真相,還汪倫才以清白,使普通民眾的合法權益得到維護,涉案責任單位和責任人得到查處,維護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尊嚴,提高了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的權威,社會反響強烈,全國多家新聞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或轉載,其中《合肥晚報》的“汪倫才案件系列報道”還被全國人大評為2001年度宣傳人大制度好新聞一等獎。
2007年,湖南郴州市人大常委會成立了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就“郴資桂高等級公路的經營權轉讓問題”開展特定問題調查。2009年,市政府根據市人大常委會的建議,收回了郴資桂高等級公路的經營管理權。
2014年,浙江省云和縣人大常委會首次啟動特定問題調查,該縣人大常委會根據特定問題調查報告,作出了《關于盤活存量提高資金使用績效的決議》。決議的實施,取得了多贏效果,張德江委員長還就《浙江人大》反映此事的通訊報道《喚醒沉睡的權力》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國人大財經委、預算工委組成聯合調研組了解該縣采取特定問題調查這一監督形式的情況。這一事件被《檢察日報》評為《2015:十大民主法治事件》。2015年,云和縣人大常委會又對國有固定資產開展特定問題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