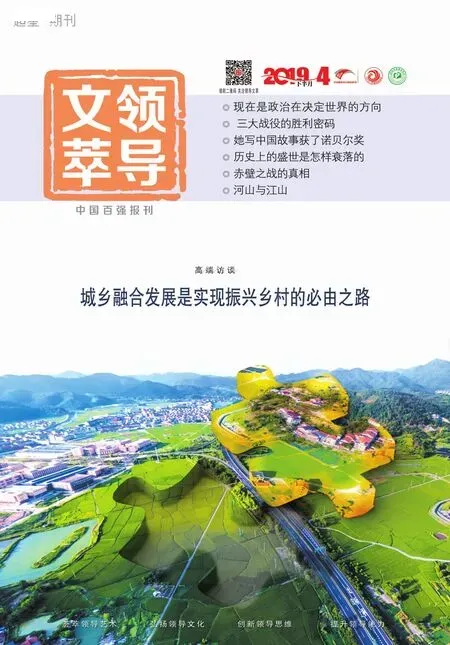羅曼·羅蘭芩的個人存在就是一出英雄劇
韌霧
1866年羅曼·羅蘭出生于法國勃艮第區的克拉姆西小城,家境十分平凡,父親這邊上溯五代都是公證人,母系方面則是農民或鐵匠。家人認為世道維艱,對他的最大期望便是努力得到一份穩定工作,一生衣食無憂。他只好服膺于家人的期望,按部就班地努力。在未經發表的私人檔案中,有人發現過一張小紙條,小羅蘭寫著:“我向媽媽保證,盡我一切力量,準備投考高等工藝學校”——從這里畢業后可以擔任高級工程師。
羅蘭的敏感天性中有壓抑不住的對藝術的熱愛。羅蘭在發現托爾斯泰的作品后,將其奉為偶像,“一個活著的莎士比亞”。晚年的托爾斯泰世界觀發生激變,放下創作,潛心投入到為世人謀福利的事業中。1886年,托爾斯泰的小冊子《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出版,讓歐洲為之震驚,他把羅蘭“最崇敬的藝術無情地革除了教門”,也讓其困惑不已。為此,1887年,羅蘭冒昧地給尊為心靈導師的托爾斯泰去信求教。
沒想到幾周后,他得到了托翁長達8頁的親筆回信。托爾斯泰闡述其藝術見解:只有使人們團結的藝術才有價值,只有為自己的信仰能夠做出犧牲的藝術家才能得到承認;不是熱愛藝術,而是熱愛人類,才是一切真正志趣的前提……羅蘭獲得了極大的心靈震動。茨威格后來評價:“這是羅曼·羅蘭全部創作的起源,道德威望的基礎。”
為英雄樹碑立傳
羅曼·羅蘭最初一直在寫劇本,他晚年在回憶錄里自述:“戲劇過去是,如今仍然是我最喜歡的藝術形式。”據統計,他一生共寫了21個劇本,公開發表過的有15個,流傳下來有書可查的有12個,而真正在舞臺上演出過的,尚不到一半。
但在羅蘭生活的時代,法國盛行絕對真實的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文學。茨威格形容其時占據舞臺的是“通奸故事,瑣碎的色情沖突,從來沒有觸及全人類的道德倫理問題”,自然主義將生活引向“狹隘、平庸和瑣碎,可羅蘭想要凌駕于搖擺不定的現實之上,想要那永恒理想的偉力”。他似乎注定孤獨,也倍感失意。羅蘭曾在寫給易卜生的信中說:“我對周圍一切感到太格格不入,所以我寫作僅僅是為了我自己,我寫了五六個劇本,寫完一個又一個。可是,我有時不由自主地由于這種孤獨而心煩意亂。”
他將眼光投向了自己崇敬的對象,發現“越是深入研究偉大作家們的生活,就越對他們畢生遭受如此眾多的不幸感到震驚”。羅蘭轉而歌頌那些不甘于平庸的天才,在痛苦與患難中奮斗的靈魂,《貝多芬傳》《米開朗基羅傳》《托爾斯泰傳》應運而生,涵蓋音樂、美術、文學三大領域的巨人。羅蘭形容自己寫《貝多芬傳》,是唱出了“病愈者的感謝曲”。盡管文學界對其無動于衷,但這本小冊子聲名不脛而走,銷量絕佳,成為羅蘭的成名作。
羅蘭的英雄主義集大成之作,是他的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獻給各國的受苦、奮斗、而必戰勝的自由靈魂”。這本書從1890年開始構思,1912年寫完,前后經歷20余年。羅蘭先用十余年構思,積累筆記;然后又經十載逐步寫出全稿,平均每年一卷,集中寫稿的時間只有每年暑假的3個多月。
“超乎混戰之上”
1914年7月31日,僑居瑞士的羅蘭在一個小鎮的火車站上,猝不及防看到一戰爆發的公告。他憂心如焚,回旅館后寫下了“戰時日記”的第一頁:“這是一年中最晴朗的一天……在這樣溫柔的良辰美景中,歐洲各國人民開始互相殘殺。”
羅蘭一貫持有反戰思想,他曾說法德之間的戰爭,讓他整個青年時代都在戰事與死亡的威脅之下度過,而現在適齡的青年們又要被送上戰場充當炮灰。他慨嘆,自從1910年托爾斯泰逝世,“歐洲再沒有一個偉大的道德權威!”而他要扛起這桿旗幟。
9月15日,羅蘭在《日內瓦報》上發表了《超乎混戰之上》一文,這也是他人生第一篇政論。他呼吁盡快結束戰爭,宣稱各民族、各國文化都有其固有的優點,應當互相尊重;還建議成立“最高道德法庭”來制止這場戰爭。
社會性的狂熱席卷歐洲,羅曼·羅蘭無疑是逆流而上,引起一片嘩然。在法國,社會輿論譴責他是賣國賊。“在當時的愛國主義者看來,羅蘭的第一個罪行是他公開思考戰爭的道德問題。‘對祖國是不能爭論的。”一些友人公開表示與他斷絕關系。德國人也并不領情,《德意志評論》指責他的和平理念,是“在陰險的中立主義假面具下,包藏著法國對德國精神的最危險的攻擊”。當時歐洲一批著名的作家、藝術家都在狂熱地支持本國政府,德國作家托馬斯·曼、霍普特曼;也有如里爾克、霍夫曼斯塔爾這樣內心反戰,但迫于壓力,不敢公開表態。
1915年,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授予羅曼·羅蘭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法國的沙文主義者又群起攻之,甚至給瑞典政府施加壓力。所以拖到1916年,瑞典方面才通知羅蘭去年獲得該獎。羅蘭將獎金全數捐給了救濟難民的多家組織。他還在瑞士的國際紅十字會“戰俘通訊處”,義務工作了9個月,登記信件、寫信,“天天沉浸在悲痛與哀傷的海洋中”。
塵封50年的訪蘇日記
1931年和1934年,羅曼·羅蘭先后發表《向過去告別》和《全景》兩篇總結性的長文,概括自己在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和以蘇聯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之間,探索社會發展出路的思考。1917年列寧曾邀請羅蘭去俄國,他拒絕了,說自己不愿陷入政黨間的混戰。但十幾年后,在著名的《向過去告別》一文中,羅蘭宣布從此同曾經的“精神獨立”思想決裂,認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證明是“真正精神獨立的唯一保障,是個性充分發展的唯一可能”。
羅曼·羅蘭被看作是“蘇聯的老朋友和維護者”。1935年,他每天接到大量信件,要他對當時蘇聯國內因基洛夫被殺而大規模鎮壓“兇手”“反對派”的局勢做出解釋。當年6月23日,69歲的羅蘭應高爾基之邀來蘇聯訪問。兩人的通信持續了20年,但一直未曾謀面。蘇聯給予了羅蘭的27天來訪最高禮遇的接待。
但人們很奇怪,羅蘭回國后卻未對訪蘇期間的觀感發表任何言論,當年曾引起過種種揣測。直到多年后,他的訪蘇日記被發現,作家詳細記下了見聞,但最后卻寫下:“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滿之前,不能發表這個筆記——無論是全文,還是片段。”
1989年這本約15萬字的日記正式出版。羅蘭在日記里肯定了蘇聯建設新社會的成就,也記錄了許多他目睹的弊病。紅場體育節日大檢閱,羅蘭看到斯大林就像“羅馬皇帝”一樣,站在檢閱臺上欣賞著群眾對自己的崇拜。他對此很反感,“對真誠的共產黨人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手段,它可能在社會上挑起向一個人頂禮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
訪問期間,兩位好友也沒有機會好好深談,到高爾基家里來訪的客人太多了,有時一天竟多達八九十人。羅蘭被招待觀看蘇聯電影和戲劇,看到的要么是“拙劣的政治宣傳品”,要么是對美國歌舞劇的“拙劣模仿”,“自從文藝形式的多樣化被強權取締后,大眾的藝術趣味竟然腐敗墮落成這個樣子”。
羅曼·羅蘭為什么要把日記封存?有人認為他的保留直接原因是出于對家人的保護,妻子瑪麗亞的親友都在蘇聯,而大清洗運動已席卷全國。也有人為其辯解,作家并沒有將日記美化后再出版,他可能從維護世界反法西斯的大局出發,且仍對蘇聯抱有期望,于是緘口不言。但無論如何,這都是羅蘭身上一道曖昧不清的陰影。1937年,羅蘭曾致信斯大林為判決布哈林求情,但沒有回音,布哈林也于1938年被槍決。有學者注意到,從1937年以后,羅蘭的書信與文章里就永遠不再出現斯大林的名字了。
1944年8月巴黎解放。當年11月,78歲的羅蘭抱病到巴黎參加十月革命的紀念活動,他在一個多月后病逝。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