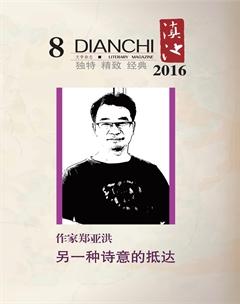散文:另一種詩意的抵達( 創作談)
鄭亞洪
寫散文要有兩個準備:語言和敘事。好的散文是兩方面的結合,詩的語言,小說的敘事方式。散文 essay英文解釋為 shortpieceofwriting,“寫作片斷”,essay在詞典里有三種文體“論說文、隨筆、小品文”,我采取“隨筆”來對應散文,“片段式寫作”比較符合我的散文寫作傾向。憂郁是事物的特定狀態(鮑德里亞語)。凡事物,它有一股憂郁之氣,這是事物吸引人、迷人的地方。我寫事物,一定是它的憂郁之氣吸引了我,我朝這個方向努力。散文不要寫得“美”,不要太“抒情”,寫散文要克制、冷靜,與被寫的人事物拉開距離,保持點憂郁的氣質。第一本音樂隨筆集《天鵝斯萬的午后》寫得較為抒情,寬闊,也很美文;第二本《音樂為什么》轉向內斂、克制,講究布局;第三本《音樂會見》朝現場的音樂會打開耳廓,朝內心旋開藝術之筆。今年下半年即將出版第四本《看不見的城市,看得見的風景》,是一本攝影隨筆集,也是我最看重的散文集。
寫音樂隨筆是我寫作的一個準備,一個訓練場。《音樂會見》最初是些零碎的聽音筆記,音樂與生活流相結合,文字感性,我取了個名字叫《音樂書》。2006年我去上海聽了一場音樂會,從此我的寫作方式發生了變化。聽現場與聽磁帶、CD完全不同,到了音樂廳里你見到了樂手、樂器、指揮家,與你坐在家里聽音響是兩碼事。最初的《天鵝斯萬的午后》基本上與我生活的城市無關,從《音樂為什么》開始我有意無意在隨筆里滲入自我,經常會在評論里蕩開一筆。《音樂會見》我不這么寫了,按照音樂的主題去寫。聽古典音樂是一種解放內心的方式,交響樂比較符合我內心關閉的那個空間,我不知道這個空間隱藏著什么,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可以承載,直到某首交響樂在一支樂隊、一個指揮家的手里開啟了我內心幽閉的大門。《音樂會見馬勒》是在音樂廳里聽馬勒的心路歷程,從一場唱片里你捕捉到馬勒的很多信息,但是當你讀完馬勒傳記,再正兒八經坐進音樂廳里聽一場馬勒交響曲,那又是一種醍醐灌頂、酣暢淋漓的感受。馬勒是一位內心掙扎的作曲家,九部交響曲就是他的傳記,樂器經常表現出猙獰、恐懼,第三樂章柔板又反映出他無比柔情的一面。從 2008年第一場馬勒到 2015年第六場馬勒,七年時間聽完五部馬勒交響曲,我也用了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完成了《音樂會見》,寫作《音樂會見》的過程是期待的、緊張的、快樂的、內省的。聽音樂會讓我找到了一條通往詩意的路徑:“為了抵達詩歌,應當穿越另一種藝術:音樂。”(雅克·朗西埃《沉默的語言》)十五年前在《天鵝斯萬的午后》里引用過叔本華的話,音樂“跳過了理念”,它“無視現象世界”。音樂為什么要跳過理念?音樂又如何無視現象世界?多年來我在書本里一次次地撞見這句話,在音樂廳聽完交響曲品味這句話的含義,它說對了,“跳過”、“無視”之后,是——沉默!緊接著,是寫作,讓聆聽變得沉默,從此,沉默走向了另一個境界:語言之美。
寫作是一場與周圍永不妥協、和解的運動。當你提起筆,寫下第一個詞,意味著你與世界隔離,你將融入另一個由文字造成的世界,一個明亮的空間逐漸暗淡,另一個隱喻、矛盾的空間升騰起來,在那里活動著你的人,你的事,你的物,它們隨著寫作的深入自動到來,之前你孤獨、自我、沉默,寫作之后,你將更加孤獨、自我、沉默,而這時的你脫胎換骨,寫作幫你走出一個熟悉的世界,在文字虛構的王國里書寫自我。從詩性的詞語里挑選符合當下的詞。我在寫散文隨筆的時候對詞語的挑選僅似于苛刻,有人說詩歌讓合適的詞找到合適的地方安放,散文寫作也一樣,有些看似漫不經心的寫作其實蘊含著我的內心世界,對應著它。詞語的差異造成了事物的差異,而不是倒過來的,詞語本身構成了一種更真實、更理想也更完美的現實,普通的一個現象,訓練有素的寫作者看來是書寫意圖的一種,逆藝術境界,越過詞語的平庸一面,抵達對岸的港灣。我寫我看見的,但絕不是簡單的看,因為你的看經過了你大腦思考,尤其經過你內心的流動,表面波瀾不驚的文字卻有一股內在的張力,需要往里面深讀下去。我是一個攝影愛好者,相機是我看世界的另一只眼,當我拿起相機走過某個場景的時候,會更用心觀察。我喜歡看細小事物,觀察它們的變化,我會對著同一個建筑物拍上好幾次,連我自己都奇怪,為什么如此迷戀于陽光與陰影?阿甘本說,“影像就是寧芙,影像是封存了過去碎片的寧芙。”多么好的一個詞:寧芙,Ninfe,漸弱,乃至幽怨。拍照就是去喚醒記憶的小寧芙,與它交媾(相機、筆,性武器象征),開啟通向記憶、通往過去的可能性。相機幫助我喚醒了過去,寫作讓美麗的寧芙永生。
2013年我有一本流產的散文集《光影手記》,后來它催生出兩本書,《看不見的城市,看得見的風景》、《小村風物史》,《看》寫城市,《小》寫農村。我出生在農村,在城里讀書生活工作,那么我的寫作將回到生活的源頭:農村。有一天我離開了迷戀許久的縣城,朝散落在煙靄里的小村莊走去,我選擇它們,小村莊也選擇了我。從樂清東鄉到西鄉,從東海岸到雁蕩山山麓,它們往往是小的,不起眼的,甚至被人遺忘了,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有存在著讓人難以割舍的情感,有引起人共鳴的風物,一座老屋、一個祠堂,一次禮儀,一條河流,讓離開故鄉的游子讀著文字思慕它,懷念它。村莊就像養育我們的父母,它們在衰敗,在老去,我們在疼痛。《小村風物史》將是一次精神的返鄉之旅,同時也是一次對那些依然守著故鄉、艱難生活人群最溫柔的禮贊。
2002年我寫出中篇小說《馬德萊娜,或虛構一種》,它在多個編輯手里輾轉,終于發表在 2006年第二期《滇池》上,從此,我開始了與一本西南邊陲雜志長達十年的愛與戀。2008年散文《物與象》刊出,我準備從音樂隨筆撤出,選擇純散文寫作。散文被人貼了很多標簽,諸如“新散文”、“原散文”、“大散文”、“美文”、“非虛構”,兜了一個圈圈后,何時回到自己?大學時期,我翻譯了博爾赫斯一篇很像詩歌的短散文《德利亞·艾萊納·圣·馬科》,從那時起,冥冥之中仿佛有一條散文的路子在我前面鋪開,雖然后來我嘗試了小說、詩歌、評論,但最終我找到了散文:最精準的自我表達方式。2011年散文《2006·時間模仿者》發表在第六期《滇池》,從新年第一天一直寫到年末除夕,那時,小說家托馬斯·伯恩哈德是我的寫作老師,伯恩哈德也教會了我朝下看,寫事物的內里和褶皺昏暗處,卡夫卡發出的邀請再次在一位奧地利作家身上得到回響:以幽默和反諷使不堪忍受的世界可以忍受和溫暖。我在散文試驗田里摻雜了虛構、非虛構、原文、詩歌;我寫短句,不寫長句;寫清晰,不含糊;用描摹,不評論;寫表面,以抵達內陸深處的幽暗。2014年八千多字的長散文《走了那么遠去看一個湖》在第六期《滇池》上刊出,這是一次寫作的信心之旅,用詩的結構為散文謀篇布局(布羅茨基),好的散文應該具有“一首詩的原創性、隱喻結構的深度、歷史和文學語境的豐富性”,布羅茨基接著說,“更為重要的是,他試圖揭示寫作此詩的那門語言所蘊藏的創作潛力”,我在文章結尾寫道:“青海湖,一個藍色的詞,從此進入了漆黑。”仿佛,又一次我被俘獲,成為了一名詩人。《臺灣隨筆》發表在今年第一期上,里面有一段寫我在臺北觀看瓦格納歌劇《女武神》的經歷,至此,我用十年時間在《滇池》走完了散文歷程。
本欄責任編輯 張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