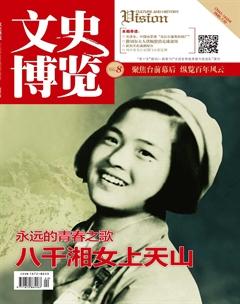清代科考,舞弊其實很難
段立新
清人錢泳《履園叢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學政胡希呂拘泥于朱熹“微,無也”的解釋,視“微須”為沒有胡須。這可苦了一班稍微有些胡須的考生了:按學政大人的理解,自己應該是沒有胡須的人。如此這般,不被學政大人當成替考者驅之考場門外才怪呢!書中記載說,一個名叫沈廷輝的江蘇常熟生員就因此吃了啞巴虧。后來,一個維權意識強的考生據理力爭:《論語》上說“孔子微服而過宋”,照你說,“微”就是“無”,敢情孔老夫子是裸體到宋國巡回表演啦?那么,胡須為何這么重要呢?
清代由一省學政主持的考試叫院試,它是博取秀才功名的最后一場考試。上面這個故事涉及了院試核對考生面貌冊環節。面貌冊相當于今天的準考證,上面詳細記載了考生身高、有無胡須、胎記等體貌特征信息。考生入場時,學正要逐一檢查考生本人是否與面貌冊描述的一致,目的是防止替考舞弊現象。
在此之前,考生要依次參加縣試、府試兩場考試。出于杜絕舞弊的考量,考生要按規定填寫姓名、籍貫、年齡等身份信息,還要交3份文字材料,一份是考生曾祖父至父親三代人的履歷資料,一份是5個參考考生互相擔保的承諾書,一份是考生所在地廩生出具作保的擔保文書。假如你是其中一個考生,你千萬不要向知縣(或知府)大人提“簡化手續、提高辦事效率”的要求,因為只有理直氣壯地上交這些材料之后,你才能被認定沒有假冒籍貫,不是請來的槍手,不是正在服喪守孝的人,不是娼優皂隸(妓女及從事歌舞職業的藝人、衙門差役)家庭子弟。一句話,你是符合參考資格的、真實不假的考生本人。
接下來的5場考試是在縣衙(或府衙)大堂上完成的,知縣(或知府)大人親自監考改卷,評定名次。大概是要貫徹“監考從嚴”原則,縣衙(或府衙)禮房要按規定嚴格執行“彌封”程序:封住試卷上的考生姓名,只留下座位號。還有一個環節很有意思:從第二場考試開始,上一場考試位居前10名的進入下一場考試時要“挑堂”——請進單間,在監考人員的注視中完成考試,這情景就是“特別的監考給特別的考生”。
與縣試、府試相比,院試的警戒級別最高。先看點名環節。考生自己請一個擔保人,縣教諭再給考生委派一個擔保人,點名時,這兩個擔保人站在學政兩旁,在點名聲中,考生一邊跑步上前,一邊連聲喊“某某為我作保……”擔保人一看,沒錯,他就是我擔保的人,于是也連聲喊:“在下為他作保,在下為他作保……”如果站在眼前的是槍手,擔保人便默不作聲。這一下有好戲看了:槍手要帶枷示眾3個月,考生要取消考試資格,然后,兩人一道去充軍。有趣的是,點名的時候,有時還可能會發現“冒籍”的。據說,這假冒戶籍的人以南方考生居多,“天子腳下好做官”,南方考生多半要假冒順天府(今北京市)戶籍。為此,順天府往往要臨時加派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來當“審音御史”,聽口音辨別考生是不是北京人。
考生入場前還要經受防夾帶檢查。奉命行事的差役很敬業,他們連搜帶摸,把考生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搜摸一遍,連文具、鞋襪也不放過。特別敬業的還要把考生請進室內,解開頭發,脫光衣服細細檢查一番。主考的學政大人也很敬業,他要對核對面貌冊環節親自把關,這便有了胡希呂“微,無也”一類的趣事。
院試特別注意試卷保密。特制的試卷卷面貼有考生姓名浮簽,考生的姓名寫在背面右上角規定的位置。交卷之后,考生自己揭掉姓名浮簽,考生姓名則要密封起來,上面蓋上大印。
都說人有三急,可院試似乎偏偏就漠視三急的存在,你舉手請示外出拉屎撒尿是吧?好,給你試卷上蓋一顆黑色圖章印,然后,請吧!“請吧”之后,任憑你文章寫得賽韓愈超蘇軾,你也注定只能是陪考生:這圖章俗稱“屎戳子”,屎戳子一蓋,試卷作廢。大概是出于人道關懷吧,考生座位下面備有一口黑瓦罐,這是考生們公用的尿壺。至于大便,對不起,不在黑瓦罐服務范圍之內,你自己看著辦吧:通常的辦法是讓自己的襪子臨時客串大便器。張治中將軍參加過院試,他回憶說:“考場里最難受的是大家不能出去解手,每人桌子下有一個瓦罐子裝屎尿,臭得熏人,悶氣得厲害,真難過。”
的確,在這樣的考場考試真難過。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準秀才們,想舞弊嗎?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