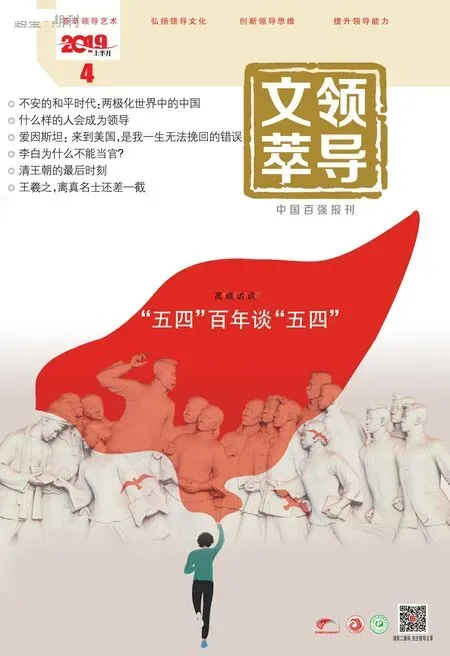居士不適于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
李一氓1903年出生于四川彭縣,1921年去上海求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后,在向廣東撤退途中,他和周恩來一起介紹郭沫若參加中共。后來他又被派回上海,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地下保衛工作,公開身份主要是文化工作者。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他受黨的委派,協助葉挺、項英組建新四軍,還特別奉命協調葉、項的關系,被指派充當兩人間的“緩沖者”。
我離開延安的時候,李富春要我作為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沖人。當時,我也沒有對這個問題做出過什么設想,也沒有向李富春提出過什么要求,就這樣很輕率地答應下來。到了軍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變,你說他們之間一定有什么尖銳的矛盾和沖突,也很難說出來。在日常情況下,項英還是很識大體的。軍部的正式會議都由葉挺主持,前方部隊的報告、請示,項英都請葉挺首先批注意見。1940年秋季反日寇對涇縣的掃蕩,作戰計劃是葉挺定的。凡是葉挺介紹到軍部工作的非黨干部,不管人數多少,項英都表示歡迎和信任。至于說一些小事如葉挺單獨有廚房,項英從未表示異議,甚至項英還在葉挺的生活細節上,做了適當的處理,維護了葉挺的威信。
有人說是葉挺作為部隊首長,不習慣政治委員制度,因此,葉項矛盾好像應該由葉挺多負些責任。這個理由不是事實,因為大革命時期,葉挺帶領的部隊都有黨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員。南昌起義的時候,聶榮臻就是他的黨代表,他們合作得很好。但是新四軍的這兩位——部隊首長和政治委員,卻在平常情況之外,另有兩個特殊情況:(一)大革命時期葉挺和他的團、師、軍的黨代表,兩個都是共產黨員,他們之間的問題,可以在黨的會議上得到解決。而在新四軍,部隊首長葉挺卻是脫黨十年之久的非黨員,葉項之間只有行政關系,只有抗日統一戰線的關系,沒有黨的關系。這就使得兩方面之間很難于自處一方面和對待另一方面。(二)更重要的是,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的關系與葉挺當團長、師長、軍長時不一樣了。那時,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關系屬于葉挺方面,而派去的黨代表跟部隊沒有歷史關系。而新四軍的情形卻恰恰相反,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關系屬于以副軍長名義出現的項英方面,而與派來的葉挺毫無關系。
但兩方都不能明白地擺出來,葉挺擺不出來,項英更不能擺出來。因此葉項之間的關系,這個矛盾卻是來無影去無蹤,雙方都沒有直接向我表示過。我當時也沒有完全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而且我無權把他們拉到一起進行仲裁。
影影綽綽的,葉挺總想借口離開軍部,采取躲避的辦法回重慶、回澳門。影影綽綽的,項英總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并且幫助他離開新四軍。1938年初,葉挺離開過軍部,從武漢去香港回澳門,攜同夫人回到軍部。同年秋,葉挺送夫人回澳門時,在廣東與余漢謀商量在東江成立游擊隊。12月到寶安縣深圳墟任廣東東江游擊指揮。他在走之前,曾和項英商量過。項大為贊成,送了幾百枝步槍到廣東,還答應調一些廣東籍的軍政干部到他的部隊中去。可是,沒多久就被蔣介石發現,取消了葉挺的任命。1939年春,葉挺由周恩來陪同,從重慶回到皖南。周恩來在皖南期間,曾和項英單獨談過兩次話,估計是談葉項之間的關系問題。周恩來走后,葉項之間保持著一種和諧狀態,這也許是雙方克制的表現。一個來月后,葉挺軍長去皖北,主持成立江北指揮部,到8月份才回到皖南。他回來后,立即向周恩來提出要去重慶,向蔣介石要求增加經費和編制,接著就離開軍部。這一次離開時間最長,到1940年的8月17日才回到皖南軍部。
皖南事變前,大約1940年秋末,我聽到葉、項二人議論過,要把皖南部隊分作兩部分,用意是軍部名義上仍留在皖南,實際上大部暗渡江北。可是,由誰率領軍部過江呢?兩人互相謙讓,都認為留下的是更危險的任務。結果誰也未走成。如果當時不管是誰先走后走,實施這個方案都是有利的。可惜他們過于謙讓了。
葉挺曾經下過一次決心離開軍部,以后不再回來。他親筆寫給我一封信,說是“居士不適于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意思是講,不是共產黨員的人,不適于充當共產黨軍隊的軍長。看來,這種苦惱也不像是完全針對某一個人的。這封信我給項英看過,項英沒有太大的反應。我得信后,葉挺已經離開了軍部,我作為緩沖人,明顯的是失敗了。葉項之間關系固然很緊張,其實這種情況在哪里都有,如后來的蘇北軍部,陳毅和饒漱石之間,關系不是也很緊張嗎?
(摘自《李一氓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