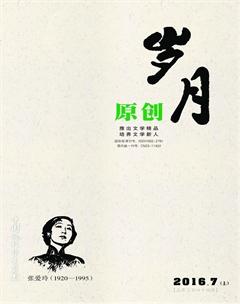深痕
楚些
提到三皇之首的伏羲氏,可能許多人會為之頷首或點頭示意。這位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其足跡之大達也許難以考證,但影響卻無疑是深遠的,《易經》中“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記載,其實就是表彰三皇五帝這些先圣們教化之功。春秋時代孔子出,創立儒家學說,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對歷史與現實的秩序規劃,換一個通俗的說法,就是為歷史和現實人物排座次,賢和圣乃為其中的佼佼者。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是,賢者多為當世或接近于當世者,而圣者則多為遠古之人。人們常說儒家的基本理念是恢復周禮,所以復古尊古的傾向特別明顯,說起來,儒家何止是尊文武召公,他們把所尊之人一直推到人文始祖那里,問題扯遠一點,在諸子之中,由此可見儒家是善于出牌之人。
但若是說及太昊陵,或許有一些人就開始搖頭了。這里面有兩種情況,一是確實不知太昊乃何許人也;二是雖知道太昊與伏羲實為一人,但卻不知太昊陵的具體位置。前幾年,河南省打出了“文化中原,老家河南”的宣傳口號,敢于使用“老家河南”的標語,概是因為河南的有底氣,而太昊陵就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淮陽縣鏡內。今天的淮陽乃至周口已是偏僻之壤,若非有涉及民生之危情的發生,已很難進入國人的眼界,如果放寬歷史的視線,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包公陳州放糧所在地就位于淮陽治所下,淮陽古稱陳州,距離當時的首善之區開封甚近,也屬于當時的京畿重鎮了。
十一期間,三家九人,一干朋友從開封啟程,沿大廣高速直奔淮陽。未及兩個鐘頭,就已抵達太昊陵門前。天氣尚暖,垂柳照舊依依,而門前的龍湖則微波蕩漾,一些游船在水中緩緩游弋,如野鴨般在湖面上懶懶地曬著日光,只是支起的羽毛多為白色,所以甚是鮮亮。
從正門進去,沿兩邊一字排開的古柏所拱起的大道直奔陵墓所在地。陵墓占地甚廣,呈圓形,繚繞不熄的香火,干枯的柏樹虬枝,以及陵墓上方蔥郁的樹木組合在一起,是此處給我留下的直觀印象。
出來的時候未走大道,而是去了靠右手的植物造型園,據說其中的多種植物造型,乃是做過段祺瑞的花工及其后人的手筆。這位花工想來已經去世,段執政時代距離今日已近百年,而其后人子承父業,將手藝與技術由私密之地,移到公眾視線之下,也是時事進步使然。夫子曾說過:“禮失求諸野”。不獨禮儀如此,專制王朝結束后,專為皇權服務的各種秘方和技術,自然散落開來,由封閉之地,走向開放之野,若不然,那些打著宮廷御制招牌的飲食或藥方,如何才能讓大眾折服!這些都是題外話,此處的植物造型還是非常有特色的,主題除了各種動物的形態外,還有塔樓、牌坊、大門等,而主構的材料卻多是由冬青或小松柏樹組成。
此時游人不多,而真正游賞者除了我們三個大老爺們,其他人等皆在擺著姿勢,等待鏡頭的收錄。于是,我們的步點自然踩在他們前面,往門口走的時候,另一個獨特的景觀扯下了我們的步伐。原來是四棵高大的梧桐樹在頂冠處密密匝匝,枝干相互伸入對方的臂膀,結果落成了一地毫無縫隙的蔭涼。此時剛過正午,仲秋的陽光曠朗密集,但在這由梧桐樹圍成的空地上,好像找不到一絲一線的陽光。更神奇的還在于,其中靠北的兩棵梧桐,高處的兩根樹枝竟然互相融合,最終成了一體,成了文化史上早已唯美化的“在地愿做連理枝”。而掛在樹枝上的布告牌,則明確標示了兩棵樹“連理”的具體時間,另有愛情樹,許愿樹,青年人流連往返等等提示。看到這些,心中不覺莞爾,贊嘆之后,我們三個仰起頭,將目光聚焦于連理枝上,開始爭論其是否是自然形成或后天嫁接。連理枝雖然是眼前之事,但理性告訴我們,這其中后天嫁接的可能性極大,不過遍尋證據無果,兩根樹枝嚴絲合縫,如這一地的蔭涼,到底是哪一只神奇的手完成了這一異事,也許只有資深公園管理人員所知了!
賞讀完連理枝這一奇觀,我的目光為南邊兩顆梧桐的樹干所吸引。激起我注意的當然不是樹干之粗壯,而是粗大樹干上密密麻麻的深痕。這些深痕的主體內容大多由名字構成,諸如張山李麗到此一游,或者王剛劉霞特此紀念之類,我細致觀察一下,諸多人名皆由兩字構成,據此可以推斷,這些主人公應該是80前后之人,之所以有如此判斷,乃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內地的人名有著不一般的時代色彩。當然,我還可以就此推斷,這些人名的后面,他們的父親母親的文化程度,屬于文化人的群體應該很少,若不然,也不會給自己的孩子起了如此爛俗的名字。他們顯然是沖著連理枝而來的,但文化史上相關情愛傳奇的男女主人公,哪一個人的名字不是韻味獨具,如祝英臺和梁山伯,焦仲卿和劉蘭芝,董永和七仙女等。一句話概括,如此人名,刻在樹上,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名字如何能深入樹干之中,想來是鋼、鐵類利器才可完成,估計最常見的就是隨身攜帶的刀具了。仔細端詳下,這些字體無一瀟灑流利,但都力道甚大,于是令我恍然,心里在還原著當時的場景:一對二十出頭的年輕男女,攜手于樹下,為表忠誠與愛意,總是喜歡沖動和表現的男孩,試著用石頭在樹干上鐫刻,不成,便掏出小刀或尖利的鑰匙,切入大樹的皮膚,然后深至紋理,歪歪斜斜地留下幾行字,轉身,對著女孩一番熱烈的陳詞,再之后,兩人攜手出了門,男孩的血管內依然翻江倒海,等等。
而時光漫漶,侵蝕了太多的人事,我的恍然能抵達最初的事實么?我沒有任何的把握。至于那些刻下名字的人們,現在在哪里?他們生活的怎樣?還會記住自己曾經留下如此“壯舉”么?過了二十年,男孩還能重溫一位女孩柔細的手掌溫度么?這些問題讓當時的我很糾結,只能選擇放棄這些內心的提問。轉而細細查看那些深痕。或許是有了一些年頭,一些深痕已經變得深黑,端口處樹干的皮膚或干裂或卷起,只見一個個細小的深洞懸掛在青白的樹干上,從而成為醒目的駐扎。而另外一些新的痕跡,深淺不一,如城市電線桿上的小廣告,見縫插針,將不長的一段軀干緊緊包裹。
再回到靠北的兩棵樹下,剛才因為忙著抬頭,沒注意軀干的情況。目光逡巡之后,這兩棵情況亦然,只是醒目程度稍微欠缺。
執情強物,原是古典詩詞的常用手法,畢竟只是落實在詩人們的假象或紙簽之上,然而在這里,從各個角落里涌來之人,竟然將此手法嵌入實在的物體之中,并且,越過冷冷的時光,與后來者不斷遭遇。依照我的分析,如此結果,來自兩個切實的因由,其一是“浪漫”現場對來者所形成的嚴重刺激,難得一見的愛情現場中,控制自我的沖動必然是很難的;其二,有了始作俑者,后來人出于模仿的本能,自然絡繹不絕。而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對于留下深痕的男女來說,那一道道刻痕是有特別的氣息的,它們有呼吸,也有味道,總而言之,非呆滯之物,而是有著此時此刻的體溫和生命氣息。不過,他們所沒有想到的是,這幾棵梧桐樹是否也擁有生命?當時的他們似乎覺得沒有,但對于我來說,難道真的沒有么?
愛情本是個一生的事情,可惜的是在我們的年輕時代,總是過度的透支,而這眼前的如此深痕,不過是最微小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