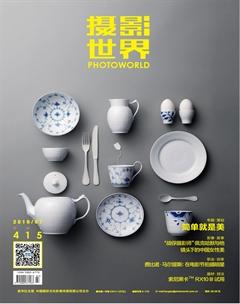厄布魯·斯達爾:白色故事
厄布魯·斯達爾 祝愿



1975年出生的厄布魯·斯達爾(Ebru Sidar)來自土耳其,30歲才拿起相機,以攝影愛好者的身份探索自然的秘密;他用極具裝飾感的精美畫面將自然變為夢境,并在其中呢喃細語。
不論是黑白照片還是彩色照片,斯達爾的作品大都具備深沉的畫風;只有一組例外,便是《白色故事》(White Story)。
雪的秘密
《白色故事》的主角是雪,照片用極簡主義手法勾勒雪景線條,天空和大地層次分明,作為主角的一棵或幾棵樹點綴其間。但不同于其他以雪為主題和內容的風景攝影作品,斯達爾拍雪并不太關注雪的純潔和無瑕,以及白色世界所呈現出的圣潔感。通常,圖片標題都像是樹木的獨白或對話,吐露著自然的情感。
在斯達爾的作品中,白雪覆蓋大地,自然似輕聲宣示萬物有靈。“我們知道,每一片雪花都有不同的形狀,這讓我們從中感知到生命力。雪讓大地發聲,卻又靜靜地邀請人們走進這明朗的世界。”斯達爾說,雪景雖簡潔空曠,但比起春夏的豐富多彩,其中蘊含著更多可供人感知和讀解的信息。而且,被冰雪覆蓋的這片土地上發生的故事,能激發更多聯想。
這種感受或許源自女性獨有的想象力,也源自斯達爾從少女時代起便對雪花抱有的感情。“對我來說,雪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自然現象,當黑白取代色彩,大地和天空便銜接到一起,仿佛時間停止,又讓我雀躍不已。”
這是自然埋藏秘密的時刻,也是“提醒”斯達爾尋找秘密的時刻。因此,《白色故事》的主旨在于探秘,而探秘的過程在于自然與心靈的對話。
“對我來說是探秘,我希望對觀者來說也如此。”斯達爾說,“我不想大家只是覺得雪好看,而是希望雪能夠通過眼睛觸及每個人的心靈;如果仔細看,你會發現每張照片中都隱藏著一個故事,大多與愛和情感有關。至少,對我而言這些場景不只是場景,我也盡力把自己的感受呈現出來。”
用心靈觀看
斯達爾是個情感細膩的女人,注重攝影創作中的情感表達;一處風景之所以會進入她的取景框,并不因為它美麗奇特,而是因為斯達爾自己站在此處與風景有了心靈感應。
這聽上去很玄妙,但是藝術創作本來就難以言說。
剛開始攝影時,斯達爾一般只拍普通的近距離肖像照片,后來將模特置于自然環境中,再后來才決定將鏡頭對準自然。不過,她拍攝自然風景時,并不是用眼睛去觀察山川河流的壯美,也不刻意留心哪里的風景與眾不同,僅是走進并放眼四周,然后慢慢地等待內心的回響。這種回響不是刻意的,也不追求確切的結果或效果。而且,斯達爾并沒有在之前設計好這一切。
極簡主義是1960年代以后開始流行的一種藝術風格,在繪畫、攝影,以及工業設計等領域都有影響。極簡主義作品的形式感和裝飾感很強,這卻并非是它被當作一個藝術名詞被接受的全部原因。相比其他現代藝術風格,極簡主義風格作品更容易理解,或者說更容易引起觀者的共鳴,乃至慢慢被很多人接受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攝影領域,極簡主義作品中流露出的攝影師主觀情緒往往不會特別強烈,畫面中大面積的留白處理也給觀看者提供了更多參與到作品中的可能。
斯達爾在拍攝時,不像社會紀實攝影家們有明確的拍攝意圖,不像商業攝影師們有清晰的拍攝步驟,也沒有捕捉“決定性瞬間”的畫面。照片中只有白色的大地,略微深調的天空,以及不時出現的形狀各異的樹木和道路……對于她所拍攝的作品,不僅意義將任由評說,其喚起的觀者感受也將任由人們天馬行空。
不放棄業余精神
斯達爾這樣形容自己:“我是一個性格開朗,充滿好奇和幻想的人,在開始攝影后,我并不想放棄業余精神。”
何為“業余精神”?或許我們能從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裔學者崔琦教授的話中有所感受。一名記者曾問他:“你每天在實驗室里,工作一定很辛苦吧?”崔琦回答說:“哪里!我每天都帶著好奇的心情進入實驗室,不知道實驗的結果會給自己帶來什么意外驚喜。每天的實驗就像過節一樣快樂!”
拍攝《白色故事》的斯達爾也擁有同樣的心態。她在土耳其安卡拉念完大學,專業是地質工程,因為朋友偶然間提起的一個攝影網站,她才開始接觸攝影;丈夫送給她一臺小型佳能數碼相機后,她才開始拍照。
從2013年開始,斯達爾開始舉辦展覽,如今也在網站上出售限量版照片,但她還未曾想過,如何以更“職業”的心態規劃每次拍攝。雖然斯達爾已經拍攝了數十個系列作品,有黑白、彩色、風景、人像,但她說并未從中感受到“工作”的壓力,仍然像當初,每次都是一種游戲狀態,給作品起名字也如做游戲。這或許就是“業余精神”吧。
采訪中,斯達爾提到最多的詞,一是“眼睛”,二是“心靈”,她在找兩者間的契合點,卻并不深究其中的內在邏輯,也不會用藝術語言來描述它們碰撞出的火花。用她的話說,《白色故事》開端于一種感受,也結果于這種感受。
“每次走進自然環境都讓我很興奮,這時我就喜歡一個人靜靜呆著,也十分享受這種孤獨。我和自然中的草木空氣對話,并靠我的想象力‘閱讀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