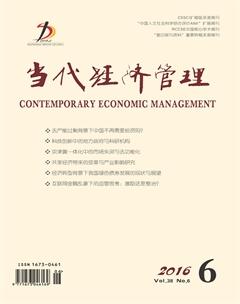基于傳統模式的城市配送新思維
王漢新 王子鳴 潘建堯
摘 要 為緩解日益嚴峻的城市交通壓力,客運發展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開發模式、貨運實施共同配送已成大城市的共識。客運與貨運之間雖有本質的區別,但也存在天然的聯系,從車輛選擇,到節點設置、線路優化,再到運營模式,城市配送完全可以借鑒城市客運的“公交+慢行”發展之路。考慮到貨物不能像行人一樣獨立中轉換乘和步行進入家門,可采用干線運輸的甩掛、郵政的信報投遞等方式,來完成城市共同配送中的接力配送和末端配送。
關鍵詞 TOD;共同配送;車輛;末端配送
[中圖分類號]F570.8;U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06-0029-06
一、引 言
貨運與客運同屬于城市的基本需求,兩者具有相輔相成、協同共生的關系。城市配送與居民出行的最大區別在于,居民出行可以借助交通工具也可不借助(步行),而貨物運輸只能借助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尤其是機動車輛的使用。隨著城市人口、經濟的快速增長,汽車帶來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越來越嚴重,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已成為城市發展的基本理念,軌道交通、BRT、慢行交通漸成重點;然而,城市貨運研究與發展卻相對滯后,城市配送的“路難行、車難停、貨難交”現象很難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城市實施共同配送的目的在于提高裝載率、減少出行里程,這與“公交+慢行”有異曲同工之處,本文將從城市客運交通、郵政信報投遞等傳統模式出發,探討城市共同配送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及運營方式。
二、城市配送之要素
一次完整的物流配送過程是由許多運動過程(運輸)和相對停頓過程(裝卸搬運、分揀)組成的,即城市配送是由多次的“運動—停頓—運動—停頓”過程所組成的。與之呼應的便是城市配送的基礎設施,它是由承擔運動使命的線路和承擔停頓使命的節點組成。而物流系統的主體便是物(貨物),傳統的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便是指物的分銷,而承載貨物的是車輛,車輛不僅需要行駛于城市街道上,也需要貨物的裝卸場所(節點),還需要相應的信息溝通平臺與組織運營策略。
(一)貨物
貨物是客戶需求的對象,是配送服務的實體。貨物需求的主體則是享受物流配送服務和利益、并為此支付相應報酬的單位或個人,包括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等。據中國物流信息中心資料顯示[1],批發零售業的物流費用占其銷售額7.8%;伴隨著近年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論是商品需求還是貨物周轉量都顯現出快速的增長趨勢,尤其是速遞業務更是連續4年的增長率超過了50%,至2014年達到了1 395 925.3萬件[2]。
(二)貨運車輛
車輛主要分為客車與貨車,貨運車輛是城市配送的主要載體,包括中型、小型、微型貨車,以及面包車、三輪車等。根據IEA報告顯示[3],2013年交通部門CO2排放量為75.436億噸,占全球CO2排放總量的23. 4%;北京環境監測數據顯示[4],2014年機動車尾氣排放的PM2.5約占全市總排放的31.1%。一般來說,車容量與單位占用道路面積、單位CO2排放量成反比,與交通阻抗率成正比;柴油車輛的顆粒物排放遠遠大于汽油車輛。車輛的能耗、排放與道路平緩、車速直接相關,擁堵時的排放明顯加大。
(三)配送節點
節點乃是網絡中的線路連接之處,其作用在于為人、貨提供集散、換乘之場所。城市配送節點不僅需要承擔城市與外部的貨物流轉,更多地是承擔將外部貨物送達客戶的“中樞神經”作用。依據“樞紐+輻射”理論、以及貨運車輛限制政策,城市配送節點應根據其服務功能、服務范圍的區別,分為不同層次的配送節點。例如,典型的城市三級共同配送網絡體系主要由集散中心、配送中心、末端節點及相應道路網絡組成。
(四)物流通道
物流通道是由城市物流節點和城市貨物運輸線路組成的,即城市內大大小小的街道,配送企業通過物流通道將消費者的實際需求“傳遞”到消費者手中,以實現貨暢其流的目的。道路與車輛的關系類似于血管與血液,血管有動脈、靜脈和毛細之分,城市街道不僅要有主、干、支、巷之分,也應有人流、貨流之區別。過分強調行人(尤其是小汽車的地位),只會讓城市步入擁堵怪圈,同時增加物流配送成本。城市起源于人的聚集與貨的交易,城市道路的建設與交通引導措施始終應以(人、貨)的可達性、方便性為宗旨。
城市功能分區的發展與產業布局,給城市帶來的巨大的交通載運需求。城市街道的平面與空間延伸,更多地是為了緩解城市客運交通壓力,解決城市居民的通勤問題,而貨物量增長的剛性、需求點的自然分布,以及不斷增強的時段限行措施,使得節點配置、車輛及線路組織成為了城市配送的關鍵所在。
三、客運交通與配送車輛
運輸是指人和物的載運及輸送。城市交通,就是指人和物通過交通工具、利用城市街道,完成空間位移的運輸活動。城市交通分為貨運交通與客運交通,即通常所說的居民出行和物流配送。為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許多特大城市不僅開始實施汽車限購、尾號限行等諸多措施,而以石家莊為首的部分城市則通過尾號限行來減輕空氣污染(霧霾天氣交通應急措施)。不管哪種情況,各個城市在諸多限行政策執行時,首當其沖的則是貨運車輛,進而造成城市物流難的問題。發展公共交通、倡導綠色出行現已成為許多城市交通發展的理念,而城市共同配送發展模式也已被眾多發達國家所證實。
居民出行可步行、騎自行車、乘坐公共交通、也可駕車或打的,依據北京市交通發展年報數據可以看出[4],居民出行中首選自行車、小汽車、公共交通的所占比例,從1986年的62.7%、5.0%、28.2%,至2000年變為38.5%、23.2%、26.4%,2010年則變為16.4%、34.0%、39.7%。而后,隨著汽車限號、搖號、軌道交通的發展,公共交通所占比例不斷增大,而小汽車所占比例隨之下降。相比于居民出行來說,城市物流往往更容易在城市交通管理中被忽視,那么我們就拿客運車輛與配送車輛作一下對比(見圖1)。據有關資料調查,采用步行、自行車、公共汽車、軌道交通、小汽車出行的距離平均為0.81km、3.08km、8.42km、13.15km和11.49 km[5]。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居民出行可以采用步行,但貨物的配送則必須借助于車輛,從而在比較時這里略去了步行方式。
(一)貨運三輪
盡管曾經的自行車大軍逐漸消失于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但面對日益擁堵的城市交通、灰蒙蒙的霧霾天氣,慢行交通又漸漸回到城市的倡議政策中。另一方面,自行車在面對擁堵時有其天然的優勢,特別是克服了體力因素的電動自行車又進一步延長了居民的出行距離。貨運(電動)三輪車同樣在城市配送中也有著明顯的優勢,如節能環保、非機動道路行駛、停靠方便、裝載容量較大,現已成為快件“最后1公里”投遞服務的重要運輸工具。
交通安全意識差、三輪車質量與超載問題等則成了城市交通管理中的一個難題,為此國家郵政局組織出臺了《快遞服務用電動三輪車技術要求》行業標準,各城市也陸續出臺了一些管理措施。例如,從2014年2月28日起,石家莊的快遞三輪都開始統一涂色(綠色),并在車身的指定部位噴有醒目的圖標(包括速遞企業品牌、石市快遞、石郵管等)。一些快遞公司還在三輪車車身的顯著位置貼上了公司的宣傳貼,統一了快遞人員的著裝,以便于居民在第一時間內區別出快遞公司的名字。貨運三輪車的規范,可以說是對配送微循環的一種有效解決途徑,盡管伴隨城市形象的提升,貨的會對其進行替代,但城市的擁堵狀況反過來又會對其進行較大的促進。
(二)城市貨的
對于許多啟動城市共同配送項目的城市來說,最大的變化莫過于貨的的出現,涂有統一色調的面包貨車開始在城區24小時通行無限制。城市貨的主要解決大件貨物和快速配送問題,它改變了那種在專業市場等待需求、從市場前往目的地裝載貨物、把貨物送達至客戶指定地點、空車返回的傳統模式。貨的運營,一般是由政府或企業搭建共同配送平臺統一指揮,調度中心依據GIS/GPS定位安排線路,實施就近配送、積載配送、捎帶配送等多種方式。貨的的運行不僅實現了客戶的快速響應,更大幅降低了空載率、空駛率,有效提升了城市配送效率,其中深圳、沈陽等市的貨的運營已證明了此論斷。
然而,城市共同配送體系的建設是一個整體,貨的確實在貨運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絕對不應是主體。貨的只是相當于客運中的出租車而已,它是城市配送中一種補充,而貨運中的主體——公共交通(共同配送)仍在探索中。正如出租汽車不可能替代公交車一樣,以面包車為主的貨的在交通指標中都是耗費最大的,這不得不讓人進行深思。此外,對城市貨運出租車投放數量目前還缺少科學測算,如果管理掌控不好,可能就會帶來大量空駛,導致更加擁堵的可能。
(三)企業直接配送
在傳統的城市交通管理中,用于通勤的家庭汽車占有主要地位,不論是街道的擴張還是停車管理,基本是都是以車為本的思維定勢。自1994年我國汽車工業發展政策的提出,民用汽車保有量開始出現快速增長,尤其是2005年以后私人轎車每年增長率都高于20%。與私人轎車相對應的配送車輛則是城市配送主力軍的企業直接配送車輛。關于大型連鎖超市配送的調查顯示[6],達80%滿載率的車輛不足六成、達60%滿載率的車輛在兩成左右,另兩成則需臨時補貨或商品更新而進行隨機配送,送達后基本是空載駛回。
實際上,大型連鎖超市的配送車輛還不完全屬于小汽車的對比對象,其更像是客運中的單位班車;與小汽車相對的應是未達到規模的眾多企業配送車輛、以及面向分散的終端客戶配送車輛。此外,在城市貨運的士出現后,過于分散的配送線路完全可以交于貨的進行配送;而配送起始點中的某一個相對集中情況下,則可采用班車的形式,規模后的班車自然會向著共同配送的方向發展。為此,城市貨運車輛的限行更多地應是針對那些零散運營的配送車輛,而具有共同配送性質的貨運車輛不僅不應限行,還應大力倡導。零散運營車輛的發展終點則是通過聯合形成規模、或被規模型配送企業兼并。
(四)共同配送車輛
現代城市的發展模式是TOD,而且隨著城市半徑的增加,軌道交通所占比例也會越來越高。比如北京市居民出行統計中,地鐵在2000年占3.6%,2009年突破10%,而2013年達到了20.6%;而近10多年來公共汽車占比則基本上穩定于25%左右[4]。盡管近幾年來,我國各大城市都在大力推進城市共同配送,但與TOD模式下的“公共交通”對應的配送車輛卻仍處于襁褓之中。那么,城市共同配送是企業主導還是政府主導呢?從目前來看,我國各城市管理者的初衷仍然是企業,比如北京的城市100、快行線等。
典型的共同配送模式也基本是以貨主為主體的共同配送、或以物流業者為主體的共同配送,以及企業間的橫向或縱向合作的共同配送。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哪種合作都是以提高載貨率、縮短配送里程、節約物流成本為基礎的,且多是以汽車為主體工具的。問題在于這些共同配送運營方式,更像是客運中的班車運輸,而非公交車、軌道交通。那么,正如城市客運交通中倡導的“公交+慢行”的理念一樣,貨運交通發展之路也應是“公交+三輪車”為主、貨的為輔的“公交式”共同配送模式。在“公交式”配送中,不僅要重視地上貨運車輛運營的線路、節點設置,更要關注地下軌道、管道物流系統的建設,例如地鐵空閑時隙貨運、德國城市鼴鼠項目等。
四、城市共同配送體系
O′Kelly于1987年提出的軸—輻式理論,現已廣泛應用于交通規劃、節點選址等領域,例如航線網絡、郵政網絡、金融網點等。軸—輻式的配送過程為典型的LD-CED運作模式,其中LD代表配送中心(Logistics/Distribution Centre),CED(Collection Exchange Delivery)為收集—交換—發送。樞紐作為軸、輻射線為輻,輻上又可含次級樞紐,配送貨物先到達一個樞紐(配送節點),經中轉換載后再送至次級樞紐,直至到達客戶手中。結合典型的三級配送網絡體系、城市公交運營線路,并考慮到街道的分布情況,城市共同配送網絡體系主要由集散中心、配送中心、末端節點及相應道路網絡組成(見圖2)。
(一)配送節點
城市配送節點主要指城市配送中心和各級配送網點,其中的配送網點包括社區內各種超市配送站、路邊停靠點、大型超市和商廈的接貨地點、需求主體臨時需求的送貨地等。從配送性質上來分,網絡節點包含配送節點、客戶節點兩種類型;而從配送運作過程上,其又包括兩大部分,即配送網絡節點間的配送過程、基層配送網點到客戶之間的配送過程。配送節點設置的數量及位置,不僅與城市面積、客戶需求等有關,也與企業規模、運營策略等相關,其中的一個關鍵指標便是配送服務半徑。配送服務半徑往往是一個相對優化、合理的配送距離,代表了某一節點的覆蓋(或服務)面積,其大小不僅取決于客戶的密集程度,也受到配送節點層次、服務效率指標、城區道路布局、以及競爭戰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約。
外圍的集散中心一般是依據城市發展規劃,結合產業結構、居住環境等,由城市管理者綜合設定的;而配送中心則更多是由企業自己設置的,其往往位于企業的貨源樞紐、原有業務地域,或根據業務需求、政策引導而確定的;而城市中心區的配送節點布局,基本上都是由企業依據業務流量、客戶分布、道路及地價,利用某種數學模型(如線性規劃選址)計算所得。比較典型的配送網絡布局可參考中國郵政,利用郵政編碼將城市劃分為多個區域,然后依次設郵電支局、郵電所,并在單位、小區內設傳達室或報箱;而順豐速遞在許多二線城市中,則是以7公里為服務半徑設置“分部”,再在“分部”下設若干“點部”的。
(二)接力配送
除少數客戶外,城市配送基本上都是接力配送形式。類似于接力賽跑,每個運輸車輛僅負責指定區域或線路的貨物配送,例如:長途運輸的大型車輛負責將貨物運輸至城市外圍的集散中心(大型貨車是禁止進入市區的),然后由中型貨車將貨物運至配送中心,再由輕型、微型貨車把貨物從配送中心開始實施送達服務、或送至末端節點,而末端節點多采用三輪車、自行車實現客戶送達服務。通過各級節點間的“中轉換乘”,可最大限度地利用車載容量。從理論上來講,接力配送可以有效增加車輛的裝載率、提高客戶的服務效率,同時便于客戶、供應商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及時發現并解決配送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然而,貨物不能像行人一樣能夠自行換乘,需通過裝卸搬運來完成“中轉換載”功能,那么如何實現貨物的快速、低成本的中轉就成了關鍵所在。干線運輸中常采用集裝箱、甩掛等形式來實現中轉,而歐盟則提出了城市物流配送Citylog項目計劃。Citylog項目主要由Bento配送箱系統、小型集裝箱系統、貨運巴士、終端配送小車等相關內容組成,其主要指導原則便是物流單元化設計思想[7](見圖3)。
“貨運巴士+貨的”的配送模式,將干線運輸與最后100米配送進行了有效融合;而Bento配送箱的模塊化思想,又為中轉換乘提供了效率的保障。以輕微型貨車為主的貨運的士將小型集裝箱運送至城市內的中轉作業區(配送節點),并在這里快速地與貨運巴士完成中轉(類似于集裝箱運輸的港口、車站的中轉)。Bento配送箱的獨立與封閉性,送達與交接的時間就可以實現分離,只要將配送箱送至指定地點卸載,客戶可以根據自己的時間進行驗收(類似于掛在單元樓內的信報箱、牛奶箱的作用),從而配送車輛可完全根據交通流量情況擇時送達,自然也就排除了夜間配送實施障礙。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充當貨運巴士的廂式貨車還可以改用軌道交通(地鐵)實現,而貨的也可以由三輪車來充當。
(三)末端配送
傳統配送一般都是將貨物直接送至客戶手中(即門到門),在客戶聚集、貨品小散、時間差異較大時,往往消耗配送人員大量等候時間、或往返路徑。所謂末端配送就是在配送中心到客戶中間又加了一個節點——末端配送節點(如校園、社區快件收發點),末端節點到終端客戶的配送即末端配送,也稱“最后100米”配送。末端共同配送在有效解決客戶需求空間、時間的分散性問題,同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電子商務的爆發,可以說是促使各個速遞公司建設末端節點的催化劑,現有的末端共同配送模式主要有便利店式、收發室式、信報箱式等。
(1)便利店式。傳統社區(街道、村莊)小賣鋪多與居民較為熟悉,可為其代為保管貨物。快遞公司與社區零售店合作后,快件送至店鋪后由客戶自行提貨,在大量減少配送人員挨家挨戶送達、等待時間的同時,也為零售店增加了客源與到達頻次,此種雙贏模式的典型代表就是7-11便利店。荷蘭Kiala通過“便利店”網點的運營,相比于傳統“送貨上門”來說,配送車輛數和車輛總路程均減少約85%,CO2排放量減少60%~81%[8]。
(2)收發室式。為了能按時接收各種報刊、信件、包裹等,郵政系統在學校、政府、大型企事業單位、商務區等都設有收發室。電商及速遞的迅猛發展,又賦予了收發室新的功能,即末端配送節點。不同的是,傳統的收發室主要是為中國郵政提供服務,而新式收發室(如京東派、菜鳥驛站)則是為各個電商企業、速遞公司提供單一或多種功能的服務。而北京“城市100”所建的末端“共同配送門店”,原則上也可以算作收發室式的共同配送。
(3)信報箱式。居民社區設置信報箱的優點在于,解決了送信人員與客戶的時間錯位,同時也減少了送信者的行走距離。而各個速遞公司在消費者取貨便利場所設置的“自提柜”,實質上就是信報箱的一種升級換代。信報箱常常一戶一箱,而“自提柜”則是多個客戶、甚至多個速遞公司分時段共用一箱,開啟箱門不再是憑借鑰匙而是密碼。典型的代表便是“速易遞”,其在為眾多中小速遞企業提供共享平臺的同時,也創新了末端配送的運營模式。
五、幾個尚待抉擇的問題
集約化是實現共同配送的前提,也就是說在城市配送的起始點、中轉節點、送達點中應至少有某一個環節具有高度的集中性。譬如,家電的廠家直接配送模式,就源于國內家電品牌的集約化,配送的起始點的高度集中。然而,三個環節極度分散性卻是多數城市配送的基本情況,這不僅有市場發展的因素,也源于城市先期布局、客戶需求多樣性等方面的原因。
第一,運營主體的抉擇。公共交通的運營主體一般為國控公交公司,也有部分城市引入了競爭元素,如北京巴士傳媒股份、運通集團等。有關城市共同配送的運營主體,多數城市都是采用扶持當地具有一定實力的配送企業,這種模式的直接效果便是貨運的士的興起,但很難具有TOD模式的效果。如何使大型企業加入到城市共同配送大軍,而又不出現早期的物流規劃用地變為企業圈地行為的怪相,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應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其實這也是城市早期發展客運交通的實施策略,同時也有利于眾多中小配送企業走上配送聯盟的道路。
第二,大型商超的作用。商圈共同配送本應是城市配送的一個典范,如同7-11一樣,因為它具有中轉節點(店面)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但縱觀我國城市內的各大超市、商場,其所在地段的繁華與擁堵程度幾乎是等同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一是商超的強勢地位,致使眾多供應商的快速、及時地配送,政府倡導的夜間配送幾乎無人問津;二是眾多商超占用了本就稀缺的停車場所(如地下停車場),更談不上自備足夠的停車、卸貨空間,致使道路兩側的公共用地(自行車道、人行道、綠地等)成了商家的“自留地”。而規范商超的客貨通道與場所,往往又會遇到各方面的阻力,并最終形成了城市管理的盲區。
第三,末端節點之爭。末端配送節點的設置,則是力圖將分散的需求點進行集約化,尤其是對貨件流量巨大的校園和CBD區域。然而,由于電商、速遞企業競爭的白熱化,幾乎是每個企業都獨立建有自己的末端節點,這顯然違背了共同配送的集約化理念。另外,因顧及成本等方面的因素,許多末端節點設施簡陋、業務尚待規范,這不僅有毀于企業的自身形象,也是其高質量服務的一大隱患。聯盟雖可以解決任何一個環節的集約化問題,并能快速提升整體服務質量,但在行業約定(法規)、企業信用等多方面還有待完善。在現有物流市場環境下,也不得不面臨著利潤分配(或費用分擔)這一重大障礙。
第四,互聯網+配送。在互聯網+的時代,物流運營模式也正發生著巨變,其典型的趨勢包括全國平臺→城市配送、車貨匹配平臺→物流應用工具、單干→聯盟、物流網人→互聯網人的變化。移動互聯網、智能手機的誕生,讓配送信息的共享成為可能,若再結合GPS、GIS、RFID等物流技術,完全可以實現物流公司所提出的“運輸過程透明管理”。雖然,有關物流信息公共平臺運營主體的爭論不斷,但本人認為城市共同配送平臺的主體必須是城市管理者。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從城市整體角度、公平公正地為所有共同配送企業來提供服務,正如率先做出抉擇的太原、南京等市一樣。
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在城市共同配送發展中,一定有一個先試水、被認知,然后再爆發的過程,即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盡管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但城市實施共同配送的趨勢如同發展TOD模式一樣是不可逆轉的,目前許多城市正處于從局部慢慢延展開來的階段,只有通過所有人的共同來努力,才能做到城市環境、居民出行、物流配送等多方面的協同發展,為打造生態城市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 2013年物流運行情況分析與2014年展望[J]. 中國物流與采購,2014(6): 61-65.
[2] 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統計年鑒、統計公報(1995~2014)[D/OL]. http://www.stats. gov.cn/tjsj.
[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15 Highlights [EB/OL]. http://www.iea.org/statistics/topics/CO2emissions.
[4] 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北京交通發展年報(2001~2014)[D/OL]. http://www.bjtrc.org.cn.
[5] 劉賢騰.城市交通方式競爭態勢及來自生態學的理論啟示[J].城市規劃學刊,2012(5): 66-75.
[6] 張迪,鄔躍,陳雷. 城市共同配送影響因素調查分析[J]. 物流技術,2012(5):36-39.
[7]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city logistics. Final Report[D/OL]. http://www.city-log.eu.
[8] 楊朋玨. 電子商務環境下城市末端共同配送網點選址研究[D]. 上海:上海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