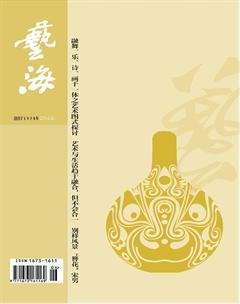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眾審美表征轉(zhuǎn)變的啟示
林雙鵬
〔摘要〕我們的文化形態(tài)確實經(jīng)歷了單元到多元、匱乏到豐富的顯性漸變過程,管中窺豹看待大眾與精英審美間關(guān)系轉(zhuǎn)變也可見一斑,盡管主流價值觀客觀上促成文藝領(lǐng)域的利好的繁榮局面,但改變一個民族的某些特質(zhì)也許根本不是幾代人可以完成的,這種潛在的不易察覺的思維慣性,還要經(jīng)過更為漫長的思想解鎖過程。
〔關(guān)鍵詞〕文化形態(tài)審美慣性西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衛(wèi)美術(shù)家與批評家默契地將藝術(shù)創(chuàng)作、批評與大眾審美保持距離,以維持精英階層的堅守,大眾作為審美主體隨著時代的逐漸開放與認知領(lǐng)域的拓寬,嘗試著有選擇地接受新鮮事物。藝術(shù)史的發(fā)展是人類文明史的另一種書寫形式,而東西方社會發(fā)展階段的落差決定了我們社會層面西化的歷史必要性,同時美術(shù)領(lǐng)域的西化也變得順理成章了。工業(yè)社會、科技發(fā)展與“工具理性”形態(tài)下的藝術(shù)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主義傾向,現(xiàn)代主義通過英雄主義式的個人意志表達對抗非人性,非個人化官僚與科技的抽象體質(zhì),這與重視普遍、共通社會經(jīng)驗的前現(xiàn)代是背道而馳的,一定意義上說這種主張精英化不愿與群眾合流的形態(tài)對大眾文化存在一種本能的排斥態(tài)度。
美本身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的大眾審美構(gòu)建似乎逐漸擺脫某種四海同一的尷尬層面,多個側(cè)面可體現(xiàn)逐漸寬松的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變化,審美也從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炮制的理想國回到爭議頻仍的社會現(xiàn)實。狹義美的方面,精英們開始討論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開始了解西洋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藝術(shù)思潮。開化的過程中,我們由對美術(shù)領(lǐng)域的欣賞習(xí)慣被迫滯留在模式化認識狀態(tài),轉(zhuǎn)向帶著思考與參與性介入對藝術(shù)品或藝術(shù)事件的解讀,由對西方藝術(shù)史發(fā)展的認知持有抵觸情緒發(fā)展到能夠結(jié)合20世紀重要理論問世與美術(shù)流派建立內(nèi)在聯(lián)系,正如弗洛伊德著作《夢的解析》理論影響到了超現(xiàn)實主義畫家達利;畢加索利用視覺移動方式創(chuàng)立立體主義,正是受到《相對論》中時間這一第四維概念的影響,而這些需要背景知識深入了解的西方藝術(shù),對于剛解決溫飽問題的中國大眾而言有著極大落差與信息不對等,賞心悅目的視覺欣賞習(xí)慣與固有的東方文化傳統(tǒng)思維,使得大眾與前衛(wèi)藝術(shù)之間無形地建立起壁壘,人們更本能的接受民俗文化的直觀視覺感受,如剪紙、年畫、鵝蛋圓臉電影明星的畫片,建立在寫實基礎(chǔ)上內(nèi)容大于形式的歷史或青春題材畫作等。事實上,自西方現(xiàn)代主義開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根本動力就幾乎歷史性的摒棄了滿足人們一般意義上的審美慣性,進而追求形式與觀念的革命性思考領(lǐng)域。
大眾審美是相對滯后的。最大的隔閡往往在于相當(dāng)比例人群認為藝術(shù)是一個與自身并不密切相關(guān)的事物,而并非意識到對藝術(shù)的欣賞、判斷以及感悟是一個個體綜合素養(yǎng)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shù)與生活一致的跡象表現(xiàn)得顯而易見的莫過于希臘的雕塑史,在制作云石的人或青銅的人之前,他們先制造活生生的人,他們的第一流雕塑是和造成完美的身體的尺度同時發(fā)展的,兩者形影不離”。希臘人創(chuàng)作出西方藝術(shù)史最偉大的高峰的前提在于對健美身體的贊美及其天然合理性,年輕的充滿活力的生命對西方人而言是本能的謳歌對象,這幾乎是大眾審美與藝術(shù)行為之間最為默契的互為因果。
當(dāng)批判性質(zhì)的傷痕文學(xué)不再是學(xué)界的關(guān)注點,似乎被大眾淡忘的有深刻時代烙印的朦朧詩歌漸漸地同那個充滿理想的年代而不復(fù)存在,歌舞升平的電視廣播形式作為主流傳媒占據(jù)著大眾眼球,聯(lián)歡會形式的中國文藝塑造著大眾審美框架,影視劇成為大眾茶余的談資。而大銀幕的部分探索者堅持著理想主義,諸如所謂的中國第五、六代電影,舶來了西洋電影本體語言的同時從敘事格式到角度、態(tài)度都較有品質(zhì)比較真實客觀的反應(yīng)歷史轉(zhuǎn)型時期的社會問題和緊繃的人性,關(guān)注且平視平民與邊緣人群的視角都與定義曖昧模糊的某些價值觀背后的虛假層面相映射。大環(huán)境相對進步的意識形態(tài)一般使得審美處于良性狀態(tài),人們有暇開始探討人性、倫理與社會問題。對時尚的追求既有傳統(tǒng)的元素又參伴著國際化標準,在時尚資源相對匱乏的環(huán)境下,媒體的單元化使曾經(jīng)暢銷期刊的封面男女明星,從發(fā)型到服飾都成為大眾追捧與效仿的對象,成為全民浪潮。變革的時代使得每一代人的成長經(jīng)歷中有著諸多類似的經(jīng)歷與審美體驗,各藝術(shù)門類的發(fā)展都離不開生存的土壤與環(huán)境。當(dāng)如今的青年人沉浸在卡通與美劇帶來的多方位刺激時,培養(yǎng)對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興趣就顯得尤為困難。這使得青年一代價值觀形成與格調(diào)品味培養(yǎng)逐漸凸顯出必要性。雖然歷史上最優(yōu)文化的傳承從來都是由少部分人來完成,且自會有深愛這一領(lǐng)域的群體,但良好的文化土壤才是枝繁葉茂的關(guān)鍵所在,此事乏善可陳。雖然從另外角度說,開放意味著良與莠的雙重介入,大眾審美庸俗化與快餐化不可簡單歸咎于經(jīng)濟和時代的進步,但大眾整體審美水準才是體現(xiàn)一個時代風(fēng)貌的不爭事實。
教育能改變什么呢,不論胡適之的問題與主義之辯,對白話文的提倡,還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德育,我們都可從中提煉出精英階層對上層建筑與社會經(jīng)濟基礎(chǔ)之間關(guān)系的不同角度與不同觀點,或是試圖解決大眾認知變革問題,新文化革了舊文化的命,新道德取締舊道德,大眾的審美因此會有顯著的提升嗎,這很難評價。時至今日,利好的各方面環(huán)境帶動著大眾對多種文化行為的參與積極性,信息化時代與互聯(lián)網(wǎng)思維將幾乎所有社會分子帶入媒體時代,每個個體都可能突然被鎂光聚焦成為熱點,資訊的發(fā)達程度更是史無前例的增長速度,如此這般最優(yōu)格調(diào)的文化形態(tài)并不能自然的被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這與教育程度、認知水平、溝通環(huán)境等太多個體差異的因素相關(guān);我們還沒有進入西方現(xiàn)代主義至今所建立起來的審美大眾對新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打破原有框架的寬容審美心態(tài),而幾乎還滯留在唯美層面,或是叛逆期帶給青年人狂熱的流行亞文化。這也許是中小學(xué)美術(shù)課堂的失敗,亦或是實用主義與應(yīng)試教育的必然結(jié)果,真正進入美術(shù)館式教育模式培養(yǎng)下一代的認識是極少數(shù)家庭能意識到的,這一定程度受到地域條件、家庭教育觀念、優(yōu)質(zhì)資源分布不均等現(xiàn)實問題的限制。
無論是啟蒙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極速發(fā)展中的目下中國,正是筆者從學(xué)習(xí)性認知到經(jīng)歷性認知的三十幾年,我們的文化形態(tài)確實經(jīng)歷了單元到多元、匱乏到豐富的顯性漸變過程,管中窺豹看待大眾與精英審美間關(guān)系轉(zhuǎn)變也可見一斑,盡管主流價值觀客觀上促成文藝領(lǐng)域的利好的繁榮局面,但改變一個民族的某些特質(zhì)也許根本不是幾代人可以完成的,以音樂作比,曾有偏激的觀點認為漢民族從古至今就缺少音樂創(chuàng)造力。不論時代意識形態(tài)碰撞如何激烈與頻仍,似乎依然是橋歸橋路歸路,一般缺少中間地帶的各自維系著自我固有審美習(xí)慣與認知。但高度網(wǎng)絡(luò)信息化的今天,似乎定論是注定要被顛覆的。無論純藝術(shù)與純文學(xué)以外的事物是否該被定義到審美概念中,密切與之相關(guān)的人類交際活動早已是現(xiàn)實存在,作為今天日益發(fā)達的網(wǎng)絡(luò)與其它非傳統(tǒng)媒介也窮盡其新聞效應(yīng)之能事,電子傳媒把我們從美帶到搞笑,雅俗合流,傳媒在販賣產(chǎn)品的同時也販賣了文化所有的終極意義。日常生活審美化表面上是對人的感性解放,實質(zhì)上卻是“工具理性”對于人的更為無情的操控,是在盲目歌頌技術(shù)力量的同時將自有定位在消費能力上面,而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文理性對于人的存在與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意義”。尺度寬泛的網(wǎng)絡(luò)文化,娛樂至上直指眼球效應(yīng)的新聞炒作,深入挖掘了人隱性的窺私心理,部分前衛(wèi)藝術(shù)家對繁雜當(dāng)代社會文化與亞文化元素挪用、揶揄或調(diào)侃方式進行藝術(shù)行為的同時,其自身同樣不可選擇的置身其中。然而批判民族性與西化又不啻是逃避之舉。良莠不齊的標準印證多元化與國際化帶來的值得深思的影響……
中國社會思想碰撞這三十余年的社會變遷頻仍,前衛(wèi)美術(shù)發(fā)展作為中國當(dāng)代社會的文化表征之一經(jīng)歷了各種社會事件的悉數(shù)粉墨登場,曾經(jīng)一度萬人空巷,之后又淡出人們視野,銷聲匿跡,審美的轉(zhuǎn)變必然的服從于表象背后的啟蒙與人文思潮的意識形態(tài)主流。曾經(jīng)高壓政治的文化環(huán)境是話語權(quán)獨裁的溫床,文藝的單一與匱乏客觀上將幾代人思維、意識、審美模式化,也許至今我們依舊是文革僵硬的政治文藝理論背景束縛下的二代三代,這種潛在的不易察覺的思維慣性還要經(jīng)過更為漫長的思想解鎖過程。甚至可以說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講從未發(fā)生過根本性的審美轉(zhuǎn)變,更多的是具有東方古典舊有審美慣性的國人,對新鮮社會事件與新思想新花樣的或激烈或平淡的本能反應(yīng),或是過去三十年放置于歷史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某個結(jié)點,不足以改變我們固有意識,但不論改變與否,或褒或貶,不予片面定論,讓它留給未來與時間。
(責(zé)任編輯:曉芳)
參考文獻:
[1]丹納《藝術(shù)哲學(xué)》第四編.第三章制度.224頁.天津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2007.5
[2]陸揚《文化研究概論》213頁.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8.1
[3]徐建融《美術(shù)人類學(xué)》黑龍江美術(shù)出版社.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