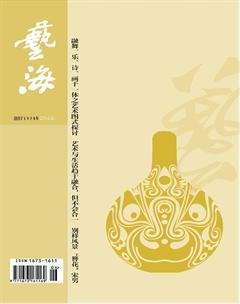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談《紅樓夢》文本的動態性
薛瑩
〔摘要〕《紅樓夢》發展的歷史,即是讀者對文本接受、閱讀與反應的過程,是一場審美經驗的歷程。讀者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不斷的賦予和重塑著紅樓文本的生命力。在紅學日益成為顯學的歷史條件下,回歸文本,從文本出發解讀紅樓顯得非常重要。
〔關鍵詞〕文本接受美學動態性
法國文學批評家圣伯夫曾經說過“最偉大的詩人不是創作得最多的詩人,而是啟發得最多的詩人”,這句話用來形容曹雪芹最恰當不過的了,終其一生,“批閱十載,增刪五次”寫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誰解其中味呢?概莫不過是后世這些品、評紅樓的粉絲們的追捧。換句話說,是紅樓的接受者,通過讀者對紅樓的接受、反應、閱讀,讀者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在賦予和重塑紅樓文本的生命力上功不可沒。正是在歷史———社會條件下的審美感知和審美經驗,使《紅樓夢》成為真正意義上完整的、活力、經久不衰的顯示出其強大藝術生命力的文本。
姚斯在1972年《審美經驗一辯》中說,“根據接受美學理論,藝術作品的本質建立在其歷史性上,即建立在它與大眾不斷對話所產生的效果上;藝術學與社會的關系只能在解釋學的問答邏輯的辯證關系中加以把握;藝術史唯獨涉及傳統和理解接受間的視野變化”。此美學原理應用在《紅樓夢》,一方面肯定了接受者在紅樓文本發展中的作用顯著,一方面也昭示了紅樓文本的動態性。小說作為一種時間藝術,本身就具有隨著閱讀而展開畫面、豐富畫面的動態性。而紅樓文本的偉大之處在于,它超越一般小說的發展的共性規律,展示了它動態發展的特殊性。
一、刻意留白
顧名思義,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應的空白,是中國畫的一種布局與智慧。畫如果過滿過實,在構圖上就失去了靈動與飄逸,顯得死氣沉沉;而有了留白,便給予觀賞者以遐想和發揮的空間。我們觀齊白石的蝦,才能感受到水的清澈與靈動;賞徐悲鴻的馬,才能體味到風的速度。最難忘南宋馬遠的《寒江獨釣圖》,一幅畫中,一只葉舟,一漁翁垂釣,整幅畫中沒有一絲水,而讓人感到煙波浩渺,滿幅皆水。予人以想象之余地。如此以無勝有的留白藝術,正所謂“此處無物勝有物”。文學上的留白便是指“言有盡而意無窮”。文學意象所傳達的經驗,多半是表象的相互暗示、錯綜交織,具有不可限定性,意義含混,內容豐富。巧妙地運用“留白”這一藝術技巧,可以給讀者留下豐富的解讀空間。芹溪先生無疑是靈活運用留白藝術的大家,意義空白沒有使紅樓夢失色,反而使文本更顯玄妙。紅樓夢的敘事中有多處斷層和空白,甚至是疑點。比如秦可卿何以會第五回就死去?死因為何?寶釵進京待選秀女,后事如何?第57回“慈姨媽愛語慰癡顰”薛姨媽答應向老祖宗提寶黛親事,卻沒有后文;賈政為何喜歡趙姨娘?賈璉何以會被稱為璉二爺?《紅樓夢》中的空白遠遠不止這些,而這些空白也為眾讀者所津津樂道與解讀揣測。作者把疑問留給了讀者,在文本和接受者之間形成了審美主客體互動的關系。作者同時也將答案交給了讀者,而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讀者的解答都是合理的,都是依據特定的審美經驗而獲得的。留白所帶來的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角度的讀者對文本的解讀,是紅樓發展史上不可忽視的篇章。紅樓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解讀史,它是顯示了紅樓文本的動態性。在王國維那里,《紅樓夢》是一部解脫的書,宣揚解脫之道;而索引派認為《紅樓夢》是具有極強政治性的映射小說;認為《紅樓夢》是自傳小說的也大有人在。
《紅樓夢》是動態文本,同時也是抒情性、意向性的詩性的文本,仿佛置身流連忘返的園林之中,“如過小橋,如循曲徑,流連間不覺風光已殊。但一回首,剛才的一山一水猶在望中,始知作家筆質精工,落墨甚遠”。正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的園林藝術“建筑的平面鋪開的有機群體,實際已把空間意識轉化為時間進程”,空間藝術與時間藝術合而為一,在這里形容《紅樓夢》文本的動態性,非常形象。
二、文本的對話性
文本的對話性,主要體現在《紅樓夢》話題的多重性上。你可以認為《紅樓夢》是關于爭取思想自主與愛情自由的言情小說;也可以認為它是寫家族興衰榮辱的社會小說;還可以認為它是為群芳立傳的傳記小說,等等。作為開放結構的小說,《紅樓夢》寫愛情,不是單一的,它不僅寫寶黛的純情、悲情;還有賈蕓與小紅,藕官與芳官等缺憾性的愛情;家族命運的興衰,群芳的去留?寶玉的執于情還是絕于情?美與丑?善與惡?寶釵是美的還是丑的,是善的還是惡?王熙鳳的手段與目的是沖突的還是和諧的?這里沒有道德宣判,卻提供了道德影響。對話性還體現在紅樓夢的敘事方式上,作者以一個鮮活的話語主體身份出現,其語言重心、色彩都側重于展示主體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力求使它退隱到客觀現象深處,消融較大的語境中。《紅樓夢》采用作者助言,這源于作者不加掩飾的自我抒情角色,這個角色可以幻化為其他形態,但是其“作者原型”還是比較明顯。《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以作者自云的方式開篇,接著以說書人的立場講述,使讀者仿佛身臨現場,與作者一起見證一場家族興衰的歷史,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一場繁華即逝的夢境。在此過程中,讀者的參與性非常強,《紅樓夢》留給讀者的問題太多,要理解這些問題,關鍵還是要以文本為依托,深入理解文本的過程,就是與文本對話的過程。
《紅樓夢》的文本是對話性的,通過與文本的對話,讀者深化著對生活的理解和對生命的認識。這種對話是開放性的,不是結論性的。文本的對話性,體現著文本的互動與律動性。
三、心理接受的動態性
還是引用姚斯的觀點。他認為,一部作品,即使印成書,讀者沒有閱讀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這充分說明讀者的閱讀接受在完整和豐富作品文本上的重要性。所以作為文本組成部分的接受者,心理接受的動態性也要視為文本的動態性。
《紅樓夢》以神話開篇,故事情節貫穿于仙界與凡界,前世與今生,閱讀者需跟隨作者一起上天入地,穿越古今,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在有情與無情之間掙扎;禮教與詩社之間取舍;在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之間慟哭;這些對立性因素構成一個似動結構,造成藝術接受心理明顯的動態性。
王國維曾言“覽過《紅樓夢》之后,念其珠圍翠繞者,鈍根也;覽過《紅樓夢》之后,念其色即是空者,解脫者也”。這句話把紅樓夢的閱讀者一分為二,也可以視為對紅樓閱讀感受的境界說。一開始閱讀紅樓,大部分讀者會被紅樓夢的美人、美景、美食、美好的情感以及嘆為觀止的園林藝術所吸引,以至于和作者一起沉醉其中,及至“呼啦啦大廈傾”時,才如夢初醒,然而夢醒遠遠沒有夢中令人愉悅。就我本人而言,覽過紅樓數遍,依然對49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念念不忘,其詩情與雪景,梅香與群芳薈萃時的團圓和諧之美,使此回成為120回中最光彩奪目的一章。依王國維此言,沉迷于紅樓溫柔鄉的,不知多少人會成為“鈍根”。而且閱讀紅樓夢,往往不可避免的走上道德評判的路子,釵黛孰優孰劣?王熙鳳是好人壞人?秦可卿人品如何?隨著閱讀和閱歷的增長,依專業所長,從美學角度解讀紅樓是水到渠成的。雖未必成為領略“色即是空”的解脫者,對紅樓的認識卻在不斷地深化。在關照文本的基礎上,跳出文本,再沉迷于紅樓溫柔鄉的同時,進一步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就此來講,讀者的心理接受是不斷成長變化的。
藝術在超越生活的欲求上關照人生,對《紅樓夢》的解讀要在尊重文本客觀性的基礎上,從更高更契合文本層面上來欣賞,避免顧此失彼的道德評判。這也是讀者心理接受的正常發展軌跡。
《紅樓夢》作為中國古典小說中的代表,四大名著之首,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偉大作品。自成書的400年來,一直炙手可熱,由于版本居多,欣賞角度和立場的不同,分別派生出文學批評派、索隱派、自傳派等數派。由研究此書的思想文化、作者原意等,而形成紅學。紅學發展的歷史,是讀者對文本接受、閱讀與反應的過程,是一場審美經驗的歷程。讀者的審美經驗以及接受效果,不斷的賦予和重塑著紅樓文本的生命力。在紅學日益成為顯學的歷史條件下,回歸文本,從文本出發解讀《紅樓夢》顯得非常重要。接受美學為我們從文本出發研究《紅樓夢》,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論指導。在尊重文本客觀性的基礎上,從更高更契合文本層面上來欣賞。(責任編輯:曉芳)
參考文獻:
[1]《紅樓夢校注》曹雪芹、高鶚原著,其庸等校注。1984年4月出版
[2]《紅樓夢美學闡釋》孫偉科著,云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3]《紅樓夢評論》王國維著
[4]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