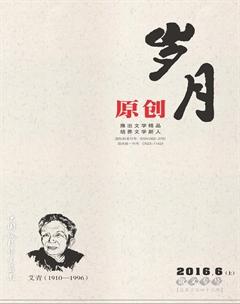消失的土地
鹿悠悠
我住的地方
寫作通常開始于自我經驗的覺醒,記憶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是最寶貴的資源。一個有豐富記憶資源的寫作者很容易建立起獨有的美學框架,他的敘述往往會有很高的辨識度。我時常懊惱自己這種資源的缺失,甚至因為沒有精彩的童年回憶而羞赧,在少年時代我就沒有可以連通同齡世界的話題。我的童年是反鎖的大門、沒有閉路線的電視機和一架子的書。對于寫作這件事情有熱情,可是沒有牢固的故事做我的城墻。
于是我看向自己,像審視一個陌生人的童年一樣,看看不太多的人生經歷里,有沒有精彩的故事被忽略。
你不得不承認,你現(xiàn)在的樣子就是少年生存的土地滋養(yǎng)出來的。這些舊的記憶可以用來把玩,用來溫暖或者治愈漫長的暮年時光。甚至很多難解的事情都可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從那些往事里找到原因。我首先把目光投向我住的地方。故鄉(xiāng)應該是這樣一個地方,有舊的記憶,有相似的飲食習慣和一樣的鄉(xiāng)音。先說吃,我的鄰居里有一個川妹子,我們在外面玩兒的時候,她爸爸總端一碗飯追在后面喂她,那一碗飯通常是白米飯加辣椒醬,我想不通她爸爸愛她還是不愛她;還有一個浙江的阿姨,她家總有很好吃的梅干菜扣肉,我媽就不會做;我家吃面條是用清水過一下的,就那樣吃,沒有鹵。我爸說這樣最好吃,但是我一直痛恨面條,確實是痛恨,沒滋沒味的,我又沒有膽量剩飯,所以面條被我認定是這個世界上最難吃的東西,直到高中住校我才發(fā)現(xiàn)其實面條可以好吃,只要放鹵。
再說鄉(xiāng)音,我們這兒的孩子,普通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要是去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不用做太多的準備至少都是二級甲等水平。那個時候我們對普通話質樸的向往和毫不掩飾的崇拜,就表現(xiàn)在誰要是操著不一樣的口音,在小孩子中是一定會被欺負的。比如四川妹子,她就管吃飯叫“撕飯”,我們每天的功課就是圍住她教她說話。當年我們都是小姑娘,而她是更小的姑娘。每一天都不許她跟我們做游戲,必須先學會正確的發(fā)音,我想,川妹子的童年記憶也許并不愉快。每一個到我家做客的小伙伴都跟我反映聽不懂我爸說話,那個時候我覺得很丟臉,怎么這么多年都學不會普通話呢,現(xiàn)在想來,我爸可能根本就不想改變他的口音。我可以為每一個來我家的人當翻譯,所以現(xiàn)在很多詞都被方方正正地鎖在記憶里,“不知道”要說“知不道”;“晚上”那叫“夜來后晌”;還有一個代表停頓沒有實際意義的虛詞,意思類似于“嗯……”發(fā)音類似“哪尼戶地”;最讓我驕傲的是,我會一個簡單又神奇的發(fā)音——“啊”,嘴巴不用張大,發(fā)音位置不用舌面,要用喉嚨。這個詞最神奇的地方在于,你其余的發(fā)音可以不太準確,只要在表示同意的時候,標準地發(fā)了這個音,我爸保證會夸我……還有好多詞,寫出來是那么不生動。
我童年的啟蒙文字不是詩歌而是老家的地址。我爸三個字一頓,念得很有節(jié)奏,我也跟著三個字一頓,背得很有節(jié)奏。我被灌輸著一個神秘的地址,在我還不認識字形的時候就千百次地聽爸說:你一定要記住。我無數(shù)次地困惑于他的強調,這與我有什么關系。那個遙遠的地方沒有提供給我生活的任何條件,即使我記住了,又有什么用。最終變成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地址。假如有一天我有了下一代,他會怎么理解這個地址和他之間的聯(lián)系。因為我認真地背誦這個地址,從此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說的所有的話,都帶著山東口音。以至于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淄博”的“淄”其實是平舌音。我用通用的語言面對這個世界,從我開始學會說話和那些經過生活千錘百煉的語言就有不可逾越的距離,學會它們對我來說像學一門新的語言,發(fā)音不地道,詞匯也掌握不了,然而語言是你迅速歸鄉(xiāng)的佐證,少小離家,只要一站在故鄉(xiāng)的土地上,只要你能用地道的家鄉(xiāng)話問路,就能立刻打開通往故鄉(xiāng)的鑰匙。這把鑰匙,被我們弄丟了,丟了就是丟了,找不回來了。
爸牽掛的那個老家我回去過三次。第一次,奶奶還在,河水還清,姐夫在家撐溜子,姐姐還養(yǎng)著很多荷花,我還能鉆進葦子編的籃子里。第二次,我再回去,奶奶不在了,姐夫出國了,河上飄著綠藻,荷塘不養(yǎng)了,再想下河要給一個陌生人十塊錢才能坐上溜子。唯獨姑姑的房子還是沒變,廁所還是旱廁。炕上坐著一群孩子,我一進屋呼啦站起來一堆。孩子們都不說話。我被拉著,挨個認,說這個是大姐家的,那個是二姐家的……第三次,姑姑也不在了,站在她的小屋后面隔著青綠的葦帳子,遠遠能看見壓路機卷起的灰塵,蒙住你看向更遠的視線。炕還在,只是炕上沒有人。問及當年的那幾個孩子,姐姐說他們上班呢,要等到下班才能回來。過了一會兒,回來一個抱著頭盔的少年,見我羞澀地一笑,再沒有當年從炕上被人拽起來,小聲叫小姑的神情。我們把時間都蹉跎到哪里去了,怎么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孩子一下子就長成了少年,唇邊柔軟的小絨毛變硬,身邊還站著他的小女朋友。人生情節(jié)相似地循環(huán)上演,可是有什么東西正在悄悄離開。
盡管我能把爸的口音模仿得惟妙惟肖,還是不理解爸的牽掛。對我來說,關上門的地方就是家。對爸來說,馬踏湖和湖里的蘆葦,才是家。他給我講馬踏湖,我就記掛湖里的金絲鴨蛋,他給我講院子里的樹,我只想念樹上的青棗。在這個地方,很多人的老家都在遙遠的地方。于是我習慣了那種好像靈魂安放在另一處的感覺。仿佛我們都是蒲公英的種子,安心扎在一處。但只要聚在一起,就開心地講著遠處那個自己不熟悉,也不熟悉自己的地方。
要說共同的記憶,我和我的小伙伴們的記憶就斷篇兒了。兒時的小伙伴,經常前一天還在一起玩兒,第二天就來通知我們,她要回上海了,或者要回浙江了。奇怪得很,我們都是在這里出生的,怎么去那么遠的地方反而叫“回”呢。我兒時的玩伴就這么“回去”了一大半。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是否是家鄉(xiāng),是否應該認同它產生了懷疑,現(xiàn)在看來其實我們都是移民的后代。這個地方歷史短暫,不像別的地方,總是那么神奇,也總是那么有魅力,總能從犄角旮旯找出點歷史的痕跡。在這兒,除了遠古的化石,再也沒有別的可炫耀的東西。
被離開的家園
我們總是需要一個家園為我們提供生命的能量,做自己強大后盾,可以生發(fā)出無窮的力量。只不過現(xiàn)在這個家園具體多了,我們更在乎有沒有房子。大部分人都已經不在乎有沒有土地了,沒有一塊屬于我的地,依然可以生存。并且不會有離開土地就會無所依傍的慌張感。家的標志不再是鄉(xiāng)音,不再是熟悉的植物和村里的老狗,而是我們能否在一大串鑰匙之中,熟悉又迅速地摸到能打開家門的那一把。離開很容易,回去并不容易。我不能一踏上那片叫做故鄉(xiāng)的土地就自然而然地熱淚盈眶。可是我想我應該不會再回到那片土地上去了。對于它來說,我是它灑向世界的種子。
我在這座城市里,隨時都可以聽到關于“被離開”的一些故事。有些人和我父親那種為了理想離開家鄉(xiāng)不同,他們是懶洋洋地等在家里,自然有人叫他們離開。在公交車上,無意聽見兩個人的對話,其中一個指著世紀大道說,“這么寬的路,你看連一個門市房都沒有?你看,你看。我就不相信,這么寬的路會沒人走。這要是開一個門市房,干點兒啥,人來人往,不就來生意了么。”我在心里說:你也太不了解這座城市了。這條路上哪里會人來人往。這里只有幾個單位,上班時間我們都在辦公樓里,哪里會有人出來照顧你的生意。何況這條路拓寬是為了走車的,哪里是為了走人的。接下來兩個人很熱烈地談論起來淮北老家,誰家的地被占了用于掏煤,誰家地被占了用來蓋房子,蓋房子和掏煤哪一種會獲得更多的賠償。沒有人感慨丟失了土地,離開了家園,他們感慨的是,“掏煤的”給的賠償多于“蓋房子的”,被掏煤的那一家一下子就過上了富足的生活。用的都是我能聽懂的普通話,幾乎沒有口音,我想他們離開土地,就再也回不去了,可能都不會想要回去。
還有一次出租車司機和我聊天說:“今天街上都沒人呀,都去逛屯子了。”“屯子”這個詞對我來說實在是很陌生。他告訴我,開發(fā)商占了他的地,這才有錢買了出租車。他說:“我媳婦還說沒有地心里沒底,我就告訴我媳婦,沒事兒,買車,開車,跑活兒,家里錢攢著,想吃啥吃啥,想吃豆角就吃豆角,想吃茄子就吃茄子。”這是一個被城市擴張簇擁著離開土地的人。接下來的一路上,他一直在給我講不同品種的豆角的區(qū)別,哪一種更好吃。這對我來說太難了,實在是想象不出豆角和豆角之間有什么不同。
這么多人都逐漸離開了土地,沒有人表現(xiàn)出我想象中的失望和留戀,反而很期盼快點能有什么力量占了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蓋房子或者掏煤。人再也不像是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植物了,更像飄在半空中的風箏。
記錄著消失
最終還是要回歸到寫作上。寫作是一種記錄,記錄下一代人成長的軌跡,記錄下逐漸遠去的那些人和事。
故鄉(xiāng)的消失無異于精神臍帶的斷裂,當我們都成長成了獨立的個體,能獨自面對這個世界,如果沒有溫暖又堅實的后盾,就缺少了一種情懷。我渴望用不斷地寫完成不斷地追尋的過程。追尋遠去的家園,追尋最初的溫暖。寫作是家園的最后一方陣地,如果有一天所有寫作者的文字都不再指向故鄉(xiāng)深厚的土地,那我們的家園就真的失守了。
所以,我很認同祝勇說的“中國的城市管理者們對城市的特質缺乏起碼的認識。他們似乎對現(xiàn)在更情有獨鐘,為了與現(xiàn)在保持同步,我們城市總是以一副動蕩不定的面貌出現(xiàn)——到處是工地,拆除與重建的工作反復進行,具有傳統(tǒng)價值的老房子遭到拋棄。漂泊不定的現(xiàn)在使我們永遠站在一個點上,而不是一條延續(xù)線上。這使我們四顧茫然,孤立無援,既不了解來路也無法判定去處。浮華的都市里隱藏著‘我們從何處來,到何處去的原始困惑。”不斷地拆解逐漸瓦解著我們的集體記憶,被標榜的個人體驗快感正在占據(jù)情感表達的大部分空間。
城市早就作為機器存在,日夜喧嘩,試圖展現(xiàn)自己的高貴和個性,殊不知在鄉(xiāng)土強大的生存能力面前,這些都是可以被不屑一顧的。在最遙遠的鄉(xiāng)間,你總能找到新鮮的去處。而城市,日趨相同的面孔正在消滅著鄉(xiāng)土的色彩。
這一點你可以在任何一個城市的古鎮(zhèn)或者古巷里找到答案。他們兜售一樣的商品,甚至商鋪陳設方式都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古鎮(zhèn)或者古巷的名字還沒變,作為一塊招牌招攬著游客。拆了再建,城市的規(guī)模越來越相似,最有生命力的東西已經不在古巷。
鄉(xiāng)土是我們的文化背景,背景越豐富我們越有底氣。可是我們離鄉(xiāng)土越來越遠,但是鄉(xiāng)土在文學中還保持著相當強大的勢力。文學如果失去這樣的生命現(xiàn)場,就會越來越輕。在這些地方空靈地探討所謂生存環(huán)境是不現(xiàn)實的。因為城市的保護隨時都在,不存在突然沒有了明天的困境。我們的問題在于關注的生命細節(jié)太多,以至于一切都顯得那么的不珍貴。那些虛無縹緲的心靈雞湯,聽多了讓人牙疼。
文字越來越精致,對文本的分析越來越清楚,對敘事方式,敘事節(jié)奏,敘事風格分門別類,文章仿佛被規(guī)規(guī)矩矩地放在一個又一個的小格子里,文學系想要講哪一種類型,伸手去哪一個小格子里信手拈來。文字像是被教育成老成少年的小孩子,說大人的話并且以為自豪,迅速地得到成人世界的認可,似乎是一件幸事。其實任何一個成年人都清楚,老遲早是要來的,而年輕,過去就不會再回來了。這樣時間久了,文字很容易失去生命力。我不希望語言總是充斥著聽起來很高級的概念型詞匯,似乎變得奇詭有趣,無所不能,所有的道理都能講得出來。成功人士的客廳文學正在蓬勃發(fā)展,華麗、單調、疲倦、虛無。文字顯得很熱鬧,唯獨缺少了最簡單的、最有原始力量的生命力。
我們不會再寫《荷塘月色》那樣的東西了,因為那個存在的時代變了。那種“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也沒有”的安靜已然不復存在。我們不再面對生存的艱難環(huán)境,只需要面對生活的競爭和各種人為制造的生存悖論。
自然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語境。其實我沒有離開過生我的地方,所以也就沒有任何的鄉(xiāng)愁可言。但是我更能體會“離開變得容易。”因為我們沒有土地的牽掛,沒有兄弟姐妹,到哪里都沒有漂泊無鄉(xiāng)的異鄉(xiāng)感。我們回家鄉(xiāng)的感覺也不是少小離家的感覺。
當我們?yōu)榱烁玫纳睿阶咴竭h;當我們被生活磨出繭皮的手掌再一次拿起心愛的樂器;當我們因為勞動變得僵硬的關節(jié),再次開始舞蹈的時候;當我們的精神陷于困頓的時候,歸鄉(xiāng)是一個永恒的命題。專注于家園能對寫作保持敏感。鄉(xiāng)土會讓我們有強大的傾訴欲望。理想中的鄉(xiāng)土世界應該很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節(jié)奏,是保有靈魂的地方,就像素手白描,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才有的真正的回憶。
希望有一天早上,睜開眼,陽光恰好照在額頭上,故鄉(xiāng)那片土地上的故事因此而永生,但我抗拒趨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