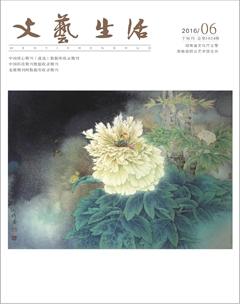韋伯:世界的除魅與確立新神
楊玉亭
摘 要:19世紀,韋伯生活的德國,終于達成了政治上的統一,并迫切希望達成價值的整合。但是在整個歐洲,走出中世紀之后卻形成了一種價值多元的僵局——諸神之爭。為了消解舊有體系的魅力,韋伯根據自己的思想對社會提出了“除魅”,并在價值的取舍,即確立“新神”上作出了嘗試。
關鍵詞:國家統一;價值整合;諸神之爭;除魅;新神
中圖分類號:C9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18-0061-01
韋伯是西方社會學的三大創始人之一,他以理解與理解的社會學、因果多元論、價值中立和理想類型來確立了社會學的方法論,那么,在認識社會的過程中,韋伯又提出了怎樣的觀點?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韋伯所處的時代背景:舊的天主教貪婪暴虐的耶和華與新教圣潔博大的上帝似乎完全不是同一個神;在17、18世紀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后,人人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申述自己的立場,反而使得價值觀一片混亂;資本主義與宗教特別是新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近代資本主義一方面是榮耀上帝的見證,一方面又是新教倫理的掘墓者;科學的發展使人們一方面有著征服自然的狂想,另一方面又因為技術的不發達而在自然面前畏畏縮縮……就這樣,“諸神之爭”成為了韋伯用來指稱現代西方走出一神統治之后價值多元局面的一個命題。
在他看來,解決“諸神之爭”這一混亂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除魅”。
一、世界的“除魅”
讓人類自造的“魅”——宗教、政治、超自然力量以及這一切的代言人,在人類社會中雜交,錯位,絕對不會利于發現人類社會的規律。只要社會還是在神和精靈的掌控之下,它就不具有可預見性。但是人們如果能夠將“魅”驅逐,那么人們就可能以一種更為穩定的方式來對待自然和社會,社會也就更容易接受理性解釋。
那么如何對世界進行除魅?韋伯的著作解釋得非常清楚:“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進,并不意味著人對生存條件的一般知識也隨之增加。但這里含有另一層意義,即這樣的知識或信念:只要人們想知道,他任何時候都能夠知道;從原則上說,再也沒有什么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而這就意味著為世界除魅。”①這樣一種“除魅”的觀點,非常近似于我們今天反復提到的“科學”。
二、韋伯確立“新神”的嘗試
韋伯可能在確立“新神”即追求一種“絕對價值”上做出了他小心翼翼的嘗試。
在達到“絕對價值”之前,首先要建構一套精確而嚴謹的概念體系來增強客觀性,減少主觀隨意性。這就需要研究者借助“理想類型”的該男體系作為衡量現實的標準,審視現實與概念之間的差距,并對這種差距作出因果解釋。
韋伯曾經不無崇敬地提出魅力型統治的理論,當然,將領袖或者制度作為終極價值,成為“新神”,不免落入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囹圄,也有曲解的嫌疑。但是魅力型統治仍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傳統化和理性化。韋伯將這一過程稱之為“魅力的平凡化”。魅力平凡化的結果,是魅力型統治轉向傳統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或者成為二者的混合形式。對韋伯來說,這可能不是良好的精神歸宿。
在新教倫理方面,這種確立的嘗試同樣行不通。誠然,新教徒通過天職觀和禁欲主義倫理把履行世俗職業的義務尊崇為一個人道德行為的最高形式,這樣使得日常世俗行為有了一種宗教的意義,工作追求財富成為一個人的天職。正是“天職”觀念使工人和企業家在復雜的經濟行為中獲得了共同的倫理基礎和精神動力,成為了塑造資本主義精神的關鍵因素。但是,由于財富的增長,人們對于享受現實幸福的一切熱愛隨之增強了,對享受的欲望隨之膨脹,“尋求上帝的天國的狂熱開始逐漸轉變為冷靜的經濟德性;宗教的要求慢慢枯死,讓位于世俗的功利主義”。②
既然在制度與精神文化思想(或者說宗教)方面碰壁之后,韋伯只能從“驅魅”處獲得一個避風港,吁求學者克制先知與煽動家沖動,保持一種助人形成清明頭腦的理性,從而幫助人們理智地自守。
這樣一種不明確的態度使得追求樹立“新神”的嘗試最終無解,韋伯對未來社會徹底的悲觀可能來源于此。也許像涂爾干一樣,追求社會整合形式的嘗試對于價值整合來說并不一定成功,但是在行為上值得一試,畢竟,這個選擇是向善的。
三、結語
韋伯的思想充滿了悲觀的論調,甚至有人說韋伯預言了世界大戰中德國必然失敗的前景。飽受精神分裂的過程中,他也是一直處于一種妄念的狀態里,也在不自覺中得到了“學術界的俾斯麥”這樣令人生畏的稱號。在對自己的“驅魅”和“立神”的過程中,這種實踐的結果卻遠遠超出了韋伯理論體系的價值意義。
注釋:
①馬克斯·韋伯,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29.
②馬克斯·韋伯,馮克利(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138.
參考文獻:
[1]韋伯,于曉(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95.
[2]候鈞生.西方社會學理論教程[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3]韋伯,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韋伯,楊富斌(譯).社會科學方法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