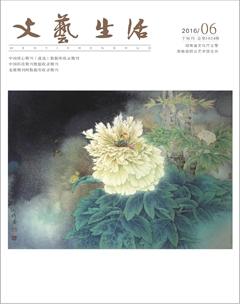鞏義石窟寺飛天樂舞初探
楊磊 袁文彬
摘 要:鞏義石窟是北魏后期開鑿的石窟,其規模雖不大但精細程度與雕刻技藝足以令人稱贊,尤其是石窟中的飛天樂舞形象更是絕妙精美。從這些精美的飛天樂舞形象中,我們不但可以了解佛教藝術在當時的發展狀況,還能夠與古代文獻記載相結合探究其演變的原因,為中國古代舞蹈斷代史的研究盡綿薄之力。
關鍵詞:鞏義石窟;飛天樂舞;佛教藝術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6)17-0076-01
中國佛教石窟藝術是宗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集合體,主要表現佛教故事與義理,同時也是研究中國古代舞蹈史乃至中外舞蹈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資料。與佛教東傳不斷漢化一樣,中國的佛教石窟雕塑藝術在雕刻技法與審美趨勢也越來越顯示出中國的風格和特點。中國的石窟寺大約興起于公元4世紀,公元5至8世紀進入鼎盛時期,至晚唐之后才漸趨衰落。“它是佛教寺院的一種形式,多依山崖開鑿……由于古代地面建筑多已毀壞,只保留了洞窟遺跡,故也簡稱石窟。”①
一、鞏義石窟寺開鑿的時代背景
鞏義位于黃河中下游南岸,洛陽以東,中岳嵩山北麓,是伊水與洛水交匯處的一座小城。鞏義石窟寺位于鞏義市區以北的大力山下,最早開鑿與北魏宣武帝時期,之后北齊、隋、唐、宋等朝代都在此相繼開鑿或雕刻了一些佛像或佛龕。
公元439年,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統一了黃河流域,結束了中國北方混亂的局面,與偏安江左的劉宋隔江對峙,中國歷史開始進入南北朝時期。此時,距兩漢之交佛教傳入中國早已過去了四百多年。佛教在此時期不斷與中國文化相融合,而融合的過程對于佛教雕塑藝術逐漸趨于中國化也起到了促進作用。北魏政權建立后先后開鑿了云岡石窟、龍門石窟、鞏義石窟等一些石窟。而這些石窟中佛教雕塑藝術風格的變化應當可以看做是佛教雕塑藝術進一步中國化與少數民族漢化的一個寫照。在開鑿于北魏宣武帝時期的鞏義石窟中,最大的洞窟面積大不過四五十平方米,雖然不能與云岡、龍門這些有著數十乃至上百平方米的大洞窟相比,但是鞏義石窟雕刻的精美程度和較高的藝術價值卻遠不輸于它們。
二、鞏義石窟寺“飛天”樂舞的分布及形態
鞏義石窟寺現存五個石窟。從現存的石窟佛龕和佛像來看,不但雕刻極其精美,具備了相當高的藝術價值,而且保存狀況也比龍門石窟相對要好。在現存的五個石窟中除了第二窟未開鑿完之外,剩下的四窟都已完工。在鞏義石窟寺的五個石窟中,“飛天”保存得也相對完整,它們主要分布在窟內佛龕的頂部和兩側,還有窟內東西窟壁下以及洞窟的窟頂上。
第一窟在中心柱西面佛龕兩側有三對“飛天”。最下邊的一對身體面向佛龕單膝跪地,身披飄帶,頭戴寶冠,手執蓮花,神情頗為莊重。中間一對“飛天”身披飄帶,雙手合十,神情莊重座于蓮臺之上,身上的長帶飄揚仿佛身在白云之間。最頂部的一對是伎樂“飛天”。南側的“飛天”報琵琶彈奏,北側的“飛天”握長笛吹曲。這對伎樂“飛天”頭戴寶冠,身披飄帶,姿態健美,體態輕盈,仿佛天女下凡一般。第一窟中心柱南面佛龕兩側的“飛天”動感十足。右側的“飛天”右手執花樹、左手拿貢品,側曲雙膝頭像微向后看,面部安詳略帶微笑,身上的飄帶凌空飄蕩。左側“飛天”雙手執花樹,雙膝側曲頭部向身體的正前方看去。這兩對“飛天”剛好是一靜一動,這種靜與動的對比更襯托出佛龕中佛像的崇高與神秘色彩。第一窟除了北面墻壁外,東南西三面墻壁下均有伎樂浮雕圖。樂器分別為鼓、琴、竽、笛、磬、阮咸、排蕭、羯鼓、法螺和箜篌。 在第三窟中心柱南面佛龕上刻有鞏義石窟寺最為精美的一對“飛天”。左側的“飛天”面容清秀,右手持蓮花,左手持貢品,頭戴寶冠,胸佩瓔珞。右側“飛天”高鼻深目,左手持蓮花,右手托蓮蕾,頭向身后望去。這一對身披飄帶的“飛天”飄逸輕盈之姿態好似御風而行。尤其是右側的“飛天”雕刻得更是極其精美,她高鼻深目的面部雖然更多的體現出了西北方少數民族的五官特點,但是仔細觀之面容卻依然清美秀麗,這是典型的南朝秀骨清像之風。這一漢一胡的一對“飛天”更是體現了在北魏孝文帝遷都漢化后,鮮卑族與漢族民族融合的結果,使得佛教藝術民族化的發展趨勢更為顯著。
第五窟是鞏義石窟中最小的也是唯一沒有中心柱的一窟。窟頂刻有一個較大的蓮花藻井,在蓮花藻井的周圍雕有六個“飛天”在環繞著蓮花藻井漫天飛舞。她們身披飄帶在云海及花叢中穿梭翱翔,而身體的線條也較北魏早期的飛天優美許多。此時南朝秀骨清像的雕刻風格也逐漸地在北魏后期的石窟人物雕刻中凸現出來。而第五窟窟頂的“飛天”無論是身體線條的雕刻,還是面部表情的塑造也的確有一種秀美、婉約、清麗的風格。
佛教是當今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它雖起源于印度但自從傳入中國,它就與中國文化相融。在這期間,它的教義經文幾乎不曾變動,且深入人心并被歷朝歷代的譯經家翻譯成文廣為傳頌。但跟隨佛教一起傳入中國的佛教雕塑藝術卻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按照其不同的民族藝術特征、民族審美心里從而傳播、發展。舞蹈是運動的藝術。在古代沒有現代攝影技術的情況下,那些存在于石窟壁畫上樂舞形象就成為了我們研究中國古代舞蹈的珍貴資料。這對中國古代舞蹈斷代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幫助。舞蹈史雖然是對歷史的研究,但是它區別于其它藝術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對舞蹈動作形象的研究。它可以使孤寂的舞蹈文物獲得重生,這也就是對佛教石窟飛天樂舞研究的重要意義所在。
注釋:
①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中國美術史教研室.中國美術簡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