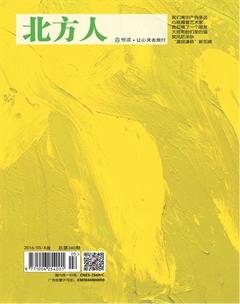我們離中產有多遠
王小妮
無意中看到兩條和“錢”有關的新聞。
一條據稱來自外媒的報道: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排名第二的有錢國,中產階級數量已經過億,每十個中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是中產階級。
另外一條是一起命案:某人在聊天群里搶了個3分錢的紅包,沒有按聊天群的規則及時派錢給別人,自顧自去睡覺,引起群友不滿,找他理論,沖突從虛擬空間升級到現實中,他們見面后由爭執演變成打斗,沒按規矩及時派錢的人被刀刺傷后身亡。
兩條新聞,涉及的數值,大到了億;涉及錢的金額,小到了分。
錢能兌換安逸、安全嗎
有錢是什么概念,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
向幾個年輕人問這問題,他們幾乎都不假思索地回答:“有錢好,想吃什么吃什么。”
吃,真的這么重要嗎?
他們反問我:“如果吃不重要,還有什么更重要?”
前不久,應約去一個年輕人家里吃飯,10年前他讀大一的時候,我給他上過課。記得有人在作業里寫他主動借錢給同宿舍里沒錢為飯卡充值的同學,他自己吃干饅頭,因為他家里也貧窮。
我曾經請過他和幾個同學來玩,是我做飯。現在輪到他親自下廚招待我了。
端上從四川鄉下老家里帶來的臘鴨燒土豆,他說:“現在想吃什么終于不是個問題了。”
一般說來,一個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能做到想吃什么吃什么,要在畢業后努力工作3年到4年,這期間從事任何一份職業都要任勞任怨,不挑肥揀瘦,特別是實習期的第一份工作,什么苛刻條件都要盡量接受。可以跳槽,最好不是被辭退。家人都得健康,不能意外生大病。一點點地改善租房條件,不要不切實際地幻想貸款做房奴,人總不能一步登天。最好留在大城市,雖然花銷高,但收入也會相對高,主要是機會多。
這么多條件都聚合在一起,假以時日,才可能想吃什么吃什么。
按前面新聞里說的,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富裕的國家,在我們前面的只有一個美國了;這條新聞還說到,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總量已經達到全球之首,有1.09億人,占全國成年人口的11%,在絕對數字上,已經超越了美國,美國的中產階級只有9200萬人。這里給中產階級的定位標準是:擁有5萬到50萬美元的財富,折合人民幣大約32萬到320萬元。
再看看百度百科給中產階級下的定義:中產階級(中產階層),是指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且中等層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較好滿足的人群。
我把百度這條定義說得再通俗一點:“吃飽穿暖,活得安全、安逸,又有尊嚴。”假設數量超過一億的人都不再為吃穿發愁,緊接著就必然追求安全、安逸和尊嚴。和金錢相比,這些不好量化的感受的界線在哪兒?安全和不安全、安逸和不安逸、有尊嚴和沒尊嚴之間的彈性究竟有多大?
不再教書以后,時常聯系的學生還有十幾個,他們在最近幾年里先后進入了社會,正是對人生有最多憧憬、渾身充滿活力的年紀,可我常從側面感到他們的煩躁、焦慮、苦惱,除了掙到了可自由支配的錢以外,他們好像缺少20多歲的人天然擁有的單純和快樂。
如果不是平時對他們有所了解,可能會簡單地說他們“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
前幾天教師節,一位同學留言問好,我隨口問她:“每天高興吧?”
她回答:“不高興也裝得很高興。”
知道她是大咧咧的人,我調侃她:“裝著裝著,就有點真高興了才好。”
她回道:“是的,自己不高興,別人會更高興。”
看著最后這一行字,我心里忽然跳出薩特那句“他人即地獄”。
深陷在被毀壞的、逆向惡化著的人際關系中,才能發出這樣的感慨吧。
我們曾經有過人人自危、人人揭發檢舉的年代,那噩夢終究過去了,在看上去還正常的生活里,相似的緊張并沒有緩解,甚至有進一步惡化的態勢,比如連“老人能不能去扶”也要討論。
不久前從香港回深圳,過了閘口,只看見滾滾人流,他們不是涌上來的,幾乎是直接踩過來。隨時有人目光發直地拖著箱子橫沖直撞而去,高聲呼喊同伴的突然斜沖出來,黑車拉客的迎面攔截行人,四面八方都是噪音。
這些近旁瑣事,如影隨形地緊跟著我們,在無意中勾逗著無名之火。
三分錢有價值嗎
分值人民幣大約在20年前就失去了使用價值,不再流通了。
3分錢在50年前,也只能買一根最便宜的冰棍。誰會想到在二十一世紀,它竟成了一個人的“命價”。
有人會說,新聞中這個人不是因為3分錢而死,是因為他破壞了規則。可看看我們周邊,無視規則的事少嗎?規則真被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不如說是某種無名之火要找個發泄口,被一個領了3分錢紅包就去睡覺的人撞上了。
我問一個熟人:“最近看你好像不高興?”
他說:“是,因為我發現,沒有人對我好,即使有人幫我,也說不定帶著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問:“平時你對別人好嗎?”
他反問:“憑什么我要對別人好?”
我得說明一下,這只是兩個人心平氣和的閑聊。
各種各樣的不如意,使得身邊坐著的某個安靜的人在看了一會兒手機后,忽然惱怒起身。
挑戰我們想像力和接受力的新聞總是不期而至,荒誕和刺激的大事總也不缺。它們雖然大,卻離我們遠,那種感同身受常常只是短暫地被觸動。我們可以自我安慰說,它離我們很遠,可以推托說我們很無力,但它似乎還是在潛移默化地侵害我們。
消化那些讓人懊惱的事情,成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成了我們自己的日課。
而真真切切發生在自己近前的事情,當然只能由自己面對和解決。
面對這么多、這么密集的真刀真槍,我們好像還沒學會良性地處理和排解,這時候最簡捷有效的方法就是迎頭反擊。
3分錢或者30萬都不過充當個引線,張口去罵,伸手去打,已經不知不覺中成了自衛和反擊的新常態。想出手時就出手,不只是梁山好漢的行事方式,所謂中產階級時刻可能成為暴力施加者,也可能是受害者。看起來我們離安全、安逸、有尊嚴真是遠著呢。
善的存在
曾經是礦難,后來是動車事故,再后來是野蠻拆遷,再后來有城管和小販,感情好像也在習慣,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麻木。現在電視里再直播井下救援,觀眾還會看嗎?這一頁已經被我們大家一起翻過去了。
懸念劇輪換場次,更刺激的下一幕總在邊幕候場,而日出日落,生活繼續著,我們在不知不覺和淡忘里,變得脆弱易怒,對于壞事情的應激反應或者過度,或者麻木。有人身處一觸即發的狀態,被不明火氣攪擾著,誰知道我們這些氣球還能撐多久。
那么,善還存在嗎?
更多的時候,是偽善常見。
有人戴上假面、披了“馬甲”立刻渾身是膽,一旦卸掉掩護,重又變回生活中的唯唯諾諾,見風使舵;很多崇尚暴力的人心里跟明鏡兒一樣,只在超級安全甚至有利可圖的狀態下,才發出惡言惡語——這時候的言語已經和憤怒沒多大關系了,因為它脫離了個人情緒,替代以更加強悍有力的群體情緒。
如果憤怒甚至咒罵成了一門生意,受害者自然會增多。更多人對惡語傷害避之不及,會退卻去求助于“雞湯”,好像泡在“雞湯”里才能得到補償和慰藉。可被攪痛過的神經卻像不可愈合的疤痕,總要揭開,總會一次次以不同的疼痛方式來侵擾我們。
我們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們本能地以物喜,以己悲,常常感覺到物傷其類和兔死狐悲。
這時候急著命名說那個人是中產階級,是準備指著那位的鼻子去激怒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