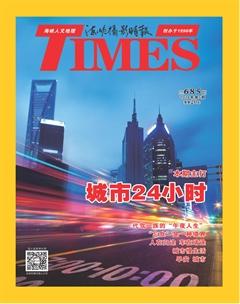代駕一族的“午夜人生”
陳拯 林原


代駕是城市的守夜人,他們穿梭在觥籌交錯的喧嘩之外,目睹一段段醉態人生。雖然他們的工作是開著別人的車,走在別人的回家路上,但他們駕著的,是自己的生活。
自從“醉駕入刑”規定出臺后,代駕行業發展迅猛,他們被認為從事著都市深夜中最有“前景”的職業。
北京無疑是國內應酬和酒局最多的城市,也是代駕需求最大的城市,這些互聯網代駕平臺上的司機,都至少擁有5年以上駕齡,他們之中有全職、兼職,平均每天接單在3到4單,也有人可以接到8到10單,收入在兩三千元到上萬元不等。
電動滑板車、自行車,是代駕一族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接到訂單后,他們會把代步工具放到客人汽車的后備箱,以便到達目的地后離開。如果去比較偏僻的地方,打不到車或者舍不得花錢打車,就只能靠這些代步工具回到四環,再坐夜班公交車。如果電動滑板車沒電了,那就只剩下推著走這個辦法了。
在酒吧,保安一般都有自己替客人叫代駕的方式。互聯網代駕平臺興起后,酒吧保安和外來代駕司機之間難免會發生摩擦。2016年3月12日,北京工體西路一家酒吧的保安因為不滿代駕司機在酒吧前的路邊等待訂單,動手推倒了代駕司機的代步電動車,雙方發生了沖突,代駕司機報警后,30多名代駕在酒吧門口等待警察討要說法,要求涉事保安露面道歉。“那個保安始終沒有再出現。”一名目睹事件的代駕說。
陳師傅是一位全職代駕,平均每天接3到4單活。“最難受的是冬天,大風大雪天在酒吧外站著,凍得腳趾頭都沒感覺了”,他說,那樣的天氣,他把手機從兜里掏出來,手機很快就被凍到關機。去年冬天,他送一個客人去昌平一個別墅區,為了趕回四環接單,他在雪地里蹬了16公里自行車才打到車。
趙師傅也是一位全職代駕,每天晚上7點準時上線干活,工作到第二天凌晨4到5點,平均每天接3到4單活。長時間地在夜晚工作,他養成了晚上不喝水的習慣,每天晚飯必須吃飽喝足,晚上在外面不敢喝水,上廁所不方便。他的代步工具是個電動滑板車,續航不到30公里,有一次凌晨在大興,車沒電了,他推著車走了8公里,邊走邊用手機打車,到了6環附近才打上車,“每天不固定地方,晚上滿北京跑,不管去了哪,都要想方設法回四環,才能繼續接單。”
李師傅已經做了一年多。他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冬天送一位客人回香河,“那一單一百多塊,那地方有點偏,結果打車花了一百,跑那么遠掙的,就剩下一個零頭”,他說,那是半夜一點多,風特別大,當時走在路上,心里特別不是滋味,“后來也只能一笑而過了,沒辦法的事”。李師傅在做代駕以前,工作是給別人開車當司機,相比之下,他覺得做代駕并不辛苦,而且更自由,“我更喜歡現在”。
專職代駕張師傅每天從晚上7點工作到第二天凌晨5點。這幾個月,他偶爾還會想起去年的一筆“損失”:一筆三百的賬單,客人沒給結,后來電話也打不通了。“剛開始我催過兩次,人家還挺客氣,說在忙回頭結,我也不好意思一直問,后來再打就打不通了。”代駕平臺的客服也幫張師傅催過,最后也不了了之,他知道這錢沒希望要回來了,“挺可惜的,那時候正是最冷的時候,這是自己的勞動,也是一筆損失啊。”
劉師傅2015年一直在老家山東泰安做代駕,2016年1月13號開始轉戰北京。叫代駕的車主形形色色,他也遇到過一些酒品不好的人。“就一次,客人上車就開始罵我,從酒吧門口一直罵到二環上,正好遇到查酒駕,我打開車門就下車,交警一看就過來把我按倒了,以為我酒駕要跑,我說我是代駕,這位顧客罵我罵得讓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不想開了。”劉師傅轉頭向后座客人說,“哥你今天投訴我也好,怎么也好,今天這單我沒法做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要愿意開自己開吧。”客人一看這情形,馬上不罵了,緩過神來趕忙跟他道歉,“我還是上車把他送回去了”,劉師傅說,自己當過兵,如果不是實在受不了了,也不會這樣。
從老家來北京后,劉師傅每天能接7到8單,是平臺上的銅牌司機。他每天從晚上7點工作到第二天早上6點,從1月13號到3月13號,除去過年幾天休息,一共做了340單。他說自己是好運氣加上經驗:用定位功能好點的手機,不去扎堆的地方,“每次送到地方,我不急著往扎堆的地方趕,就查查小區附近有沒有大點的餐館,有的話就去等,絕對出單”,出去接單,他一直蹬著自行車,“做了5個多月,瘦了30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