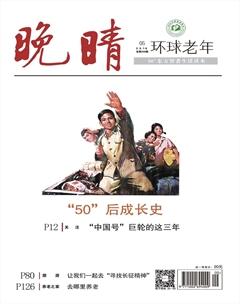捐獻:生命的禮物
王怡波
在器官捐獻和移植體系中,捐獻是一個起點。捐獻者發起生命轉移,協調員牽線搭橋,使得已經逝去的生命得以以另外的方式延續下來。
悲痛抉擇
在2015年全國完成2766例器官捐獻的基礎上,兩歲小女孩“小不點”的器官捐獻成為2016年的最早案例之一:1月1日,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黃埔醫院,“小不點”捐獻了她的肝臟、腎臟和眼角膜。此時距離事故發生時,剛過一周。
2015年平安夜,“小不點”因車禍被送到醫院搶救,由于傷勢嚴重,最終住進了東莞東華醫院重癥監護室。在病房外,母親徐霞偶然看見擺在架子上的紅十字會關于器官捐獻的宣傳冊。在知道女兒生命已無法挽回時,她決定捐獻女兒的器官,“有用的用一下,我們也高興一點,為社會做一點點貢獻”。
跟醫院溝通后,醫院聯系了紅十字會的協調員,很快,當天他們就辦好了捐獻手續。元旦前,“小不點”被轉院至器官獲取和移植技術十分成熟的黃埔醫院。雖然黃埔醫院盡力挽救,但最終,2016年元旦,噩耗來臨。“小不點”的生命旅程結束了,而她的器官也迅速開始挽救他人生命的旅程。
生命使者
如果不是放在東華醫院里的紅十字會宣傳冊,徐霞一家人可能不會跟器官捐獻發生關系。“以前老人肯定不會同意捐獻。但是我們現在一代一代要改變思想觀念。”徐霞說。這種觀念的改變,也是一兩年來中國器官捐獻例數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而觀念為什么會改變?在莊一強看來,最根本的還是器官捐獻事業公開透明了,而包括紅十字會協調員和醫院OPO組織專業協調員在內的“生命使者”隊伍,起到了最直接的推廣作用。
“紅十字會的協調員與社工類似,不一定是學醫的,主要負責器官捐獻的宣傳推廣,并去做家屬的溝通和協調工作,更多地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協調員。”莊一強介紹,而醫院的專業協調員,本身就是醫護人員,他們更多地進行一些更專業的捐獻相關工作,例如,發現潛在的器官捐贈者,評估潛在器官捐贈者全身的狀況、器官的功能狀況,了解家屬是不是愿意做器官捐贈,進而協調神經醫學專家,對捐贈者的生命狀況進行判定。
在黃潔夫看來,“協調員是器官捐獻工作中間最辛苦最有貢獻的一群人”。他將他們譽為“生命使者”,并用自己去年所得的一些大獎的獎金在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下面,專門設立了“生命使者”種子基金,用以支持協調員工作。
而之前的十年,大家對器官捐獻不僅是不了解,更多地是不信任。
2005年9月,以志愿者身份在深圳市紅十字會辦公室值班的高敏,接到了一個來自湖北天門的電話。電話中,一名女子告訴高敏,她女兒遭遇車禍,快不行了,想把器官捐給紅十字會,可是打了好多地方紅十字會的電話,沒人幫她。高敏幫那名母親輾轉聯系到了武漢同濟大學醫學院,著名器官移植專家陳忠華親自帶隊去天門,幫她完成了捐獻,并將器官用于移植。
后來高敏從報紙上得知,這位女孩的肝臟讓一個小伙子重獲新生,兩個腎臟救了兩名上海少年,眼角膜讓四個深圳眼疾患者重見光明。生命的延續,讓她開始對器官捐獻協調充滿信心。
2007年,國務院頒布《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明確規定,紅十字會依法參與器官捐獻的宣傳等工作,一批器官捐獻協調先行者開展起器官捐獻協調工作。當年,深圳紅十字會設立了全國首個器官捐獻辦。
協調員不是勸捐員
2007年起,高敏每天都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出門都背著幾袋厚厚的材料,其中包括各種器官捐獻的宣傳材料、捐獻登記時所需的各種文件、表單,她說“這是救命的事情”。
而“救命的事情”是這樣的:一名在東莞臺心醫院救治的病人家屬打電話給高敏:可能快不行了,希望捐獻。了解相關信息之后,她連家都沒回,直接帶著材料,奔赴東莞,溝通、協助辦理手續、幫忙處理遺體,一直第二天天亮后從東莞陪送遺體前往深圳,高敏一直在忙碌中。
高敏這樣的工作狀態十分常見。可很多時候,她希望自己清閑點,這意味著面臨死亡的捐獻者少了;但她有時候又更愿意不計付出地去推動捐獻,盡量多地挽救更多人。這也是她在工作中面臨的最艱難的處境:“我們是協調員,而不是勸捐員,不能勸,只能是跟家屬去解釋相關的政策和程序,不能引導他們做決定。而等到他們真正做決定了,我們的心情往往又是最復雜的。”
北京佑安醫院轉OPO專業協調員王璐對此也深有感觸:“其實我最難過的時候,不是別人拒絕我的時候,而是他們說‘愿意的時候。”
因此,高敏特別愿意在完成器官捐獻的時候,跟家屬長期保持聯系,又成為一個心理撫慰角色。常常有捐獻者家屬半夜給高敏發來短信或者打來電話,哭訴對逝去親人的思念。每次,高敏都靜靜地傾聽,平靜地安慰。她最常用來安慰的一句話是:“他(她)其實沒有走,他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