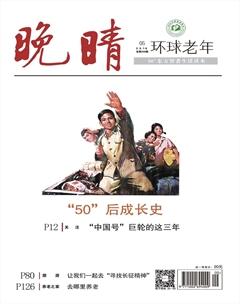分配:生命共享希望
王怡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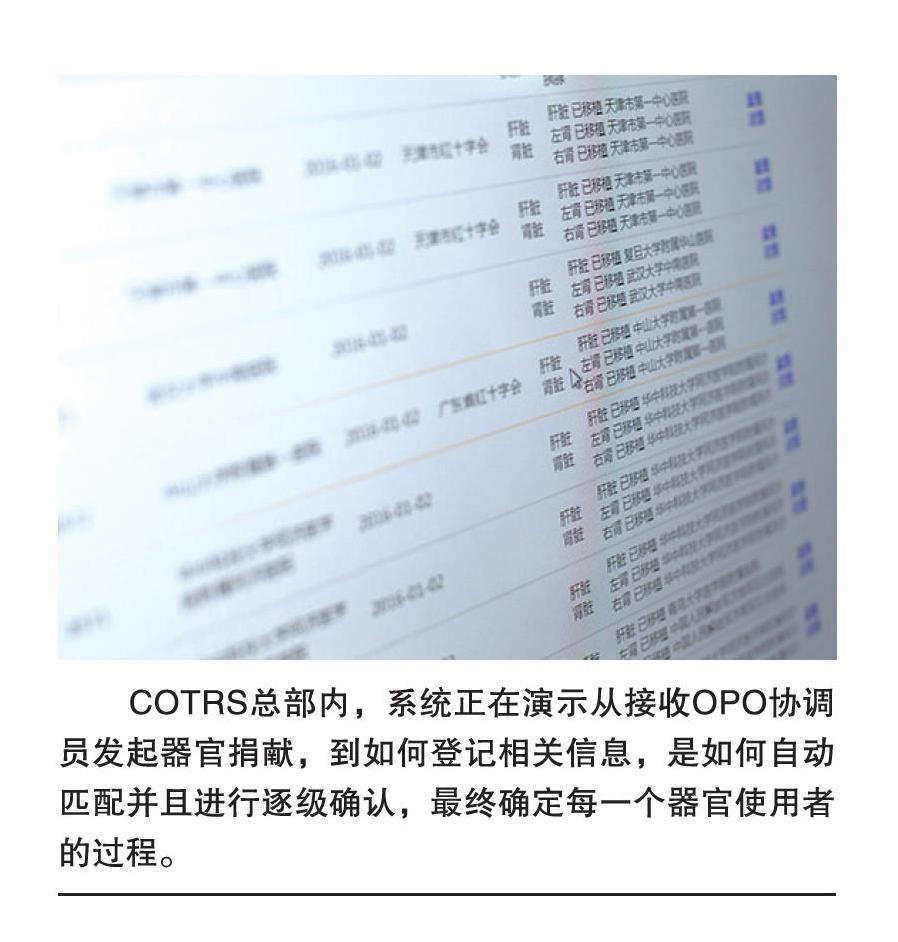
人體器官是稀缺資源,解決好“怎么分配”,是涉及整個捐獻移植體系能否贏得老百姓信任的基石。
人體器官分配是信任基石
器官是稀缺資源,但不是常規意義上的稀缺資源。
2010年,當在香港長期從事器官移植科學注冊系統研究的王海波團隊接受任務,研究器官分配政策時,對于器官捐獻的社會信任度就處在令人堪憂的狀態中。
“器官不是我們制造出來的,也不是生產出來的,是老百姓捐出來的。”王海波說,任何捐獻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怎么用”,器官捐獻中,如果講不清這個問題,那就失去了社會的信任。
王海波認為,實際上,如何保證老百姓對器官捐獻和移植事業的信任,才是一切工作的基石。“只有說明白是如何使用的,才會有人捐獻。器官捐獻的基石實際上并不是醫療技術,而是社會信任。”
在系統全面鋪開之前,有網友曾在網絡上質疑,器官的分配是不是就以兩個標準來衡量:錢和權。
王海波說,要獲得公眾支持來穩定整個信任體系的根基,器官分配的透明和器官的可溯源性就要保證,“要清楚地記錄它怎么來,根據什么原則,去到哪里?如果這些能夠做到公開透明的話,就能確保公眾信任體系的建立。更重要的,是要保證器官這個稀缺資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公開。”王海波說,醫學需要是唯一的排序標準,而不是權力,不是財富。
是政策決定如何分配,不是計算機
2013年8月,國家衛計委出臺《人體捐獻器官獲取與分配管理規定(實行)》,首次明確嚴格使用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COTRS系統)實施器官分配。王海波團隊設計的系統開始成為器官捐獻后分配的唯一通道。
“分配器官就是分配生命。”王海波說,如何搭建完善的分配體系,最根本的是先有清晰的分配政策,這些復雜的政策最終掌握和“分配生命”的大權,其最終目的,是使器官最安全、最高效地匹配給最需要的人。“COTRS系統只是從技術手段上,承載了這些政策。”王海波說,有人會誤認為,現在的分配機制是由計算機決定的,“其實不對,計算機系統只是執行者,負責分配的是政策。”
在綜合評定原則中,排在首位的是病情危重原則。“第一個目標是要降低等待名單的死亡率。”王海波解釋,就是從醫學需要出發,使在等待名單上的人,死亡率降下來,“這樣是最佳的匹配”。
經過一套嚴密的評分系統測算,每一名在COTRS系統里排隊等待移植的患者都會生成一個分數,而一旦發生器官捐獻案例,經過區域優先原則篩選后,這個分數的排序將成為器官分配順序的最重要依據。“如果一個病人不接受移植,死亡的可能性是90%,另外一個病人是10%,當然要先救那個90%的病人。”王海波說。
復雜的政策仍在不斷進化中
COTRS系統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器官分配的各種人為干預的問題,甚至一些倫理難題。例如,器官捐獻者能否指定將器官捐獻給親人?如果在傳統意識中,這應該是可以的。但在嚴密的分配政策中,答案是否定的。
王海波便曾經接觸過一個這樣的案例。2011年起,一名29歲的患者黃某患慢性腎功能衰竭,在上海一家醫院等待腎移植;2013年8月20日,他的父親因交通意外,被送往醫院救治無效,腦死亡,家屬決定捐獻器官。但他的器官只能進入系統分配,而不能指定捐獻對象。后來,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系統破例,允許他捐一個腎臟給兒子,但最終因為血型等醫學原因,這個腎臟沒能用在兒子身上,還是進入系統分配。
“但是分配政策中設計有專門針對器官捐獻者直系親屬的優先原則。”王海波說,黃某因為父親捐獻在排隊系統中獲得了加分,在其父親過世大概一個月后,便通過分配系統獲得右腎,成功進行了腎移植手術。
這只是捐獻器官分配中可能碰到的極端情形的一種,分配政策需要考慮到各種復雜的情況。“排隊最簡單原則就是四個字:先到先得。但是,全國世界器官分配的政策都是從等待時間開始,很快演化為紛繁復雜的分配政策,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要避免人為干預,盡可能保持公正公平。”王海波說。
為了保證能應對各種情況,這套本已十分復雜的系統,仍在不斷地完善進化中。但是,政策的改變要通過一個公平公正的過程,不能是某個人說的算,而是專家委員會定下來,然后還要評估政策改變會有什么影響,這是一個復雜的業務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