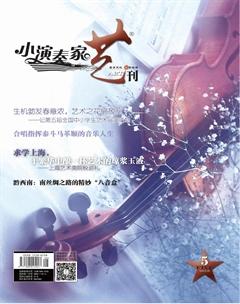我與音樂的故事
我的專業之一是音韻,因此常常有人誤以為我也懂音樂,這實在是一個美麗的誤會,因為我確實曾經希望自己懂得音樂。音韻學界的一些前輩我的師爺羅常培先生、師叔張清常先生就都懂音樂,當年西南聯大的校歌就是張清常先生譜的曲。此外,學界前輩、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幾乎就是一個作曲家,至今仍常聽到有音樂會上演奏他作的《海韻》《教我如何不想她》等曲子。懂音樂對于研究音韻應該是有好處的,但是,很遺憾,我的音韻研究跟音樂沒有絲毫關系。
小時候,我有跟音樂擦肩而過的經歷。畫家筆下常見牧童短笛之類的情景,但是我的家鄉是不允許放牛的兒童騎到牛背上去的,理由是牛耕地已經很辛苦了。可能與此有關,我住的村子里沒有一個小伙伴是會吹笛子的,而跟音樂最接近的人是我的鄰居“德國人”。“德國人”喜歡剝了蟒蛇皮蒙胡琴,他家徒四壁的墻上總是掛著好幾把胡琴,他喜歡躺在他那稻草為褥的床上,翹著腳拉他的胡琴。不知道是因為“德國人”的琴聲不夠悠揚悅耳,還是因為“德國人”五保戶的身份無法贏得我們的尊敬沒有一個小孩愿意拜他為師,學習拉琴,我自然也不例外。現在認識到當年若是跟他學會拉琴將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已經追悔莫及:我長大了,做了遠游的異鄉人,而“德國人”也已經于十多年前去世了。
上小學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迷戀文藝表演,最輝煌的舞臺經驗是參加全公社的小學生文藝匯演,演唱《紅星照我去戰斗》。記得有一次學校老師給我們編排了一出歌頌當時一個村干部的戲,我是主角,依稀記得有說有唱的。第一次在村祠堂演出時,我剛唱了一句,我父親就一個箭步沖上臺來,揪著我的耳朵,一把把我拉了下來,一直拉到家里。因為當時我父親對那村干部的一些做法很有意見,大約他以為所謂文藝表演就是歌頌他所不喜歡的人,從此,父親嚴禁我參加一切文藝演出。學校老師自然也不好再找我,我呢,也很是郁悶了一段時間。假如我父親不禁止我參加學校的文藝活動,我的性格恐怕要比現在活潑許多,很可能還會學點音樂。
上了初中開始有音樂課,所謂音樂課,也就是老師彈著腳踏風琴教我們唱歌。那位愛打扮的音樂老師因為外貌和舉止的某種相似,被同學們取了個“白桃花”的綽號。“白桃花”是當時一部朝鮮反特電影《看不見的戰線》里的女特務。可能是革命的浩然正氣加上青春期故作排斥女性的矯情起了作用,我那時候不喜歡“白桃花”,自然也不喜歡“白桃花”的音樂課。每次上課,我都在腳踏風琴聲和別的同學的歌聲掩護下做小動作、開小差,到了考試的時候,就亂吼一氣。反正“白桃花”老師總是會給我們及格的。班里有兩位男同學,是“白桃花”的得意門生,同時也是我們大家嘲笑的對象,他們的成績都在90分以上。當時因為完全沒有學到“白桃花”講授的音樂知識,并不覺得那兩位同學唱得比我們好,只覺得他們唱歌的嗓門比我們都大,他們唱的《滿懷深情望北京》的余音至今猶在我耳邊縈繞。現在唱歌跑調,遭人取笑的時候,我就會后悔當初沒有好好聽“白桃花”的音樂課。
大學沒有音樂課,但是一入大學聽過幾位音樂家的演講,我就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立志要學習音樂,把中小學的缺憾彌補回來。可是,那時候文學和學術幾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時間,學習音樂的計劃只好擱淺,所學到的東西便零碎而不系統。不過,今天回想起來,吉光片羽倒也覺得很幸福。當時,下鋪的趙同學有一個錄音機,常放臺灣校園歌曲:“我從山中來,帶著蘭花草。種在小園中,希望花開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時過……”《蘭花草》是聽得最多的一首。一位廣受同學們愛戴的古漢語老師花一千多元錢買了一臺當時十分稀罕的“夏普”牌雙卡錄音機,給我們掃交響樂之盲,我們多次在教室里懷著無比虔誠的心情聆聽貝多芬、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貝多芬交響樂中,命運的敲門聲深深地震撼了我。讀研時,室友阿貴是古典音樂發燒友,沒有什么名曲、歌劇是他不了解的,從作曲家到演奏演唱家,從旋律到風格到背后的故事,他都可以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他的一個單卡錄音機,讓我的耳朵也領略到勃拉姆斯、肖邦、德沃夏克……我還曾買了介紹西洋歌劇的書,不過現在只能記得“不要學那穿花的蝴蝶,只知道成天地飛來飛去”之類的句子了。
開始工作之后,人就被安放到了一種軌道上,變得功利寡趣起來,音樂則被進一步疏遠。八十年代末期,交誼舞在高校里蔚然成風,許多歌曲都如倩女幽魂,借了舞曲這個肉身還陽,親近了我的耳朵。
近些年,量販式KTV復活了卡拉OK,我也跟著大家學了一些流行歌曲,偶爾也聚眾、從眾地去“錢柜”、“麥樂迪”之類的地方擊甕叩缶地吼一吼,數年一覺京城夢,贏得歌樓跑調名。
不懂音樂是我很是遺憾的一件事情,因此,有時候也不免冒出一點雄心壯志,試圖效法孔子的“假年學《易》”,來學一學“豆芽菜”,學一學吹拉彈唱以彌補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