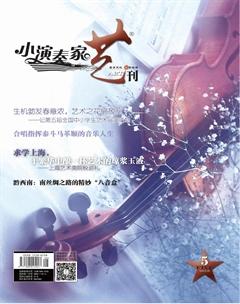舞蹈之外的生活
在16歲認識二高(何其沃)以前,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場現代舞的演出,對于舞蹈唯一的認識不過是學校里那幾個跳街舞的小年輕。而對于獨立文化、獨立創作的認識也只是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時期,在Live house里的一些記憶。那時的我戴著夸張的墨鏡,穿著浮夸的衣服,在地下搖滾的演出現場,與其他和我一樣的窮酸小子們瘋狂推搡,第二天又會很正常地坐在中學的教室里補作業。我不泡夜場、不聽流行歌、不看綜藝節目,生活中最大的樂趣應該就是認識奇怪的人了。
于是,我認識了跳現代舞的二高,他喜歡我叫他二高。我強烈的好奇心和他極大的包容心使我有機會直面他和其他舞者們臺前幕后的生活,相機成為我記錄這些畫面的最直觀的方式。
我們住得很近,幾乎可以算是鄰居,于是見面拍攝的機會很多。我也開始接觸他身邊各種各樣的朋友和舞伴,了解不同藝術工作者的生活狀態,可以說差不多和舞者們生活在了一起。
很快,我接觸了諸如“環境舞蹈”、“在地創作”等詞匯,聽上去都非常的先鋒和前衛,而且很時尚,但如同大多數人一樣,我根本不明白這些到底是什么。我最初的感覺是舞者們在臺上的行為和他們自己本來的生活是割裂開的,不過我一直相信,他們能出現在舞臺上,這個表象的后面一定有著諸多復雜的“化學反應”,也肯定和他們的成長息息相關。
暑假這段時間,我幾乎天天跟拍二高與他的團隊,排練、試衣服、演出、開座談會、買菜、煮飯都事無巨細地拍攝。這種反復的生活讓我產生了審美疲勞,我很難被肢體舞動的美妙所打動,不斷重復的音樂也不再讓我興奮。而美之外、舞蹈之外舞者的個性更能吸引我,舞者們習慣了我的相機后,對我的警惕慢慢放松了,于是鏡頭靠得更近,飽滿笑容之外的其他表情越來越豐富。
前幾個月,我拍攝了他們做商演的過程,直到開演的那天,我索性變成了工作人員,替他們拿衣服,心里想的是舞臺邊緣的釘子會不會傷到他們的腳、觀眾會不會喜歡他們的表演等等。那個時候,我才覺得拋除給舞者帶來收入維持生活外,商演其實是一件挺殘忍的工作,臺下的人們為你優雅的舞姿驚呼,卻不關心你的個性。一個住在廣州的美國紀錄片導演曾跟我說,當你熱愛做的事情變成一種賴以生存的職業時,它或許就會變得索然無味。
毫無疑問,我更愛他們的環境舞蹈,比如在日本的地鐵站跳12個小時的舞、在韓國冬天的河里跳舞,或在云南的露天菜市場里拍打一塊豬肉、在陽江的美術館里被觀眾滿場追著跳舞,這些我都覺得十分有趣,下一秒是不可預測的,身體是靈動的,心是真誠敞開的。
暑假結束后,大家重新投入到高考前昏天暗地的校園生活,我拍攝的時間也不再那么充裕。沒多久,傳來二高住院動手術的消息。在生病期間,二高仍鼓勵我去拍攝他。學校秋游那天,我請假沒去,而是去醫院探望和拍攝二高,到醫院看到他忍著病痛跟探望他的朋友有說有笑時,我想起他曾說的“人只有在痛苦的時候才能感受到自己身體的意識”,他的樂觀使我充滿了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