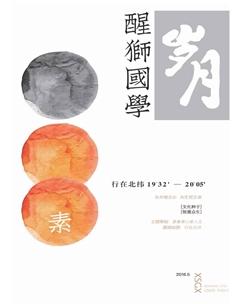素食素心素人生
說辭解詞
素食二字在我國的文字歷史中由來已久,它們結合在一起,組成的詞匯共同構建了一個中國傳統的飲食文化體系。
字以詞的身份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經歷了上千年的風雨之后,那些到如今還能被人們使用的字身上賦予的含義多多少少地都會發生一些變化。
這些變化是很奇妙的,有的詞義范圍會擴大,有的詞義范圍會縮小。不僅如此,有些詞在詞義發展變遷的過程中其本來的意義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得不再常用,但是它們的特點因為可以用來比擬其他的事物而被繼續流傳,這時候這個字本身的含義就變了。
“素”的詞意經歷了一個長久的遷移變化。
大體上看來,除卻作為姓氏的用法,幾乎可以將它的詞義變化劃分為從名詞漸漸發展為形容詞。最早的時候,素是一個名詞,它的意義是“沒有染色的絲或絲織品”。在《上山采蘼蕪》中有“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這里的“素”指的就是原色的絲織品,后來漸漸的有了“沒有染過的素色”“像素絲一樣質樸”的意義。因為“素色”本就是原絲的顏色,“素”也開始有了“本來”的意思,繼而“素”的意思被人們漸漸地遷移它用,開始有了“平常、平素”“交情、情誼”的意思。
何食·素素
沒有染色的絲叫素絲,那么以蔬菜瓜果為食材的飲食便順理成章地被稱作了“素食”。“民以食為天”是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的名言。作為一種盛世文化的表現方式,花樣繁多的烹調方法與流派莫不見證著中國千年來的繁華與盛況。
無論是古時的三牲祭祀,還是絲竹聲伴地宮廷大宴,有些東西是永遠都上不得席面的。因為,“席”屬于繁盛,蔬菜瓜果即使在菜牌之列也不過是漂亮的陪襯。
因為要用一種“君子皆不忍見聞”的慘烈方式奪走其他生靈生存的機會,千刀萬剮之后還要美其名曰鐘鳴鼎食,“肉食”好像自來就帶著美味、奢侈、放縱甚至淫靡的標簽。
“素食”因為樸素、簡單、仁慈、甘心被認為是一種自身就帶著樸素意蘊的吃物,它從“素”中來,終究又回到“素”中去。
素與災荒
在那些已經被太平世人忘卻的饑荒歲月里,那樣的歲月里野味是不可多得的奢侈品,素是人們不得不選擇的選擇。
歷史中很少詳細記載一場饑荒的全部細節,譬如沒有能力的人會被餓死,有能力的人會選擇起義。起義之后普通百姓的生活究竟會變成什么樣,沒有人詳細記載,我想可能只是江山易主,換個人帶著自己的親戚吃肉,更多人還是在吃菜的。
素的風骨
曾經有古人說:“貪享口腹是為敗”。
因為肉食者們脫離了實踐,都是些躺在功勞簿上尸位素餐的人,真正的高手該是在民間的。這樣的話從古說到今,好像什么人都可以拿來評遑論一番似的。一個論斷聽得多了會讓人覺得酸,像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似的酸”。
有些人說的話像是玩笑,有些人說的話一字一句可見風骨。這樣就變得很有意思,換個人、換一個語氣,甚至換一種光線,都會覺得意味變得不一樣了。
譬如一個大晴天,還是青春年少的你和一個“憤青”的同學站在學校的操場上,吹著風的你們一起吐槽著你們還沒見過的那個所謂的“社會”。
那時候說的話哪怕絲毫不差,都不會有夕陽之下的山村庭院中,拄著藜杖,撫著稀疏的東院籬笆悠然南眺的陶淵明說出來的讓人覺得更有說服力。
就像那些年老師常對我們說的:“為賦新詞強說愁算個啥,有些事兒不自己經歷一回是沒有發言權的。”
這個話說的雖然“素”了點,但是正因為它“素”,不得不承認理兒確實是這個理兒啊。
且看縱橫
從饑不擇食的“沒得選”,到返璞歸真的“棄葷腥”,這一切好像是在沿著陰陽互化的軌跡在運轉。但是“食素”好像又不僅僅是一種對食材偏好的選擇。
現今時代,信息的溝通與來往讓更多擁有同樣觀點與論調的人可以相互溝通與扶助,或許這就是人類對于一種與自身息息相關的事情進行深度思考的過程。
縱觀中國歷史的素食文化,仿佛是跨越了時間,橫貫世界素食論調,仿佛是打通了空間。歷數時代縱橫不難發現,“素食”的內涵就像是詞義一直在變遷的“素”字一樣,一直在被賦予更多的含義。
無論是出于何種原因與角度對生命的尊重、對物種的保護、對身體健康的追求,還是對高潔品格與智慧的緣法,都一樣值得深思;無論是什么樣的論調與思潮,只要是有情的,總是很動人的。
吃著青藜的口,像是安穩吃素一樣的心境,是最讓人覺得安穩的上等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