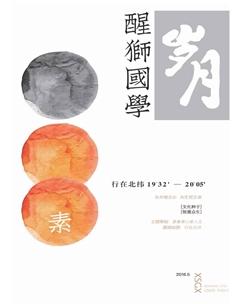《左傳》中的“肉食者”
高政銳
在朝在野
魯莊公十年,齊魯之間爆發了長勺之戰。野人曹劌參與了戰役的指揮,并使魯國最終取得了勝利。這場戰役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是曹劌對魯國貴族的評價,也先入為主地成為了人們認識貴族的一把標尺。
實際上,在風云變幻的春秋時代,受到良好教育并擁有豐富社會閱歷的“肉食者”,不乏雄才大略、志向高遠者。齊桓公、晉文公等國君,管仲、晏嬰及鄭國的子產等賢臣,皆可為代表。但是,貪財好利、目光短淺的“肉食者”亦大有人在。這些人大多愛慕榮利,甚至胡作非為,往往落得身敗名裂乃至國破家亡的下場。
愚者鄙者
崔抒是齊莊公時代的齊國權臣,尚武好色。他到大夫棠公家去吊唁時,看中了棠公之妻的美貌,便想娶之為妻。崔抒同棠公之妻同為姜姓,按照同姓不通婚的禮制,二人是不可以結婚的,何況棠公新喪。
崔抒沒有顧及到這些,并拒絕了陳文子的勸告,娶了棠公之妻。齊莊公也是一個為長不尊的國君,暗自和崔抒新婦相通,并屢次到其家,甚至把崔抒的帽子拿出來送給別人。崔抒勾結了莊公近侍賈舉,找了個機會,殺掉了齊莊公。
這是發生在魯襄公二十五年的事,《論語》通過子張之口,對這件事也有側面記述。齊莊公好色樂淫,因此喪命,是對“肉食者鄙”的再一次生動詮釋。而另一“肉食者”崔抒,愚昧顢頇,為一己之私,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韙,其愚鄙的程度遠遠超過了魯莊公。
肉食奉公
此后的記載,有兩件事令人感動。
其一,齊國太史書“崔抒弒其君”,一個“弒”字對崔抒進行了終極的歷史評價。史載“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兄弟三人前仆后繼,不僅記錄了歷史的本象,維護了史官的尊嚴,更表現了人性的高貴。他們的行為也得到了南史氏的聲援,“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不畏權勢、秉筆直書正是中國史官的不屈精神,也是我們民族得以延續發展的不竭動力。
其二,另一“肉食者”大夫晏嬰,在莊公被戮后,并未畏懼崔抒的兇殘,未逃亡,未躲避,而是伏在莊公的大腿上號哭,并頓足三次而去。連崔抒都承認,晏嬰是“民之望也”,不得不放過他。晏嬰的有禮、有節、有力,為他后面在齊國執政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鄙者于心
“肉食者”是春秋時期的貴族,相對于平民,他們占有巨大的社會資源。在資源有限的古代社會,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吃肉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孟子說,“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肉食者”身居高位,一旦擁有權力,往往忘乎所以,不能自持,做出令人悲嘆之事,這是“肉食者鄙”的一個根本原因。
春秋時期,晉國是一個大國,其國君晉靈公是一個貪財好利而又荒淫無道的家伙。他規定的賦稅很重,民怨沸騰。他還站在高臺上,拿著彈弓打人,看著大家躲避彈丸而哈哈大笑。更為荒唐的是,廚師做熊掌沒有做熟,他居然將其殺掉。正如大夫士季對他的勸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晉靈公最終被趙穿在桃園擊殺。
禮崩樂壞的時代,子弒父者有之,臣弒君者有之。亂臣賊子固然可恨,但被弒者的君父,也要承擔一定責任。“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這是孔子無法忍受的幾種行為,這又是“肉食者”司空見慣的現實表現。由此觀之,“肉食者鄙”的評價可謂是客觀而又理性的。
為天下笑
相對于晉文公的荒唐,迂腐的宋襄公則是另一類“肉食者鄙”的具體表現。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記載了宋楚之戰,宋軍已排好了隊列,楚軍正在渡河,大夫司馬子魚建議立刻攻擊敵方,宋襄公不同意;楚軍渡河未排成隊列時,司馬子魚再次建議發起攻擊,宋襄公還是不同意。
結果宋軍大敗,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傷,親兵全部被殺死。當被責備時,宋襄公以“仁義”自詡,認為行軍打仗,不以險要地方取得勝利是一種“仁義”之舉。“仁義”是不錯的,但它也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仁義的實施,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地點等客觀因素的具備,否則,只能自取其辱。
宋襄公的悲劇在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一廂情愿地躬行仁義,于現實無益,徒為別人的笑柄。
重在離心
目光短淺、貪圖財色、愚蠢顢頇,是“肉食者鄙”的集中體現。
但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問題當然不是這些貴族吃肉的結果。不錘煉自己,以自我為中心,面對外部世界,毫無恐懼之心,即使整日食菜,亦于事無補。
“肉食者”只是一個關聯性極強的借代修辭而已,“肉食者鄙”的教訓,不僅后世“肉食者”需要吸取,“素食者”也需要吸取。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