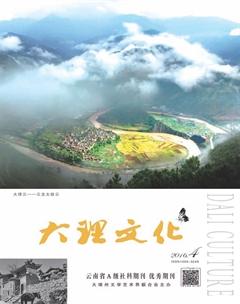鳳羽河畔
河流孕育著生命,孕育著文化,因為河流,民族生生不息。
故鄉的鳳羽河,沒有史詩般的輝煌,沒有絢麗動人的樂章,甚至沒有一個足以讓人流連的轉折,但它自有它的沉靜與堅守,自有它獨特的詩行。河流如血脈,沒有哪一段因渺小而多余,淺淺鳳羽河,因為打上故鄉的烙印,帶著童年的記憶,瞬間便溫暖起來,生動起來,慰藉著思鄉的心。
我是命定與故土相守一生的人,卻也會生出鄉愁,仿佛自己還在回家的路上。漫步鳳羽河畔,溯流到時光深處,而家一直在那里。
關于鳳羽河,最早的記憶是幼時跟在三老(爺爺)的后面,到蛤蟆塘給集體出工的人們送飯。那個年代,大人們都要掙工分,小孩則被隨意放養。三老年輕時讀過黃埔軍校,解放后回到隊里孤人一個,便被派去守打場。我家在打場旁,年已六十歲的好心人三老,便順便帶我,當孫兒一般疼。三四歲的我眼中,鳳羽河寬闊而遼遠,仿佛沒有盡頭。河埂上,一老一小,一擔飯食,一段遠路。正在挖地的大叔大媽從土里刨出幾個灰褐的“土個兒”(樣子像蟋蟀而個頭更大的一種土蟲,我至今沒弄明白是什么),小心翼翼地裝在一個缽頭里再罩上碗,讓我帶回去油炸,算是對我的獎勵。送飯路一來一回,幾乎耗掉一個下午,河堤上有很多樹,陰森森的,我常常要拽著三老的衣襟,生怕自己丟失在那段神秘而漫長的路上。
洱源壩子廣闊的田野是少年的樂園,我常常跟在更大的孩子后面去探險,下河捉魚,上山摘果,甚至還到珍珠澗去洗澡。而更多的歲月卻與橋有關。
出小橋,過東門大石橋,再穿過田野,漫長的“跋涉”只為到九臺村大澡堂洗澡。東門大石橋,是圓形的拱橋,橋的兩邊都給人踩出便道下到河底,就著河水洗洗菜,洗洗衣服。今天,站在霓虹閃爍的大橋上,我真難想象,那時的河為什么特別寬,河底的沙石為什么那么透亮?
青昌大橋則是解放后修的。家在西面山下。田在橋東壩子中央。一座樸素的水泥橋,貫穿了四季,也牽扯出煙火人家,根植于泥土,所有的悲歡也種在土里。那些年月,水利設施匱乏,所有的耕種灌溉都要等鳳羽河水下來,上游的栽插完了才輪到下游,為了水,經常要半夜去閘。雖然是夏天,半夜也是冷的,打著電筒,走三四里才能到田頭,夜風寒涼,青蛙叫累了睡去。看著水汩汩流進田里,仿佛看見了豐收的景象。若干年后一個蠶豆成熟的夜,我在暮春的晚風里走上鳳羽河,繞過南山小橋,繞過福壽橋,走進青昌大橋荒涼的夜色里,坐在兒時常坐的河堤上,洱周路上的夜燈像一粒粒明珠,璀璨了遠處的新城,田壩里混雜著水薄荷小秧苗蠶豆葉的香味清新了靜靜的夜,夜空里一顆顆星子遙遠而親切。潺潺的鳳羽河水,把我帶回勞作的過去。
割豆尖、背豆稈,在打場里揚起的豆糠把整個人染成墨綠色。我家準備的籮筐要比別家的小,捆谷子用的草繩要比別家多,母親不能減少我們的勞作,只能減輕我們的勞動。背著一捆谷子屁顛屁顛地跟在母親身后,她背著兩大捆像一面厚厚的墻,只有兩截小腿艱難地在地上移動,每一步都能在沙地上踩出個深深的腳印。三四里的路,能休息的一站便是青昌大橋邊的四個石墩。可是,來來往往的人那么多,很多時候,只能在河堤邊歇一下,放下背子容易,再站起來就難。往往是我先在后面推母親的背子,母親跪在地上用手拄著地使力地站起。有時,背子太重,單推站不起,還得請旁邊的人拉一把。好在,路上都是鄉親,大家就在你推我拉里把谷子背回家。后來漸漸多了手推車,拖拉機,活路才漸漸輕了些。
星光之下的石墩早已積滿厚厚的灰塵。河東的土地大半已經被征用,那個忙碌奔波的耕種季,那個熱鬧而辛苦的收獲季都淹沒在河堤深深的草叢問。那個背谷子的我,背著籮筐送飯的我,在河堤下打一罐翻砂水的我,踩著沙石洗腳的我遠去了;那個枕著蓑衣躺在田埂上看護篾籮里的弟弟的我,那個在沆泥潭的水溝里撈到許多大貝殼的我,那個在田邊土灶上做鑼鍋飯的我也遠去了。鳳羽河,我童年的河,教會我勤快,教給我艱難,教會我珍惜的河,依舊在風雨里悄然流淌,從不吝嗇。
鳳羽河東與勞作有關,鳳羽河西,與生活相連。外婆家在大埂村,又在村尾,一出門就是鳳羽河支流的一條大溝,算是消水河的上游了,這條溝曾承載過多少茈碧漁船逆流而上,販賣瓜果糧食換取生活必需?而我,幾乎有十五年的時光都在這溝邊度過,跟在表姐后面一起洗衣,洗菜,甚至渡到溝里玩水,更多的是每天都要跟著外婆或是小姨去鳳羽河邊的井里挑水,來來回回幾趟,挑滿一大缸也僅僅夠一大家子一天用。外婆總會把桶里桶外洗得干干凈凈,一塵不染,還會在初一十五到井邊點香,感謝水井龍王的饋贈。那是一條鄉間最普通的田埂小路,那是鳳羽河眾多翻砂井里普通的一眼,但是,這路這井卻養活了一代代人,直到自來水取代了水井,礦泉水代替了山泉水。廢棄的井像一只幽深的眼,終于失去了往日的光澤和清澈,被荒草掩蓋。
走過童年少年的青昌大橋,走到青年的南山小橋。鳳羽河邊讀書三年教書十三年。我人生中最燦爛的季節都寫在了這里。黃昏,大家走出校園,到河邊讀書,一條寂靜的河便在夕陽的余暉里沸騰起來,放牛的老爹悠然地抽一竿旱煙。牛兒自在地啃著細草,綠油油的田野在風里掠過一道道波浪,那是一幅美麗的畫卷,和諧恬靜。再后來,和很多老師飯后散步,大家一路熱烈地討論,交流,迎著晚風,是另一條文化之河。現在,這一段讀書走廊是徹底沉寂了,即使沒有封閉式管理,學子們也更愿意把所剩無多的時間割讓給手機。雖然老師們還可以去河邊散步,但大家更習慣于回到霓虹深處的家,集體的時代已經終結,集體出工的時代也屬于歷史。
逆流而上,上村水庫樹影依依,上村濕地雖不及茈碧湖的規模,但風車草美人蕉蘆葦叢與水相攜,確實增色不少。走在濕地的蔭涼道上,我懷念起清源洞,懷念起白石江,也懷念起鳳羽壩子來。
農歷六月十三,清源洞會,那一年,我們一家心血來潮,要去赴會。因為不識路,在鳳河村下了車,沿著天馬山腳一路向南。山路的辛苦自不必說,走到一個山坳處,聽聞一陣巨大的水聲,走近,竟然是一道湍急的溪流從山里直瀉而出。大家倒掉帶著的水,幾乎要跳到溪流里,水出奇地甘甜冷冽,水杯上都冒著冷氣。都說鳳羽水好,總算是眼見了。遇到村中一個老爹,說起有這樣好的水真享福,他只淡淡一笑。而真到清源洞,水卻安靜如玉帶,四周幽深,未進洞而冷氣撲面,鳳羽河的靈秀該是源自于此的。清源洞系蒼山北麓,是鳳羽河之源,也就是洱海之源。這樣看,蒼山十八溪是洱海的山水之源,清源洞則是把蒼山臟腑里的水繞了一個大灣又送回它的面前,地面之上河流星羅棋布,地表深處,則又是一脈相連的。
鳳羽河滋養了兩岸的白子白女。羅坪山的渾厚又提攜著壩子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如果說鳳羽河是洱源的母親河,羅坪山則是洱源的父親山了。白石江水清清涼涼地流淌,羅坪山深處的溪流瀑布帶著山的精靈傳遞著大地的生命,也造就了白族兒女的勤勞質樸與深深的文化底蘊。
早春三月,聽說上寺村有個荒廢的山村大澗。便急匆匆趕去看,大澗依著羅坪山,雖是旱季,但山澗里溪水潺潺,別有一番意趣,據說,沿著山路,能翻越羅坪山去到煉鐵。而大澗朝南,就是蒼山西北麓,遠望過去,層巒聳翠,高拔而深遠,谷底寬闊,沙石碩大,可見,雨季時這里有何等的水勢。向北張望,鳳羽壩子美如錦緞,透過上龍門的隘口,可以看到洱源壩子的一角了。山水相連,從不曾疏離。大澗水順流而東匯入鳳羽河,蒼山水羅坪雪,共同滋養著這清淺悠長的河流,也把大理山水的情懷沿路播撒。
黃昏時分,我像往常一樣,漫步鳳羽河的文化走廊上,從消水河繞道鵝墩橋,再回到溫泉小區邊的涼亭,兒時漫長崎嶇的路現在卻只感覺安謐閑適。河堤上的青石路在傍晚的霞光里泛出暖暖的光,早春的櫻花已經凋謝,新葉濃綠了枝頭,河中的風車草美人蕉在水的滋潤里旺盛地長著,三三兩兩的人踱著悠閑的步子享受愜意的時光。再過兩年,整個鳳羽河生態工程完工后,這古樸的青石路便徑直延伸到茈碧湖,鳳羽河也將成為一條花草的香徑了。我坐在小亭子里,忽然想起關于河流的種種碎片……
生命之河,生生不息。清清鳳羽河,帶著它的故事,奔流向前。
編輯手記:
作為國內“新散文”的運動踐行者之一,石岸以其個性敏銳的感覺和體悟,使其作品流動著深沉蒼茫的生命意識,充滿著對時光、人生的思考與回味,交融著對美好與滄桑生活的矛盾與平衡。《在時光中打撈》顯示了作者與眾不同的敘事風格,文字在世俗與超越中自由游走,憂郁理性的思考,展現了一個真誠、熾熱、理性的個體,舒緩自由的內在節奏,傷感中透著對善良美好的追求,整體發散著憂思而又優美的情懷。張旗的《苦楝子》把記錄祖母生平、哀思祖母的情懷寄寓在小小的苦楝子上,文章寫得很有功底,平靜、自然的筆調,對生活的經歷不褒揚,不貶斥,以情動人,顯出厚實與深度。李智紅的《神樹》語言老道沉穩、極具語境,充滿著對那棵古老的黃連樹的敬畏感,一種原始、古老的信仰縈繞其間,精煉短小的文字卻讓讀者為這樣樸素、純粹的情懷感動。徐汝義的《鳳羽河畔》寫得柔美、安然,文字內斂、天然,讓人充滿想象,可謂筆到情到,溫暖樸實間讓人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