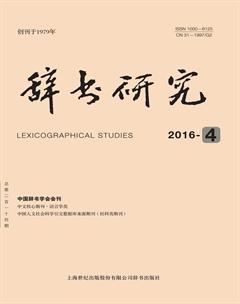語料庫驅動詞典學、語料庫詞典學與語料庫輔助詞典學
撰薛梅
摘要近年來,隨著語料庫在各項語言研究及詞典編纂實踐中的廣泛運用,出現了“語料庫驅動詞典學”或者“基于語料庫的詞典學”的說法。文章論述了語料庫與詞典編纂的辯證關系,討論了語料庫在注釋專科術語詞條時的局限性,認為“語料庫輔助詞典學”的說法較為準確地描述了語料庫與詞典學的關系。
關鍵詞語料庫詞典編纂術語注釋
一、 前言
半個世紀之前,第一個電子語料庫付諸使用,語言學界與詞典學界的爭論也隨之而來。有的學者很快接受了這種便利的新資源,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這種新資源持懷疑態度。Lees(1962: 100)認為語料庫分析“純粹是浪費時間、耗費政府錢財”,而Itkonen(1976: 65)也稱此為“多此一舉”。Lees(1962: 110)稱: “英語本族語者在十分鐘之內說出的語法點要比幾百萬字的隨機文本多得多。”
許多早期從事語料庫理論和實踐研究的學者,例如Francis(1979)反駁了Lees和Itkonen的保守觀點。時至今日,語料庫已經廣泛地用于各類語言學研究和詞典編纂。詞典學家們能夠從大型語料庫中更迅速、便捷地獲取和挑選數據。與之前的方法相比,語料庫提高了詞典學家們的工作效率,也有助于提高詞典的質量。這和Lees在半個世紀前對語料庫的看法截然不同。許多學者,例如Sinclair(1987),Atkins & Rundell(2008: 45—96),Hanks(2012a,b)和Bergenholtz & Agerbo(2014)都展示了如何利用語料庫編纂詞典。他們所提出的利用語料庫編纂詞典的許多方法都受到了批評。這些批評對于一個不斷發展的學科來說很正常,更無法否認語料庫對詞典學研究和實踐的價值。
不過,所謂的“詞典學界掀起了語料庫革命”(Hanks 2012a)的說法有些言過其實,甚至會阻礙某些詞典編纂活動。Lees和Itkonen的說法盡管武斷,但至少就專科詞典學而言還是有幾分道理的。在專科詞典學領域,需要考慮利用語料庫編纂專科詞典的局限性,而不是直接否認語料庫的作用。隨著新科技或者新范式的出現和發展,許多研究者經常會否定之前的研究方法,即使他們曾從中獲益良多。他們往往會盲目相信新科技的神奇和便利,無法即時預見新范式的局限性。往往經過一段時期之后,大家才意識到這些局限性,而此時這些新范式已經根深蒂固。
二、 語料庫與詞典學
運用新科技建構語料庫并從中獲取數據編纂詞典時,大量的新術語由此而生。要充分描述新的社會現實,這些新術語絕對必要。然而,有些術語卻問題蔓生,根本無法如實描述學科研究現狀。或許在引進這些新詞之前學者并未認真探索其真實含義,例如“語料庫詞典學”“語料庫驅動詞典學”和“基于語料庫的詞典學”等詞語。
詞典學實踐所涉及的遠不止是實證基礎(Tarp 2014a)。從這一角度而言,語料庫并不是詞典學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是完成詞典編纂過程中的某一任務的方法之一。因此,Bergenholtz(1996)指出,不論語料庫在詞典編纂過程中完成的任務多么重要,用“語料庫詞典學”一詞描述整個詞典編纂方式是不恰當的,因為語料庫不過是用于編纂詞典的若干實證資料的一種而已。例如,我們編纂詞典時也會用到檔案、問卷、日志文件,但是沒有“檔案詞典學”“問卷詞典學”“日志文件詞典學”之類的說法。
Krishnamurty(2008)指出,“語料庫驅動詞典學”的說法可以追溯到John Sinclair。“語料庫驅動的方法自上而下,先從語料庫中挑出未編輯的實例,確認這些例子的共同特點和各自特點,然后按照詞典的編纂目的將它們分類、組合。”(Krishnamurty 2008: 231)這段引文中的觀點極有參考價值和科學性。然而,“驅動”一詞使用不夠恰當,因為語料庫是一個被動的實體,無法驅動或者決定詞典中應該包括什么。例如,描寫性詞典、規定性詞典、建議性詞典(指的是遵循建議原則而編纂的詞典,參見Tarp & Gouws 2008)挑選數據和呈現信息的方法就各不相同。
語料庫為詞典編纂提供語言證據,但是詞典編纂也講求系統原則。例如,用以挑選《馬達加斯加語—德語詞典》(Bergenholtz et al. 1991)詞目的語料庫中,詞語talàta(星期二)出現的次數極少,未達到詞典收錄的詞頻標準,但是出于系統性原則考慮,該詞必須和其他表示星期的詞語一起收入詞典。因此,“語料庫驅動”的說法低估了詞典學家在詞典編纂過程中的積極角色。“基于語料庫的詞典學”的說法也有問題。現代化的數字詞典的編纂在許多環節中需要語料庫輔助完成,但是也有許多環節和語料庫毫無關系。顯然,“基于語料庫的詞典學”的說法過于籠統,有待商榷。
電子語料庫對于挑選或者佐證諸如詞目、等價詞、搭配、成語、慣用法等的實例、釋義或者特點之類的詞典編纂活動非常有用,但是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以上所討論的三個術語反映了當前詞典學研究中表述混亂的現狀。但這些術語已深植于詞典學界觀念之中,不太可能廢棄。盡管如此,本文建議使用更為精準的術語確切地描述詞典編纂與語料庫之間的關系。例如,“語料庫輔助挑選”和“語料庫輔助佐證”的說法要好于“基于語料庫的挑選”或者“基于語料庫的佐證”,因為除了語料庫以外,詞典詞目的挑選和佐證也來自其他實證基礎。
三、 學科專家與專科詞典的編纂
專科詞典的編纂傳統悠久而豐富,但許多普通詞典學的研究者常常忽略這一點。Hoare(2009)指出,英國皇家圖書館里的大部分詞典都是專科詞典。其他研究的調查結果也是如此,例如,Leroyer(2011)對2008—2009年的網絡版詞典標題的調查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結論。迄今為止,已經編纂的專科詞典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學科和人類的文化活動,正如Tarp(2014b: 214)所言: “詞典尤其反映了過去四千年的社會、歷史文化變遷,無論是從語言發展的角度,還是從手工業、經濟生活、文化、教育、自然社會科學、人文、體育,甚至諸如消遣、娛樂、節假日之類的種種奇異現象的角度。”
這些詞典學研究和實踐都證明詞典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且具備跨學科的特點,強調學科之間的相互合作(FuertesOlivera & Tarp 2014)。上述的許多專科詞典都是由各個領域的專家獨立完成或者聯合完成的。例如,西班牙前財政部長José Canga Argüelles在1826年和1834年出版了兩部專科詞典。第一部詞典的序言題為“供高級公務員使用的財政詞典”。在序言中,該書的作者寫道:“這部詞典可以看作是財政學的小型書庫……一開始編輯這部詞典,我的目標是歸納財政學的知識,為財政部的高級公務員提供信息。”(Canga Argüelles 1826: vii)
這部被作者稱為“財政學書庫”的詞典依照傳統由專家編纂。這一傳統在歐洲始于啟蒙時期(Tarp & Bothma 2013)。18世紀的詞典學家區分了語詞類詞典、事物類詞典和事實詞典(DAlembert 1754: 958)。但是,有些作者,例如英國著名的詞典學家Samuel Johnson不認可這種分類(Tarp 2015: 183)。在《科技詞匯》(也叫《人文與科學英語通用詞典》)一書的序言中,Harris(1704)解釋道: “我的目標是編纂一部不僅是詞而且是事物的詞典。讀者不僅能查閱到有關科技詞匯或者人文科學中用到的藝術術語的闡釋,也能查閱到人文科學知識,這一部分知識對整個人類來說最有用、最有益處。”
Malachy Postlethwayt于1749年出版了著名的《商貿通用詞典》。他解釋說,要通過發展貿易和航運來推動大英帝國的崛起,但是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員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他們沒有時間閱讀相關的書籍,更沒有錢購買此類書籍。
“國內外貿易涉及的事務千變萬化。那些經驗豐富、技術嫻熟人士傳播的知識散落于萬卷書冊,要從中查詢所需信息遠非易事”,因此“按照字母順序將這些具備廣博內涵的知識編纂成一部詞典來滿足人們查詢信息的需求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Postlethwayt 1749: 2)
如上所述,以此為目的,歐洲自啟蒙時代以來出版了大量的專科詞典。這些詞典的作者和合著者大多是各個學科領域的專家、前衛的研究者,有些甚至是諾貝爾獎獲得者(Besomi 2011: 16)。例如,三位經濟史學家Astigarraga, Zabalza & Almodovar(2001: 29)分析了Iberian Peninsula出版社在18至20世紀期間出版的政經方面的詞典和百科全書之后,認為Canga Argüelles在1826年和1834年編纂的兩部財政學詞典毫無疑問是“19世紀前半期西班牙經濟學家所編纂的最有價值的經濟學類詞典”。最近由專家編纂的專科詞典有《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和《牛津經濟學詞典》,也都聲望很高。
即使有專家編纂專科詞典的傳統,有些詞典學家和術語學家還是瞧不起,甚至是否認學科專家編纂的詞典。例如,Frawley(1988)建議專家們不要編纂詞典,只需為專科詞典提供信息即可。他認為詞典編纂是“詞典學家和語言學家的范疇,因為他們知道如何使用詞匯、表述詞匯的含義”(Frawley 1988: 196)。術語學家Riggs(1989: 90)對此持相同意見,認為那些“只懂專業的專家既不是詞典學家也不是術語學家”,他們即使努力學會了“詞典的格式,也不知道如何正確地編纂詞典”。最近,León Araúz, Faber Pamela & Montero Martínez(2012: 95)也提出了類似看法: “術語的釋義經常由各領域的專家解決……然而,將釋義等同于專業背景,并將其視作專業人士的專權,也會令人質疑詞典和資源的質量……顯然,了解專業知識和如何解釋、描述專業術語是兩碼事。工程師或者科學家可能是各自領域的專業人士,但是他們很少能用一般語言講述專業知識。”
這三位學者認為無須專業人士的參與,術語學家就可以完成專科詞典中詞條的釋義工作。他們建議使用“框架式術語”,強調“概念結構”和“各類專科知識的多樣性”,以及“運用多語語料庫提取語義、句法信息”。(Len, Faber & Mart′nez 2012: 97)在詞典編纂過程中,如果術語學家或者詞典學家有所疑慮,則可以咨詢學科專業人士。
本文不討論“框架式術語”,也不討論用這種方法得到的復雜釋義是否有用。本文認為以質疑專家撰寫釋義的能力為由排斥專家參與詞典編纂的做法不可取。即使有的專家不具備撰寫術語釋義的能力,訓練專業人士撰寫專業術語的釋義要比訓練一個外行(無論他們是詞典學家或者術語學家)容易得多。另外,就時間而言,專業人士比詞典學家和術語學家的工作效率更高,這一點稍后討論。
四、 語料庫在提供專科詞典詞條釋義方面的局限性
專家和外行在判斷專科詞典和外部資源中的釋義的時候所持的方法和標準不同。以deemed cost為例,《會計詞典》將術語deemed cost定義為:
Deemed cost is an amount used instead of cost or depreciated cost at a specific date. Any following amortisation or depreciation is made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nterprise initially recognised the asset or liability at a cost equal to the deemed cost.
Kilgarriff(2012)在評介FuertesOlivera & Bergenholtz的合著時曾經質疑這個釋義。他建議使用谷歌搜索語料庫獲取如下釋義:
“Deemed cost” is a surrogate for cost at a given date. For example if a building is purchased at $100000 this is cost and also the deemed cost at that given date...
Kilgarrif(2012: 27)對搜索到的釋義非常滿意,評論道: “如上所示,用谷歌搜索很容易獲取百科全書式的詞條。詞典學家還能做什么呢?”
當然,不是會計行業的專家可能很難看出上述兩種定義有何不同,也很難判斷哪個定義在具體的詞典中更好用。Kilgarrif似乎也有此疑惑。通過谷歌搜索獲取的釋義在特定的語境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并不適用于詞典學家和會計專家聯合編纂的會計詞典。Kilgarriff用谷歌搜索獲取的釋義太過寬泛,其含義超過了《會計詞典》的《國際財務報告標準》(IFRS)要求。
Kilgarriff(2012: 29)說: “我們需要利用語料庫獲取事實求證。”下文我們列舉三位經濟學家的意見。其中兩位經濟學家是著名的《牛津經濟學詞典》的作者。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三位經濟學家Hashimzade, Myles & Myles(2014)談論了網絡釋義的優劣和相關性。下面是搜索到的對corner solution的釋義:
A corner solution is a special solution to an agents maximization problem in which the quantity of one of the arguments in the maximized function is zero. The more usual solution will lie in the nonzero interior at the point of tangency betwee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the constraint...
這三位經濟學家認為在網絡上獲得的corner solution的釋義和第二版《牛津經濟學詞典》中的釋義相似:
A solution to a system of equations where some variables are zero...
但是,Hashimzade, Myles & Myles(2014: 19)認為這兩個定義都不是corner solution的一般定義,“這兩個關于corner solution的釋義都不正確。在適當的語境下,這兩個釋義或許正確。語境缺失的話,釋義就不正確了,還有誤導性”。
三位經濟學家給出了以下釋義,應用在《牛津經濟學詞典》第三版和第四版中。
corner solutionIn the context of a constrained optimization problem this is a solution that does not change in at least one direction in response to any arbitrarily small perturbation to the gradient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t the optimum.
Hashimzade, Myles & Myles(2014)其實對上述釋義也不太滿意,但是認為這條釋義從經濟學理論的角度來說優于上面討論的其他兩個釋義。很明顯,只有該領域(會計學)的專家可以根據目標用戶的需求特點決定這類釋義正確與否,充分與否。那種“使用語料庫獲取事實”的方法根本無法通用,特別是在專科詞典學中。
五、 語料庫與普通詞典中術語的釋義問題
不僅專科詞典會涉及術語的釋義問題,普通詞典也會有此類問題。例如Bergenholtz & Kaufmann(1997)分析了收錄在不同的德文和英文普通詞典中的許多和分子生物學相關的術語的釋義,包括一些平時常用的術語,如gene, chromosome, enzyme, bacteriophage等等。著名的英語學習詞典《牛津高階英語詞典》和《柯林斯COBUILD高級英語詞典》中包含了普通語言中用到的主要的法律術語。這兩部詞典公開聲稱運用了權威的語料庫,例如英國國家語料庫,牛津英語語料庫和英語語料庫。但是,如Nielsen(2013: 151)所言: “兩部詞典都未包含英國法律1999年新引入的民法程序術語,例如claim form取代了writ of summons,statement of case取代了pleading。這兩部詞典收錄的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取代的術語。”
英國民法1999年以claimant取代了plaintiff。如果目前(2015年6月)查閱在線的《牛津英語詞典》,會發現詞典里收錄了claimant和plaintiff,并附加說明這兩個詞的釋義取自《牛津高階英語詞典》。但是,這兩個詞條列舉的普通釋義義項(見截自屏幕的圖1與圖2)都不包含法律意義。詞典的這一做法暗示用戶可以繼續使用法律界在20世紀末就已擯棄的法律術語。
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語料庫的文本過于陳舊,普通語言中可能仍然在使用那些過時的、廢棄的法律術語,新的術語要一點點地融入普通語言。詞典收錄“陳舊”的術語對文本閱讀仍有用。但是,如果詞典要幫助文本輸出,則需添加信息說明這個法律術語已被摒棄,并提供參見新的術語,即使這些新的術語在語料庫中并未達到被選錄的詞頻標準。
根本上而言,這是由于詞典編纂者不了解1999年的“新民法”(雖然網絡上可以獲得相關信息)造成的。這個問題普遍存在于許多普通詞典中。對于此類問題一般有兩種解決方法,但都不完美。詞典學家在編纂《丹麥語網絡詞典》時使用了第一種方法。該詞典的大部分編纂人員并不是語言學家,而是各個專業(例如數學、物理、化學、分子生物學、法律和經濟學)的學生(Bergenholtz 2013: 5)。經過一段時期的詞典學訓練(主要是從語料庫中挑選詞義,撰寫釋義)后,學生們一般可以撰寫和本學科領域相關的術語的釋義,也包括在普通語言中使用的專業詞匯的釋義。他們所撰寫的釋義質量也很高。但是,這些經過訓練的學生在撰寫其他領域的術語釋義時,依然困難重重。
釋義撰寫有困難,也可采納第二種方法——咨詢專家。但是,這種做法也有很多問題。因為很難找到理解問題現狀,并能用普通語言簡潔解釋術語的專家。在編纂《丹麥語網絡詞典》時也遇到過這類問題(Bergenholtz 2013: 5)。如果找不到專業人士參與詞典編撰,那些錯誤的、有誤導性的釋義就會在普通詞典中長期存在。普通詞典既然收錄了這些術語,就應該盡力提供專業含義。語料庫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所以人的因素就至關重要了。
六、 專家參與編纂詞典
下文討論奧胡斯大學詞典學研究中心在編纂專科詞典和普通詞典時是如何選條和撰寫術語釋義的。例如,在編纂《音樂詞典》時,除了一般概念的闡釋,音樂家Inger Bergenholtz承擔了所有的工作,包括挑選術語詞條、撰寫釋義、改編釋義使其適合音樂學院的學生和對音樂感興趣的外行理解。詞典選條時,作者并未依賴語料庫,而是如Bergenholtz & Tarp(1995: 93)所薦,參照了音樂教材和音樂手冊上的目錄。該詞典的理念是幫助用戶閱讀文本和拓展知識,因此詞條內提供了長短兩類釋義。簡短的釋義是可視的,用戶閱讀文本時只需參照簡短的釋義。詳細的釋義則以折疊的方式隱藏,供那些想了解更多知識的用戶使用。圖3展示的是詞條cello完全展開的內容。
另一個例子是奧胡斯大學詞典研究中心編纂的《基因工程百科詞典》。這部紙質詞典是丹麥、古巴的詞典學家和專家共同合作的成果。該詞典為多功能性詞典,目標用戶包括半專家,見識廣泛的外行(Tarp 2005)。編纂者在挑選術語時參考了已出版詞典的詞條、索引及西班牙語和英語分子生物學文本。這些文本是根據Bergenholtz & Pedersen(1994)提出的標準挑選的。選條(對等語)由經過詞典學專門訓練過的專家完成(Bergenholtz, Kaufmann & Tarp 1994)。下文以詞條gene中的釋義為例進行討論。這一詞條包含了用以幫助文本產出和翻譯的語言信息,不過在例子中并未顯示。
geneA gene is a DNA sequence encoding a protein. tRNA or rRNA. For eukaryotes a gene can also be defined as a transcribed DNA sequence or transcript unit. In prokaryotes two or more proteins are often encoded in the same transcription unit, and such a transcription unit plus its associated regulatory sequences is termed an operon.
這條釋義和其他的釋義都是分子生物學專家和詞典學家反復討論后撰寫的,力圖符合目標用戶的特點。詞典學家認為應該使用大眾化語言,但是專家們卻擔心大眾化的語言會影響釋義的科學性。最后,雙方達成一致,根據目標用戶的特點來決定用哪種表達方式撰寫釋義。在詞典編纂過程中,專家們并未查詢語料庫來撰寫釋義。當然編纂過程中,詞典學家曾利用語料庫協助選條、挑選搭配和使用實例等。
相對而言,《丹麥語網絡詞典》是專為外行編纂的普通詞典。下面是該詞典中丹麥語單詞gen(基因)的兩個釋義,一個釋語偏科學化,另一個釋語偏大眾化。
gen
1. arveligt anlg, som knytter sig til knscellernes kromosomer i mennesker og dyr
2. tendens til eller disposition for noget bestemt
gene
1. hereditary systems related to the chromosomes in female or male sex cells i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2. tendency or disposition for to like to do something
這兩個釋義中,第二個釋義是分析語料庫得來的,第一個釋義是詞典學家根據所具備的專業知識撰寫的。這種注釋方法似乎和上文所討論的英語詞典的釋義方法不一樣。
七、 結語
本文開頭質疑了Lees和Itkonen對語料庫的否定看法,認為事實并非如此,語料庫對于詞典學有巨大的實用價值,許多詞典編纂都要求以語料庫為實證。然而,本文也發現Lees和Itkonen看似武斷的說法也有幾分道理,因為語料庫分析的結果也有可能不準確、有誤導性。雖然這些問題多出現于普通詞典領域,但是也和專科詞典研究息息相關。簡而言之,專科詞典選條和釋義有兩種方式: 一方面,詞典學家可以在語料庫中搜尋相關的術語和釋義;另一方面,可以讓專家(經過基本的詞典學訓練后)來做此類工作。只有當專家根據個人從事的專業領域的知識來評判語料庫中的數據時,語料庫才能在詞典編纂的挑選數據階段有所幫助。
詞典學家或者術語學家通過查詢語料庫來確認某個術語是否正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學科專家們可以立即判斷該術語是否正確或者是否與某個學科有關,但是外行(例如詞典學家或者術語學家)則可能意識不到某些術語應該屬于某一學科范疇,因此會忽略許多術語詞匯及相關的搭配組合。另外,語料庫里的釋義有可能過于陳舊、不正確或者不相關。專門建立一個即時的專科語料庫也不太可行,因為釋義常常受語境所限而不全面,只有專家才能判斷實情。經常有言論稱,使用語料庫是為了證實收錄在專科詞典中的術語和釋義的真實性。很明顯,用戶總是想要知道他們是否可以信任這類詞典里的信息。然而,語料庫既無法確保這些術語適用于某一部待編詞典,也無法判定其中釋義的質量優劣。
一般說來,編纂一部專科詞典最好在兩年內完成,以避免在完工之前前期工作成果已過時。對于那些在兩年內無法完成的大型詞典的編纂,建議分模塊進行,例如按詞典功能分步編纂,或者是按信息類型分步編纂,同時按照學科變化(諸如科技創新、發現和現行法律的修訂等)來修訂已經完成的部分。但是,只有具備基本專業知識的專家才能完成這樣的工作。毋庸置疑,語料庫可以協助詞典學家完成相當一部分詞典編纂任務,但是,人在詞典編纂過程中的積極因素不容忽視。“語料庫驅動詞典學”或者“以語料庫為基礎的詞典學”的說法和看法有待商榷。相較之下,“語料庫輔助詞典學”的說法更為準確地描述了語料庫運用于詞典學的現實。
參考文獻
1. Astigarraga J, Zabalza J, Almodovar A.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aedias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Iberian Peninsula(18th,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Storia del Pensiero Economico, 2001(41): 25—63.
2. Atkins B T S, Rundell M. The Oxford Guide to Practical Lexicography.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3. Bergenholtz H, Rajaonarivo S, Ramasomanana R, et al. Rakibolana MalagasyAlema. Antananarivo: Leximal, 1991.
4. Bergenholtz H, Pedersen J. Zusammensetzung von Textkorpora für die Fachlexikographie.∥Schaeder B, Bergenholtz H.(eds.)Fachlexikographie. Fachwissen und seine Reprsentation in Wrterbüchern. Tübingen: Narr, 1994: 161—176.
5. Bergenholtz H, Kaufmann U, Tarp S. Vore mnd i Havanna: Udarbejdelse af konception til en spanskengelsk genteknologisk ordbog.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4(13): 291—304.
6. Bergenholtz H, Tarp S.(eds.)Manual of Specialised Lexicography. Amsterdam: Benjamins, 1995.
7. Bergenholtz H. Korpusbaseret leksikografi. LexicoNordica, 1996(3): 1—15.
8. Bergenholtz H, Kaufmann U. Terminography and Lexicography. A Critical Survey of Dictionaries from a Single Specialised Field.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7(18): 91—125.
9. Bergenholtz H. The Role of Linguists in Planning and Making Dictionaries in the Modern Information Society.∥Deny A, Kwary N W, Musyahd L.(eds.)Lexicography and Diction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ASIALEX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rabaya: Airlangg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
10. Bergenholtz H, Agerbo H. Extraction, Se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eaning Elements for Monolingual Information Tools. Lexicographica, 2014(30): 488—512.
11. Besomi D.(ed.) Crises and Cycles in Economic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aed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