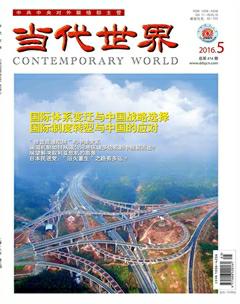“修昔底德陷阱”與中美關系
徐棄郁
關于中美兩國多方人士熱議的“修昔底德陷阱”,其真正意義在于提出一種警示,提醒精英階層和大眾清醒認識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但其警示意義也絕不應夸大,因其無法覆蓋當今世界的一些重要變化。在這些舊的變量面前,傳統國際政治邏輯的慣性不會消失,但其最終結果一定會受到影響。
近年來在涉及中美關系的新詞匯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使用頻率無疑名列前茅。不僅國內外學者為之展開激烈的爭論,中美兩國領導人也在公開場合加以引用,標志其已經進入決策話語體系。然而,關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爭論仍在發展,其中的一些問題反而更加復雜化,使人們更難對中美關系的現實做出準確判斷。在當前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均有所增強的情況下,進一步解讀“修昔底德陷阱”確有必要,以便廓清我們的語境,更好把握中美關系的趨勢。
“修昔底德陷阱”的由來
在西方經典戰略研究中,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有著特殊地位,其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位于戰略典籍之首。對于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發生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他將戰爭起因總結為一句著名論斷:“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這一論斷如此醒目,以至于后人往往忽略了古希臘語中“不可避免”一詞的語氣遠弱于現代漢語和英語,也忽略了修昔底德忠實撰寫的具體史實。比如,斯巴達并不害怕雅典的實力,真正急于打仗的不是雅典和斯巴達,而是第三強國科林斯,等等。這一論斷經過后世反復引用,已經被當成解讀大國崛起和大國戰爭的重要歷史規律,并且構成了一種特殊的語境。在這里,修昔底德已經不再是作為歷史學家的修昔底德,其豐富的思想、深邃的洞察被符號化為一個非常簡單的判斷句式。只要提到修昔底德,往往就暗示著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零和”競爭以及最終難以避免的大規模對抗。
因此,當中國實力迅速上升、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斷突出的時候,美國國際政治學界重提修昔底德也不出意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拉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于2012年8月22日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文,首次運用了“修昔底德陷阱”一詞。在這篇不到800字的短文中,阿利森將“修昔底德陷阱”稱為“歷史學家的隱喻”,意指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競爭所帶來的危險,而全文的問題則是中國崛起能否避免這種“修昔底德陷阱”。就此,該文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對中國崛起后的中美關系前景表示不樂觀,其主要依據就是歷史經驗,稱1500年以來大國崛起的歷史案例中多數以戰爭告終;第二,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目的不是要說明悲觀的結局不可避免,或者說“國家領導人是歷史鐵律的俘虜”,而是要認識兩國所面臨挑戰的艱巨性。因此中美兩國必須更加坦率地討論可能的對抗和熱點,并根據對方的核心要求進行自我調整。[2]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正值中美在南海問題、中日在東海問題上關系緊張之時。實際上,從2010年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后,中美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不斷增加,雙方在地區事務特別是地區安全事務中的關系趨于緊張。中美兩國的學界已經對中美關系的前景表示擔心,一些學者開始探討如何降低相互間的不信任感,比如中國學者王緝思和美國學者李侃如合著的《中美戰略互疑》就體現了這一傾向。[3]“修昔底德陷阱”在內容上延續了這些看法,其不同之處在于,由于“修昔底德”一詞反映出一種強大的傳統語境,因而體現出更多歷史含義甚至是歷史宿命,所以對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的艱巨性”強調得更加充分。另一個不同之處在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是對中美關系現狀或未來的真實描述,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總結或歷史歸納,而是一種建立在粗線條歷史梳理基礎上的抽象概念,最終的落腳點是對中美關系的政策建議。所以,“修昔底德陷阱”與現實政治的關系更大,與學術特別是歷史研究的關系較小,屬于學者對政府的提示和喊話。
對“修昔底德陷阱”
的反應、爭論及錯位
“修昔底德陷阱”一經提出,就引起了政界和學界的關注。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國家利益》雜志上發表了《美國、中國和修昔底德:北京和華盛頓如何避免典型的不信任與恐懼模式》,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也發表了《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4]這些文章與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立意基本一致,重點在于政策建議,即如何避免中美重蹈歷史上大國爭衡的覆轍。政界特別是決策層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反饋總體上比較正面。在中國方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接受美國《世界郵報》專訪時就公開使用“修昔底德陷阱”一詞,提出中美兩國“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中國正視歷史上其他大國的教訓,將堅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發表演講時再度提到該詞,明確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主要來自大國之間戰略誤判。9月25日,習主席在美國國會山集體會見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領導人時又指出:“中美關系發展要防止跌入所謂大國沖突對抗的‘修昔底德陷阱,要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在中國對外話語中,習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恰恰可以視為“修昔底德陷阱”的解決途徑,兩者實際上構成了相反相成的一對概念。在美國方面,奧巴馬政府同樣強調中美不會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總體來看,決策層沒有也不可能對“修昔底德陷阱”的提法在學術上進行較真,而是將這一提法作為抽象的警示概念接受下來并做出正面回應。這基本符合了“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質和最初立意。
而學術界對其質疑則一直存在,特別是2014年一戰百年的紀念更使得“修昔底德陷阱”的爭論升溫。[5]在中國和美國都有不少學者參與其中,爭論的焦點大致有三個。
焦點之一:“修昔底德陷阱”是否適用當今時代。持反對意見的學者認為,修昔底德是在2000多年前做出的類似論斷,今天的世界則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很可能走向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說法已經不適用于當代。柯慶生曾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其在新書《中國挑戰》中專門指出,核武器出現、全球化進程、國際機制的發展、國際金融、跨國生產鏈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中美面臨著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完全不同的國際環境。[6]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埃利克森也在國會聽證中加以呼應,稱“修昔底德陷阱”是“過時”的、“屬于歷史垃圾堆”,而且給中國方面利用,因此美國政府的話語體系應加以摒棄。[7]實際上,不少中國學者也否認“修昔底德陷阱”在當今時代的適用性。但是,阿利森教授堅持原先的立場,而且隨著中美在南海等問題上的矛盾尖銳化,他比2012年時更加強調中美對抗的可能性:“美國與中國在未來十年內發生戰爭的可能性要高于目前大家所認識到的”,“當今時代首要的地緣戰略挑戰既不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也不是復興的俄羅斯,而是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8]
焦點之二:“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提法本身在學術上是否嚴謹。“修昔底德陷阱”一經提出,就有學者將其作為一種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來進行評判,質疑其可靠性和嚴謹性。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副教授詹姆斯·霍爾姆斯屬于立場一貫的“疑華派”,但在“修昔底德陷阱”問題上卻表示了異議。他在《當心“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一文中將反對意見集中于四個方面,比較有代表性:(1)修昔底德關于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判斷不能看成是一種歷史鐵律,歷史發展應充分考慮人的能動性;(2)歷史類比非常不貼切,如果將中美看成是雅典與斯巴達,那么誰是斯巴達、誰是雅典?換言之,美國自認為是西方文明的執牛耳者,心理上不可能接受讓中國來類比西方文明的正宗源頭——雅典;(3)后來的歷史特別是一戰前的歷史與修昔底德的論斷不符,同是崛起大國的美、德、日與守成大國英國的關系發展差別巨大;(4)現實中中美之間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存在,但可能性不是必然性,最終的結果取決于兩國的決策者。[9]面對這些質疑,阿利森將歷史上崛起—守成大國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案例研究,表示在其選擇的16個歷史案例中,一共有12個案例都是以災難性的戰爭結束。[10]實際上,阿利森教授本人并非歷史專業出身,其16個案例的選擇和研究均存在問題,所以在效果上似乎適得其反,有越描越黑之嫌。
焦點之三:誰應為“修昔底德陷阱”負責。其中美國學者大多認為崛起大國應更多負責,也應更多自我控制,而中國學者則強調守成大國應負起更多責任,另有不少學者就中美是否會落入這樣一個陷阱而爭論。當然,還有一些學者干脆將“修昔底德陷阱”作為“極端現實主義”甚至是一種反華宣傳加以揭批,或者深挖雅典帝國主義擴張的根源,這些就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從對“修昔底德陷阱”的反應和爭論來看,政界更多將其當作一種警示性的抽象概念,而不是歷史規律的總結,因此中美兩國的領導人的反應實際上符合了這一概念的政策建議性質。習近平主席后來一再提及這一概念,更是借用了其特有的語境來向世界強調中國和平發展的決心和信心。相形之下,學界的爭論焦點與提出這一概念的本意卻不盡相符。正如前文所述,“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本身既不是現實的展望,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總結,因而學界爭論的三個焦點實際上相關性并不很強,關于其學術嚴謹性的爭論尤其有錯位之嫌。平心而論,霍爾姆斯等人的反駁本身沒有什么問題,只因其對歷史并非專熟,存在一些瑕疵。但有趣的是,阿利森教授本人面對質疑,居然也開始將“修昔底德陷阱”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學術概念來論證,而且還要證明其是一種歷史規律,結果只能使爭論越發偏頗,含義更加模糊,學術價值反而進一步降低。
“修昔底德陷阱”
對中美關系的意義及其限度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的真正意義是在于提出一種警示,提醒精英階層和大眾清醒認識中美關系面臨的挑戰。這種挑戰的艱巨性來自其深遠的歷史背景,來自根深蒂固的西方戰略文化傳統,也來自現實政治的邏輯。從歷史上看,大國崛起從來不可能一帆風順,其實力和影響力的迅速增長大多會被守成大國視為挑戰,這種結構性的矛盾的確存在。更重要的是,這種矛盾和沖突不可能簡單地歸結為某一方的責任或“險惡用意”。在多數情況下,雙方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結果卻可能引發對方的錯誤判斷而導致緊張升級,發展成為典型的“安全困境”,最終導致雙方戰略性的攤牌。
深入觀察中美關系近年來的發展,可以發現類似的趨勢已經出現。如在南海問題上,中國捍衛的是自身重大國家利益,而美國維護的則是其在地區盟國中的“可信度”或者威望,雙方的讓步空間都不多。隨著中美兩國實力差距的縮小,這種對峙將具有越來越深層的戰略含義,“力量的較量”很容易滑向“意志的較量”。在美國方面,對中國的疑懼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以往,美國一直認為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有利于美國將中國納入自身軌道。然而近期,這種基本認識開始受到公開質疑。美國對外關系理事會(CFR)2015年3月發表報告,宣稱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試圖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做法是錯誤的,“無疑幫助中國成為美國的未來對手”。[11]其對策就是要把中美之間的利益聯系重新分割開,阻止甚至逆轉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進程。總體上看,這種在國際體系中排斥中國、以免中國過于強大的想法已經作為一種政策選項在美國出現。現實中,奧巴馬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并取得突破,也可以看成是這種在國際體系中“排斥中國”的一種表現。這種傾向無疑將侵蝕中美關系最重要的基礎——利益上的相互依賴,防止中美走向對抗的任務也因此變得更加艱巨,更加緊迫。
當然,“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意義絕不應夸大。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它無法覆蓋當今世界的一些重大變化,其啟示必然是單一的、線性的。目前,中美兩個大國既競爭又合作的總體態勢沒有改變。雙方在亞太事務,特別是南海問題上的對立非常明顯,互信程度難以提高,但在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上的立場卻比較接近,承擔著相似的大國義務。201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大會的成功反映出,中美在重大全球性問題上不僅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也有著相當大的合作空間,中美兩國的密切合作是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必要環節。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雙方務實合作將“更多更好惠及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12]在這些新的變量面前,傳統國際政治邏輯的慣性不會消失,但其最終的結果一定會受到影響。中美關系終將超越、也必須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責任編輯:徐海娜)
[1] [古希臘]修昔底德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謝德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9頁。
[2] Graham Allison, “Avoiding Thucydidess Trap”,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2.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2265/avoiding_thucydidess_trap.html.
[3]王緝思、李侃如著:《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4] Robert B. Zoellick, “U.S., China and Thucydides: How ca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void typical patterns of distrust and fear?”The National Interests, 2013, July-August, pp.22-30; 鄭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觀察者網, http://www.guancha.cn/zheng-yong-nian/2012-09-04-95260.shtml.
[5]美方學者的觀點可以參見Richard N. Rosecrance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6] Thomas J.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5, pp.37-62.
[7]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關于“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安全角色”聽證會,2015年7月23日,http://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50723/103787/HHRG-114-FA05-Wstate-EricksonA-20150723.pdf
[8]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The Atlantic, Sep.24,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其歷史案例研究參見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16 major cases of rise vs. rule”,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9] James R. Holmes, “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 Trap: Why the U.S. and China arent necessarily Athens and Sparta or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WI”, http://thediplomat.com/2013/06/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
[10]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 Trap Case File: 16 major cases of rise vs. rule”,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publication/24928/thucydides_trap_case_file.html
[11]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ouncil Special Report no.72, March 2015, p.18. 多位美國學者與作者會談時表示,該報告不能代表CFR觀點。然而作為CFR的一份大報告,其影響和象征均不能低估,在美政界已經產生不少共鳴。
[12]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載《人民日報》2015年12月1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