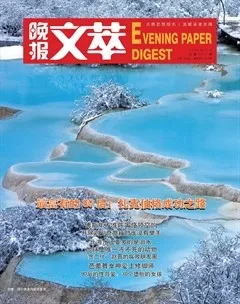鄉下的留守老人
木梅
國慶節回鄉下老家,我驚訝地發現,偌大的村子只有少數幾個中壯年和二三十個老人在。得知我回來了,老人們紛紛來看我,其中有幾個老人用十分羨慕的語氣對我的母親說:“還是你家的娃讀書有本事,有正式單位,能放假回來。我家的在外打工,一年到頭都難有假,很少能回來看我們。”
老人的這些話,倒出的是無奈和失落,也反映出當下農村的現狀,由于子女們紛紛外出務工,年歲已高、本該頤養天年的他們,卻要重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幫下輩們背負起本不屬于自己的責任,弱勢、被動地處理著復雜甚至是險惡的鄉間人際關系。
我有一個堂伯,今年已83歲,背駝得十分厲害,走路時,上半身幾乎彎得跟地面平行,頭都要貼到地上了,樣子顯得非常艱難。路上見到時,我遞給他一支煙,他接過后,說了一句讓我驚訝不已的話:“兒子不在身邊就是不行,只能任人欺負。”
原來,堂伯到村里另一戶人家的稻田里撿稻穗,都是些主人家漏掉隨后也會被翻壓到地底下去的,即便是全部撿上來,也碾不出多少稻粒來。可這塊稻田的主人,比他低一輩的非本家侄子狠狠地將他罵了一頓,還強行將其推搡開。“把我都推倒在地,腿差點摔斷了。”
像這樣的事,絕不只是個案。我另一位七十多歲的大媽,也跟我說了一件令人痛心的委屈事。她獨自一人在家養了十幾只鴨子,整日精心照料,希望日后能賣點錢,補貼家用。可誰知,鴨子偷吃了一個強鄰家的稻子,那強鄰便將拌有農藥的米撒在田埂上。結果,一夜之間,大媽的鴨子全部被藥死。“兒子不在家,我一個老太婆,吵也吵不過他,打更打不過他,只能忍氣吞聲。”
委屈除了來自外人,往往也來自親人。我們村子有一位老人,兒子和媳婦都在外面打工,便將正上初中的兒子交由她帶,老人幾乎將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放在這個孫子身上,為他洗衣、做飯,操勞一切。可孫子天生頑劣,成績不好,性格也倔強,兒子和媳婦便將所有的責任都怪罪到老人身上,說她沒盡到責任,把他們的孩子帶壞了。那孫子甚至還問她:“奶奶,你是不是把我爸給你的伙食費偷偷克扣了?”老人一邊抹著眼淚,一邊跟我說:“一天三頓,只給20元錢伙食費,還要天天有葷菜,我怎么克扣?”
我在村里沒見到一個老人是不干活的,村里的紅白喜事、各種人情往來都是需要錢的,而他們又不愿開口朝在外打工的子女要,也很少有子女會主動給,因此他們只能拼命地節省,并將地里耕種出來的東西拿到外面去賣,以應對這些開銷。
我還有一個叔叔,在家養了好幾十只雞,我問他養這么多雞干嗎?他說,三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過年回來要吃,走的時候,每家還要帶上幾只。我問,那他們給錢嗎?“給錢?不向我要錢就已經很好了。”叔叔回應道。
更多的是留在老家的他們時刻都在等待著孩子們的歸來,渴望能跟他們團聚。我一個小學同學在鎮上開了一家手機維修店,他說,有一天,有一個大爺來修手機,他檢查后卻發現手機是好的,不需要修。可大爺堅持認為手機是壞了,因為近一個月來,他一直沒接到在廣州打工的兒子打來的電話。
這就是我的鄉下父老鄉親,年邁的他們善良、堅毅,生活得艱辛,強鄰的欺負,子女的錯怪和誤解,他們都能默默地忍受下去,他們是一群無人歌頌、無人在乎其尊嚴和內心需求的鄉下留守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