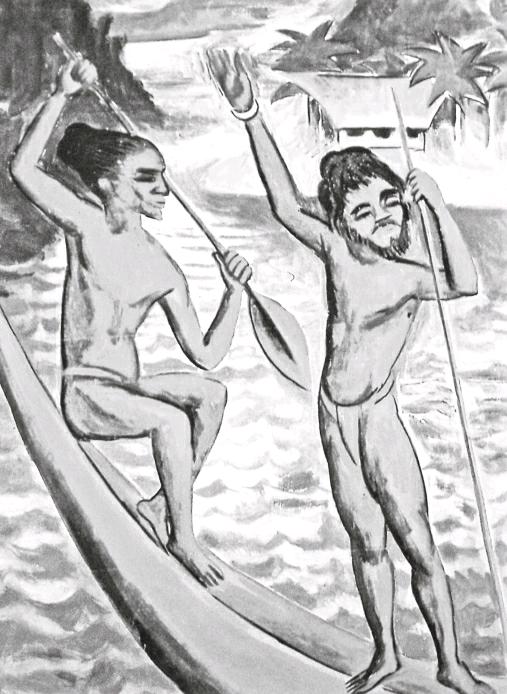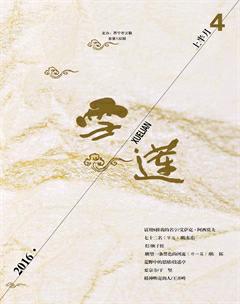文學和記憶
伊凡·克里瑪
我經常被問及正在寫什么,但是至今沒有人問我為什么寫作。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種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和真誠在它手中泯滅。我們寫作是為了保留對于一種現實的記憶,它似乎無可挽回地跌入一種欺騙性和強迫的遺忘當中。
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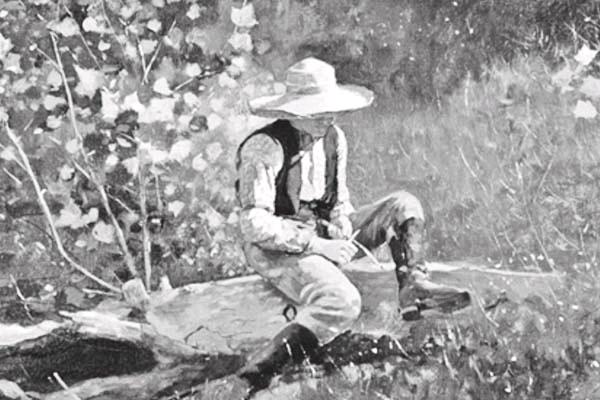
過去常常把寫下的東西都認為是文學。李維、塔西佗,同樣還有西塞羅和維吉爾,都簡單地被認作文學創造者。我們將圣經稱作“書中之書”,于其中我們發現和神話故事并列的有儀式規定、歷史記事、箴言集錦、法律條文及愛情詩。許多古代和中世紀關于法律、醫藥、地理、數學等學科的書都是用韻文寫成的。在它們當中,幻想的成分超過事實本身,今天我們更寧愿將其當作文學來讀而不是考慮它們在科學上的優點。只有在現在,我們才開始考慮一門技術性的、最特殊的寫作,將其從“文學”中分離出來。我們怎樣把每天淹沒讀者的洪水般的垃圾進行分類?關于什么是文學什么不是文學的精確界線在哪里?當然,有著許多種分界線和定義,其中大多涉及作品形式上或美學上的特點。從形式上定義文學的嘗試在結構主義的理論和定義中達到了一個頂峰。它也許能將科學著作從藝術著作中劃分出來,但是忽略了內容因素,而通過內容,將真正的藝術從僅僅是娛樂中劃分出來的一系列品質才顯露出來。更有甚者,結構主義對作品于社會的沖擊毫無興趣。我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想引起對一個理論問題的關注,而是作為一個作家,我愿意盡可能精確地定義我所以從事的活動的原因和意義。
兩百年前,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伊曼努爾·康德在他的《判斷力批判》中詢問了同樣的問題,他試圖區分科學和藝術(藝術是在自由狀態下的創造)以及藝術和手工藝(在一種杰出的區分中,他將藝術定義為從中受益的)。康德當然意識到一部作品美學品質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于創作者本人的作用賦予了密切的注意,或者,用他的術語來說,如果沒有天才,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將不可能產生。我并不想分析康德關于創造者現象或他的活動的定義,但是,他發現若不考慮到創造者本人的素質,他的思想及動機,便不能真正理解一部藝術(并且因此是文學)的本質,這是非常關鍵的。
2
這使我返回到我最初提出的問題上來:我為什么寫作?盡管這個問題很少被問及,但其答案可以告訴我們許多。這里,僅舉希臘作家尼科斯·卡贊扎基斯談促使他寫作的因素為例:
“在我們內部,有著層層疊疊的黑暗——喧鬧的聲響,多毛的、饑渴的野獸。那么,沒有什么東西死去嗎?難道說在這樣一個世界中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死去?那些原生的饑渴和憂傷,在人類黎明到來之前的那些夜晚和月光,將繼續存活;那些饑渴和苦惱將永遠伴隨著我們。我曾經驚恐地聽見我所承載的可怕的負擔在我的內臟中開始吼叫。我將永遠不能得救嗎?……說到底,我是最小的和最受鐘愛的孫子,除了我以外,他們(我的祖先)沒有指望和庇護。所有他們遺留下來的復仇、享受和受苦,只有通過我們才能繼續。如果我消亡了,他們也將跟著我消亡……”
這個充滿感情的自白以同樣充滿感情的作家使命的展望而結束:
“我知道我的真實面貌和我靈魂的責任:盡可能富有耐心、充滿愛意及運用我所能掌握的技巧,將這個面貌描繪出來。去‘描繪它?那是什么意思?它意味著將這一切大白于世。因此卡倫從我這里什么也拿不走。這就是我最大的野心:什么也不讓死亡帶走——除了一點骨頭什么也拿不走。”(尼科斯·卡贊扎基斯《向希臘人報告》,第26頁,布魯諾·卡西勒出版社,牛津,1965年)
當我最初讀到這一段時,我驚訝于卡贊扎基斯如此接近于我對為什么要寫作和在寫作中我期待什么的答案。我記得在戰爭最后的日子里我的感受如何:在一個集中營里我度過了大部分戰爭時期,幾乎在我周圍的每一個人——我的同代人和我的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人——都死去時,我卻幸存下來。這時我被一種類似賦予了一種責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壓倒:去變成他們的聲音,他們抗議將他們的生命從這個世界上抹去的那種死亡的叫喊。幾乎正是這種感情促使我去寫作,而我當然沒有想要去遏制寫作、創造故事和尋找最好的方式向別人轉述我想說的東西那種不可遏制的沖動。
3
變成別人的聲音這種令我振奮的感情,以不同的形式在其他時機再現于我的生活之中。在不自由的時期,當我們被謊言所轟炸,每一件真實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本身的事情實際上并不存在并被宣布為虛無和遺忘時,寫作是為了戰勝這種毀滅。寫作是為了否定死亡,而它采取了如此眾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每一種都將現實、人類尊嚴、受難、挑戰和真誠在它手中泯滅。這種感情為大多數寫作的作家所擁有,在不自由的條件下,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只活了不長時間。我們寫作是為了保留對于一種現實的記憶,它似乎無可挽回地跌入一種欺騙性和強迫的遺忘當中。引用米蘭·昆德拉在 《笑忘錄》里的一段話說:“一個民族毀滅于當他們的記憶最初喪失時。他們的書籍、學問和歷史被毀掉。接著另外有人寫出不同的書,給出不同式樣的學問和杜撰一種不同的歷史。”在同一本書中昆德拉發明了一個短語并啟發了我:“遺忘的總統。”一個在“遺忘的總統”引導下的民族將走向死亡。而適用于一個民族的同樣也適用于我們每一個人。如果我們失去記憶,我們將失去我們自己。遺忘是死亡的癥狀之一。沒有記憶我們將不再是人類成員。
超越我們自身死亡的斗爭是人類的精華。死亡不再是每一件事情結局的情感,是基本的生存情感之一。通過反抗死亡,我們反抗遺忘;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通過反抗遺忘,我們反抗死亡。回到卡贊扎基斯充滿情感的自白,這種反抗可能采取的形式之一,是創造的行為。自覺或不自覺地,這種確信必然成為創造者當下的頭腦狀態:因為我創造,所以我反抗死亡。“我建立一座比銅還持久的紀念碑”。這就是我們為什么不能忽略為什么寫作、為什么創造這種問題的原因,如果我們沉思創造的意義、價值和真實性的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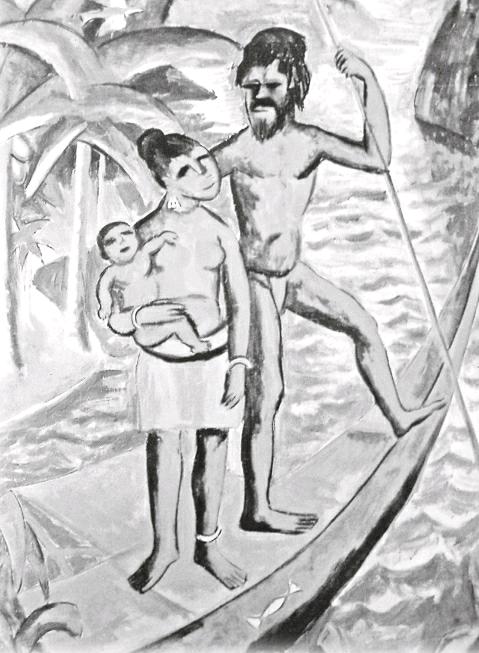
戰爭結束之后,我卻并沒有從一個幸存者的角度寫出關于戰爭和集中營的經驗,實際上關于那些事情我幾乎沒有動筆。記憶并不僅僅通過對某一種特定經驗的如實報道來體現,而毋寧說它是一種責任,這種責任產生于對過去曾經降臨又離開的每一件事情延續性的意識,是對于如果我們不想在真空中消失便不能遺忘的那些東西的責任。我們正在經驗文明加速度的感覺,包圍在我們身邊豐富的信息及其喧囂同時帶來危險,我們將要在它的空洞中走向結局,我們將斷絕和根的聯系,陷入無盡時間和虛無。同樣的危險威脅著文學和所有的藝術。在現代歷史的某個時刻,對許多人來說,似乎記憶和傳統僅僅是一個必須加以拋棄的負擔。在我們這個世紀降臨于人類的災難由這樣一種藝術提供幫助,它推崇原創性、變化、無責任感、先鋒派,它嘲笑所有以往的傳統和蔑視在畫廊和劇院的觀眾聽眾,它以一種自以為是的愉悅沖擊瀆者,而不是對那些拷問人的問題提出解答。出現在這期間的極權主義制度將先鋒派文學視為頹廢而加以抵制,這無關緊要,然而基本上它也像先鋒派一樣輕視傳統和傳統價值以及真正的人類記憶,接著便試圖強加給文學一種假冒的記憶和虛假的價值。
每隔幾秒鐘就有一本新書問世。它們中的大多數將是使得我們失去聽覺的那種欺騙的一部分。這種書甚至變成遺忘的工具。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的問世是作為其創造者的一種喊叫,是對于籠罩于他本人,同樣也籠罩于他的前輩和同代人、他的時代、他所說的語言身上的遺忘的抗議。一部文學作品是激怒死亡的某種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