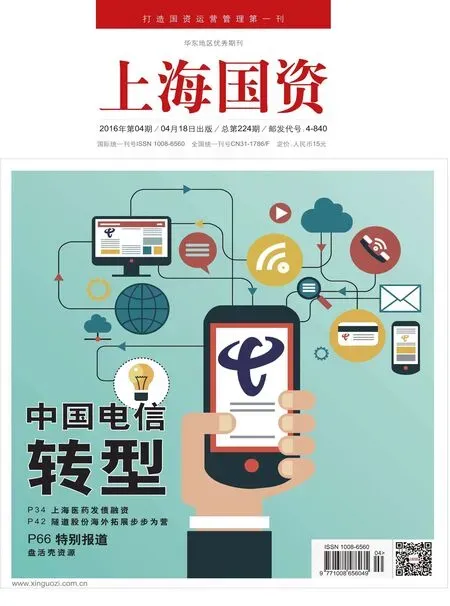上海電氣核電新局
文‖《上海國資》記者 孫玉敏
?
上海電氣核電新局
文‖《上海國資》記者 孫玉敏

全球首臺高溫氣冷堆壓力容器順利發運
“智能制造”的核電裝備巨頭漸行漸近
上海電氣在核電領域技術地位繼續鞏固。
3月初,在東海之濱的上海電氣臨港基地,全球首臺具有四代特征的高溫氣冷堆核電主設備——壓力容器、金屬堆內構件分別在上海電氣核電集團上核公司、一機床公司順利發運,并成功交付華能山東石島灣核電站。
此前,上海電氣已順利完成三代核電AP1000、EPR技術關鍵核島主設備的制造交付任務。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裁、核電集團總裁朱根福表示,面對核電復蘇的機遇,上海電氣核電產業已進入發展新階段。未來,核電集團將在專業化基礎上利用互聯網技術,譜寫核電智能化制造的新篇章。
高溫氣冷堆
高溫氣冷堆是由清華大學自主研發的具有第四代技術特征的先進核能技術,以其優良的發電效率,尤其是突出的安全性和快堆技術等被并稱為“超越下一代”的“未來核電”。
朱根福告訴《上海國資》,高溫氣冷堆的特性,使得這種堆型可以避免類似于福島核事故出現的堆芯熔化、放射性大量釋放的重大事故。“高溫氣冷堆以耐高溫的石墨作為慢化劑和堆芯結構材料,用化學惰性的氦氣作為冷卻劑,堆芯有煤球粗細,而壓水堆的燃料塊大概香煙粗細,高溫氣冷堆這種堆芯結構和設計方式,使得所有現實可設想的嚴重事故的后果,都沒有顯著的場外輻射影響。”
但是,這也使得高溫氣冷堆這種堆型,與其他傳統核電主設備相比,擁有更大的外形尺寸和更復雜的結構,制造難度更大。反應堆壓力容器、金屬堆內構件作為這種堆型核島一回路的關鍵主設備,制造難度更是可想而知。
“該堆型在實驗階段,上海電氣就曾參與設備制造,加上上海電氣已有多年豐富的核電設備制造經驗,通過不計其數的項目技術溝通會、現場技術與施工人員夜以繼日的艱苦工作,我們最終完成了一個又一個突破。”
朱根福強調,兩件主設備的順利出廠,標志著通過自主創新、技術攻關、試驗驗證、制造測試,上海電氣已完全實現高溫氣冷堆反應堆壓力容器、金屬堆內構件的國產化。“這意味著上海電氣核電裝備制造能力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也為后續順利建成全球首座球床模塊化高溫氣冷堆商用核電站示范工程奠定了重要基礎。”
但是,高溫氣冷堆在某些地方仍需改進,比如造價高于目前市面上的壓水堆機組等。
“這些特點,決定了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高溫氣冷堆還難以成為主流技術路線。未來上海電氣核電設備制造的主要市場,仍將在國家2003年前后即確定的壓水堆技術路線上,也就是目前的CAP1000、‘華龍一號’、CAP1400三代核電技術。”
進步之路
據了解,目前核電站的堆型一般根據慢化劑和冷卻劑的不同來劃分。冷卻劑,一般有液態水和二氧化碳、氦氣等氣體,堆型分為水冷堆和氣冷堆。
氣冷堆的慢化劑是石墨。水冷堆的慢化劑一般是水,水又分為輕水和重水,堆型就有輕水堆和重水堆之分,輕水堆又分為沸水堆和壓水堆。
朱根福對《上海國資》介紹,現在世界上商業運行的約440臺機組大部分在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后建設,稱為第二代核電機組。但自美國三里島核電站和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發生后,在美歐等國家的推動下,第三代核電的概念產生,與第二代的根本差別在于,第三代把設置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作為設計核電站必須滿足的要求,更安全也更經濟。
他介紹,我國第三代核電建設的步伐走在世界前列。國家核電技術公司引進的美國西屋公司的非能動先進壓水堆AP1000(落地電站浙江三門、山東海陽,在建)以及中國廣核集團公司引進的法國阿海琺公司的改進型壓水堆EPR(落地電站廣東臺山,在建)都屬于第三代核電機型。同時,由中廣核和中核聯合開發的融合了“能動與非能動”先進設計理念的我國自主三代核電“華龍一號”,也落地福建福清5、6號機組和防城港二期,目前均已開始建設。
此外,在消化引進第三代先進核電AP1000技術的基礎上,我國還正在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功率更大的非能動大型先進壓水堆CAP1400(示范電站規劃于山東榮成石島灣)。
2014年,上海電氣率先在國內完成三代AP1000核島主設備(壓力容器、蒸汽發生器、穩壓器)產品的配套交付。2015年,AP1000首臺堆內構件、控制棒驅動機構、EPR首臺堆內構件也已完成交付。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CAP1400項目也在順利制造中。
據朱根福透露,隨著紅沿河、寧德、方家山、陽江、防城港、福清等一系列二代加核電項目的交付,上海電氣具備了CNP1000、CPR1000二代改進技術的關鍵設備制造能力,形成、固化了批量生產百萬千瓦級機組的制造和管理體系。通過三門、海陽AP1000和臺山EPR項目建設,上海電氣已基本掌握了三代核電制造技術,關鍵設備批量化制造能力開始顯現。
與此同時,2015年3月,上海電氣與法國阿海琺AREVA集團合作,承擔了南非Keoberg核電站6臺更換蒸汽發生器的設備供貨任務,這是上海電氣首個真正意義上走出去的核電項目,也是國內裝備制造企業第一次通過國際合作的方式直接向國際市場供貨的大型核島主設備項目。
“這表明上海電氣完全有能力按照國際標準面向國際市場提供核電產品。”朱根福表示。
沖刺“智能制造”
超過20年的核電設備生產經驗積淀,上海電氣在核島主設備市場占有率達到42%,其中堆內構件、控制棒驅動機構達85%。目前,上海電氣的核電核島產品已經涵蓋第二代核電、第二代改進核電M310、CNP1000和CPR1000、第三代核電AP1000、EPR和“華龍一號”、CAP1400以及第四代核電技術特征的高溫氣冷堆等所有主設備產品機型。
除了承接國內訂單,目前上海電氣也已與意大利Ansaldo核能公司、西班牙Ensa公司分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并與德國、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的核電先進企業開展交流,積極拓展在核廢物處理和核設施退役等領域的國際合作。
在朱根福看來,無論是國內核電新建項目重啟,還是旨在推動核電技術裝備和電站設計建造能力輸出的“走出去”,“安全高效”都將成為我國發展核電的首要準則,核電設備企業要提高自身競爭力,都須從“安全高效”四字入手。
這需要設備制造企業在質量管理、體系管控方面有更大的提升。朱根福表示,2014年,上海電氣將旗下核電核島主設備制造企業組建核電集團,正是從專業化角度提升運營管控能力。成立一年多來,核電集團已在一體化管控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核電集團成立之初,我們按照一體化總體方案,對上核、一機床兩個不同體系的管理過程進行了整合優化,過去一年多,圍繞一體化管理制度和流程、管理職能重建和梳理,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重復問題,我們進行了重點解決,為從根本上實現核電集團集約型一體化管理體系,從根本上實現管理系統優化,建立優化的工作管控流程,做了很多工作,從根本上解決了以往機制性的問題。”
同時,核電集團正積極擁抱互聯網,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制造體系效率。朱根福表示,上海電氣在2009年前后就上馬了ERP等信息化系統,包括計劃管控系統、項目管控系統等,但在核電管理方面并未很好發揮作用,核電集團成立后有意識加強了這些工具的利用。“信息化系統等都是工具,作用在于提升傳統制造企業的管理能力。”
目前核電集團主要致力于用好原有的信息系統,但同時也在規劃引入智能化、互聯網系統設備進行加工制造和自動跟蹤記錄等信息化管控,探索核電設備制造向智能化制造轉化升級,實現核電產品從“傳統離散型制造”向“智能制造”的生產模式轉變。
據悉,目前上海電氣在核島關鍵設備堆內構件的制造中已成功應用了大功率激光焊接技術;同時正在積極探討在蒸發器管子管板焊接、堆內構件堆芯罩焊接等主設備制造中引入焊接機器人系統的智能化制造方案。
一個“智能制造”的核電裝備巨頭漸行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