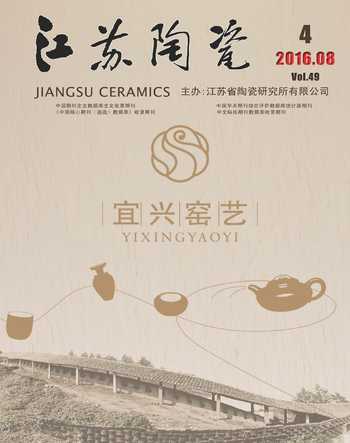借虛化實
王家新

說起佛所有人都知道,但要用語言或者形象來描述,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這是因為要將一個只有名字的概念具現出豐滿的形象,全憑每個人的主觀想象。如果對藝術創作的理解不深刻、不透徹,難免走向牽強附會、自說自話的歧路,甚至有時候會孤芳自賞,向隅而立。紫砂壺藝傳承已有幾百年,在不斷的繼承和發展中,紫砂藝人們總能吸收不同的文化和藝術元素為己所用,兼收并蓄的結果就是越來越豐富的題材和工藝在紫砂壺上被表現出來。以佛為題材的作品不可勝數,佛題材壺就是其中比較成熟的一個分支,造型主要有“僧帽”、“蓮座”等,都帶有鮮明的佛元素,因此也可以說佛與紫砂壺淵源頗深。紫砂壺藝不斷推陳出新,并非佛元素的簡單重復。如果單純為了契合主題而做出一把格調低下的壺,不僅毫無美感,且有違應有的藝術理念。壺終究并非雕塑,佛元素說到底仍需為壺服務,這是制作此類作品之前必須考慮到的。
佛門寺廟經常用香,香必用爐,其中有一種圓形三足香爐最常見到,其扁圓的形態簡潔大方。有人說香爐便是趺坐冥想的人,細細觀察頗有幾分相似,這件“佛心壺”(見圖1)便是以此為靈感衍化而來的。靈感是紫砂壺創作的先決條件,靈感迸發時雖只有一個不確切的輪廓,但各個部分已經在腦海中初步成型。隨后定圖稿,逐步完善造型上的種種細節,在這個過程中不時地查閱相關資料,可以加深對創作的理解,每有所得,有時甚至會恍然大悟,接著便以圖制樣。
作品“佛心壺”圓腹硬肩,周身玉潤,簡潔大氣。壺口置于平肩之內,壺鈕為含苞待放的蓮花,壺身層次以壺肩為界:上部安靜通達;下部仿佛蓮臺凈土。簡繁分明恰如兩個世界,芙蓉出水,意態寧靜,符合佛家安寧不爭、無糾無擾的思想境界。可以說 “佛心壺”通過造型表達的理念契合了佛家思想,形態承天接地,大度瀟灑,神態自若,如來自在,仿佛一片微縮的掌上凈土,有佛緣之人則一目了然,心靈得到凈化。流、鈕皆采用了暗接的手法,一彎曲線自壺流始,環繞一周,至壺把終,前后上下一氣呵成。“佛心壺”整體具有沉穩的禪態、福態、神韻和佛家的恢弘氣度,其最關鍵的原因便在于蓮臺狀壺身的塑造,配合點砂云貼,平添了光華素彩,以極樸素的手法重現了佛壇之上的蓮座云霓,配合壺蓋之上亭亭玉立的蓮苞狀壺鈕,不僅創造出騰云駕霧的感覺,而且還具有升華的禪覺,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時,原本在腦海中隱現的佛與現實里這把壺的影子重疊在一起,細細觀之,則壺即是佛,佛即是壺。
藝術作品需要一定的維度,然而人的心靈沒有這樣的維度。通常人們在對紫砂壺進行審美的過程中會帶有二維本位,而紫砂壺實際上有著三維的結構。進行壺藝創作就是要把內心深處的無維度加諸紫砂二維、三維的審美過程中,這也被稱為“借虛化實”。我們往往不能將心中的造型通過雙手簡單地呈現出來,而這一點可以通過圖紙實現:為造型披上一層文化的外衣,方便觀者理解其內涵和外延。
同樣,也不能在創作中簡單重現想象的事物,而經常將其模糊化處理,隱性地表達自身內涵。吳冠中先生曾說大象無形,越細致入微越是能找出更多不同,越模棱兩可越是能套入每一個輪廓——朦朧和神秘是思想馳騁無忌的樂園。需要說明的是,紫砂壺藝的模糊性體現在創作思維上的有意識模糊或無意識模糊,因創作主題的不同而有所選擇,這把“佛心壺”選擇的恰是前者。
借用文化上的共同認知及模糊化處理的技藝,可以極簡單塑造出令人心動的藝術作品。在紫砂壺的創作上,情感是靈魂,觀察是先導,想象是核心,思維和方法是上述一切的延伸。以自身的文化造詣為基礎,廣泛吸收文化知識,不斷開拓自己的視野,可以顯著提升作品的藝術境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豐富的物質生活創造了當下和諧安寧的創作環境,為藝術創作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經典可以再一次走上臺前,新的靈感不斷涌現,不同的文化元素、不同的思維方式,借一雙巧手流傳開來。紫砂藝術的前路是寬廣的,即使激烈的競爭在所難免;只要不斷提升自己的技藝,就必然能開拓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創作之路。